
《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美] 克里斯蒂娜·J.沃利著,张伊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月版,332页,68.00元
以梭罗为主要代表的自然写作是美国文学历史中的重要分支。近年来,随着对自然写作研究的深入,对这方面的作家和作品的挖掘和了解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关注与自然写作相关的一个象征意象,也即,作为美国象征的“田园意象”(pastoral image)。
田园意象古已有之。古罗马维吉尔笔下的田园描写,后来在中世纪时转换成牧羊人形象,到了文艺复兴早期更是关联到了爱情的内容与意境。但是就美国而言,作为新世界的栖居地,田园意象华丽转身,一方面沿袭了传统的意境指向,另一方面融入了新的内容,与这块崭新的土地相匹配,更与新土地上的主人的心理欲求相结合,表现了对田园意象的新的理解。简单而言,就是处于自然与人工间的一种“中间状态”。里奥·马科斯在其名作《花园里的机器: 技术与田园理想在美国》(1964)用总结性的话语指出,“的确,花园与森林的混成,那种带有‘人工野味’的意境指向了美国式的田园意象”。
马科斯的新发现基于对西方文学传统的透彻了解,同时也蕴含了对美国古典作家作品中的田园意象的深刻感悟,他上溯古罗马维吉尔笔下的牧歌传统以及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的田园象征,下及美国作家霍桑、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等作品中田园意境的表述和由此产生的情感的纠结,并以美国历史和文化中各个方面的人物对田园意象的阐释为背景,深刻剖析了田园意象在美国人生活中构成的文化情结,由此导致的对于在荒蛮与人工自然间的“中间地带”生活状态的渴望,以及面对以机器为象征的工业化时代到来的既欢迎又抵制的矛盾心理。如果说对于旧世界的那些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的诗人作家而言,田园意象更多的是表达一种远离尘嚣的乌托邦愿望,那么在马科斯看来,这种乌托邦情结在新大陆依然留存,如溪流般缓缓但不间断地流动 ,同时,不同的是,在这里,人工的自然也参与自然的生长与生存过程。所谓“人工野味”,强调的是“野味”,支撑的是人工的力量,“花园”是其努力的结果,“森林”是其仿照的对象。两者的结合既维持了自然的原态,也体现了人的存在。人在自然中,也在自然外,于是构成了一种“中间地带”,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观赏者、发现者、理解者与研究者。自然不仅仅是生活的来源,更是思想的源泉,哲思的灵感提供者。爱默生1836年写的《自然》是这方面典型的代表,也是“中间地带”概念的提倡者,尽管在其字里行间并没有提及。梭罗的《瓦尔登湖》则更是践行了这个概念,对自然美景的描写无不相衬于对人性的评判与思考。哲思是梭罗对于观察自然、研究自然的终极目标。这当然是沿袭了西方文学前人的传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思考方式的出发点是基于一种物质的存在,就梭罗而言,是他自己建造的湖边小屋,一个不可小觑的“中间地带”。就对这种中间地带的迷思而言,马科斯发现,早在1705年有一个弗吉尼亚人罗伯特·比福莱(Robert Beverley)就在自己的著述中大谈特谈野性的自然与人工的“花园”结合的必要,书名叫《弗吉尼亚当下史》。八十年后杰弗逊在《弗吉尼亚笔记》中也大加赞赏这种“中间地带”,称其为“可期盼的、无论从什么角度而言,都是最可持守的做人状态”。显然,在杰弗逊这里,“中间地带”概念上升到了道德的高度,这应与其一生所秉持的“自耕农”理想一致。马科斯进一步阐释道,“中间地带暗含的道德性在富有秩序的乡野意象上可以得到完美体现”,这种“既不荒芜(wild),也不城市化(urban)的景象该是人的最希望的(生活)环境”。自然,所谓“人”应该是“美国人”,而所谓以“中间地带”作为美国式田园风光的意象也多少构成了美国梦的成分之一。
马科斯的分析手法带有些许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的“神话象征”批评的痕迹,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这本著述被认为是在其时发端的“美国研究”的代表作之一。美国文学作品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挖掘美国田园意象的对象。在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哈克与吉姆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的竹筏遭遇蒸汽船的撞击,这被看作是机器对于田园的侵入,吐温并没有扩大这种遭遇带来的冲突,而是让哈克和吉姆继续有机会在大河上自由自在地活动,说明了自然对于机器危害的克服,自然在马克·吐温的时代依然可以起着调和机器带来的危害的作用;但“中间地带”的一头——“人工花园”——随着时间的进程,越来越多地遭遇了种种非自然的侵蚀,这便是工业化过程给美国带来的改变。机器不只是以看得见的物质形象出现,其象征意蕴逐渐渗透到了生活方式中,导致的变化成为更大的隐患,一种以“中间地带”为核心的美国田园理想被破坏的隐患。在马科斯看来,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便是一部透露了关于此种隐患消息的作品。其中描述的东西部的对峙以及金钱与理想、当下与过去间矛盾的角度,隐含了田园意象在工业化时代不可避免地逝去。
马科斯的分析令人浮想联翩。沿着这个思路,往后看可以发现田园理想意象走过的曲折道路。二十五年以后,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田园意象时隐时现,影影绰绰的姿态或许并不会给读者留下太深的印象,但是细读之后却能体悟其中的深意。主人公霍顿·考菲尔德视周遭世界皆为“虚伪”,唯一可以摆脱的办法是逃遁,而远走高飞的方向则是北上或者西去,无论去哪儿,在其脑海里萦绕的图景不是森林便是隐居,与“中间地带”意象不谋而合。可惜与可怜的是,这仅仅成为他的谈资而已,作为他表达对世俗不满与愤怒的话语出口。小说题目恰如其分地包含了霍顿心心念念的所想所思,讽刺的是,只不过流于一种语言象征。也许可以说,文学中的田园意象在美国逐渐远去。如果说在马克·吐温那里,归顺正常生活的哈克,不堪道戒之困,最后还是要远走他乡,吐温到底还是给哈克留下了一条出路:自然的诱惑依然可寻可觅。相比之下,在塞林格这里,霍顿也被归顺,但只能在医院里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已,臆想一番向西逃逸,作为疗愈。由工业化而转成消费化的后工业社会文化,如同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言,占领了一切领域,包括曾经未受污染的“自然”与“无意识”。飞地已不存在,中间地带的田园理想的结果可想而知。
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的生活似是照旧拥抱中间地带田园风光。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里,蕾切尔·卡森开篇就描述了这么一幅景象:
美国中部有一座小镇,一眼望去,镇上所有生命都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共生。小镇四周是一大片茂密的农场,阡陌分明,宛若棋盘,田地里庄稼茂盛,山坡上果木成林。每到春天,怒放的白色花朵覆盖清脆的原野,如流云一般摇曳生姿;秋日里,橡树、枫树和桦树的斑斓亮丽透出茂密的松林,如火光一样灿烂。那时常有狐狸在山间嗥叫,野鹿半隐在秋季的晨雾中,静悄悄穿过田野。(马绍博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人与自然的和谐造就了美丽的环境,“人工花园”与大自然中的生物相依相存,一派田园风光,所谓“中部小镇”,换了一个词语,不经意间替代了“中间地带”。但是,正如卡森在随后的描述中所强调的,这一切正在经历急剧蜕变,树木消失了,狐狸不见了,更可怕的是,小镇上的人一个个莫名其妙地倒下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弥漫在天空中,笼罩在大地上。卡森的这部名作吹响了向污染环境的化学工业的宣战号角,而这位女生物学者和作家则成为文学批评与创作领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生态文学的肇始者和主要推动者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引描写其实是基于她的文学想象,但是也确实指向了很多美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真实生活,直到她在书中所强烈批判的化学工业制造的杀虫剂等的广泛使用给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原本在文学想象中渐行渐远的田园理想,在卡森笔下被做实了,而且更基于科学的依据。于是,文学描写的现实意义以环境关切的名义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张扬,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获得了干预生活的力量,给在后现代大众文化流行的气氛中愈加处于边缘地带的纯文学带去了诸多新鲜血液,于现实主义文学而言,让其活力倍增也许有点夸张,不过,文学边界得以扩张确应是事实。
在美国,环境正义以及为此目的而斗争的行为早已经成为主流叙事。但是曾几何时,有人开始对这种主流叙事提出疑问,怀疑起其合法性的存在。在2013年出版的《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和阶级》中,作者克里斯蒂娜·沃利从一个人类学家的角度,讲述芝加哥东南部后工业化时代的状况。此作不只是一个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融入了大量关于自己家庭历史的叙述,从她的祖辈到父母亲这一代,特别是她的父亲作为典型的工业化高涨时代的工人代表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因此,这是一部掺入了强烈家庭情感的学术著述,而在表述手段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文学描写特征,类似于卡森的作品。不同的是,对于后工业化下的这个地区的美国人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从环境角度而言,沃利明确表示了一种深深的忧虑,甚至是怀疑。简单而言,因去工业化而带来的环境变化值得吗?“尽管环境更干净了,但我强烈怀疑,许多芝加哥东南部的居民会像我父亲一样,绝不愿意因失去工厂而付出这样的代价”(200页)。芝加哥东南部曾经是世界上最多的钢铁厂聚集地,在十九世纪后期后,沿着密歇根湖发展壮大,世界各地的移民来到这里寻求美国梦的实现,包括作者沃利的祖辈。炉火通红,烟囱林立,煤灰遍地,曾是这块地区的普遍景象,而工人们则从早期的为生存拼死讨生活到后来逐渐争取到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待遇,工人阶级在这里成为一个含有尊严的身份。撇开身份不谈,这个过程实际上会让人联想到马科斯讨论的“花园里的机器”问题。工人住宅区依旧会有花园,但机器的力量则早已淹没了花园的芬芳,“中间地带”哪里可寻?卡森所描述的“美国中部”小镇,落实到地图上,恰恰就包括了芝加哥钢厂这一带区域。工业化过程带来的环境恶化确实是抹不去的印迹。沃利的父亲患上了肺癌,或许与自己抽烟有关,但很有可能与吸入钢厂的煤烟脱不了干系,沃利自己在还不到三十岁时就得了子宫癌,尽管那个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老家,但也不得不怀疑起从小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带给她的隐藏的祸害。但即便如此,为什么作者还是提出了另一种怀疑?
其实,这不是作者的怀疑,更准确而言,是作者替其父亲那样的工人们长期在心中压抑的怀疑发声。用失去工作换来环境的改善,值得吗?看起来一个逻辑分明的问题,其实背后串联起一系列复杂的东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个地区的钢厂陆续倒闭。去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但理论家们所说的消费社会并没有在这里发生,繁荣远离此地,失业后的工人难找工作。更加糟糕的是,曾经由尊严作为主要支撑因素的工人阶级身份也一并如烟云消散,而这正是“值得吗”这个问题须直面的最重要的内核。抽离了“尊严”的工人阶级,其身份犹如抽去了空气的气球,只剩下一层皮囊。这又让我们想起马科斯笔下的中间地带田园风光的意蕴,从比福莱到杰弗逊再到马科斯自己,美国式的中间地带田园理想不单单是表现了与自然亲近的人居欲求,更重要的是,蕴含了一种自在自由自为的精神追求。就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实际的现实情况,杰弗逊的自由“自耕农”大多也只是一种口号,但至少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嵌入很多美国人的心灵之中,成为美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沃利要揭示的正是这个问题。芝加哥东南部地区的工人们失去了他们的生活目标和精神支柱,换来的环境变化在多大意义上能够弥补他们不再能够恢复的过往?
情况其实还要复杂。沃利继而问道,工人阶级为什么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从事对个人和家庭健康有害的工作,要么失去工作但拥有更健康的环境?为什么不能同时拥有两者?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针对的不只是沃利笔下的芝加哥密歇根湖边区域的美国,而是扩大到了整个美国中东西南部纵横交错的广大区域,所谓铁锈带区域。也是曾经的工业化蓬勃发展的景象,也曾拥有沸腾的岁月,之后废墟一片,铁锈斑斑,更不用说,其实环境的改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空壳的厂房依旧随处可见,被工业化污染的土地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修复。沃利谈到了当地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但依然要面对开发商的再次土地利用计划,从中得到利益的会是什么人?作为一个集体概念而言的工人阶级还能重生吗?再者,环境在再次开放中一定能够得到保护吗?比如,把旧时的厂区改造成垃圾掩埋场。附近的居民或许会看到花园般的景象再现,但是他们的心能安宁吗?这是一个人与环境间关联与冲突的大问题,“自然”在这里早已失去了席位,“人工花园”或许依然可以随处可见,但“中间地带”估计难以寻觅,田园风光顶多只能是存在于文字中的理想。沃利这本书主标题的英文是: Exit Zero (中文意译为“无地可存”),原指当地一条高速路出口的标识。字面意思是“零出口”,显然沃利用“零”来表示环境与人的生存和生活(包括阶级身份维持)间的一种纠结关系。出口为零,这象征了什么?
沃利似乎无解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回响。文学新人苔丝·甘缇的第一部小说《兔子窝》荣膺2022年美国全国图书奖。小说的地理背景就是铁锈带,具体方位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市镇。这是一部叙述方式很有后现代风味的小说,由几个不同的故事构成,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不同人物最后互相间形成了某种关联,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是他们都与一个叫做维卡维尔的地方有关,一个典型的铁锈带地区。老鼠的数量要比这里的人口多,而穿梭在野草丛中的棉尾兔则要比老鼠更多,从数量上可以一比的还有犯罪率,包括抢劫、偷窃、强奸、吸毒等。此城上了“美国十个正在死亡城市”的名单,这大概不会让太多的人感到惊讶。不过,也要看到,其中或许有夸张的因素在,因为开发商、投资方与市政府正在拟定一项“城市复兴计划”,把这个地方描述得悲惨一点也许更能赢得关注,对计划的推行有利。但是对普通人而言,无论计划是否能够得到执行,他们窘困的生活是每天要面对的现实,汽车的油费要等到下周的薪资下来才能解决,简陋公寓房里住的有未成年的年轻人,也有七十多岁的老年人。后者曾是这个地方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如同其他铁锈带地区一样,这家名叫左恩的汽车厂曾是美国的骄傲,是美国汽车行业从无到有到领先世界的代表。不同的是,它的衰败史发生得更早,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走向了一蹶不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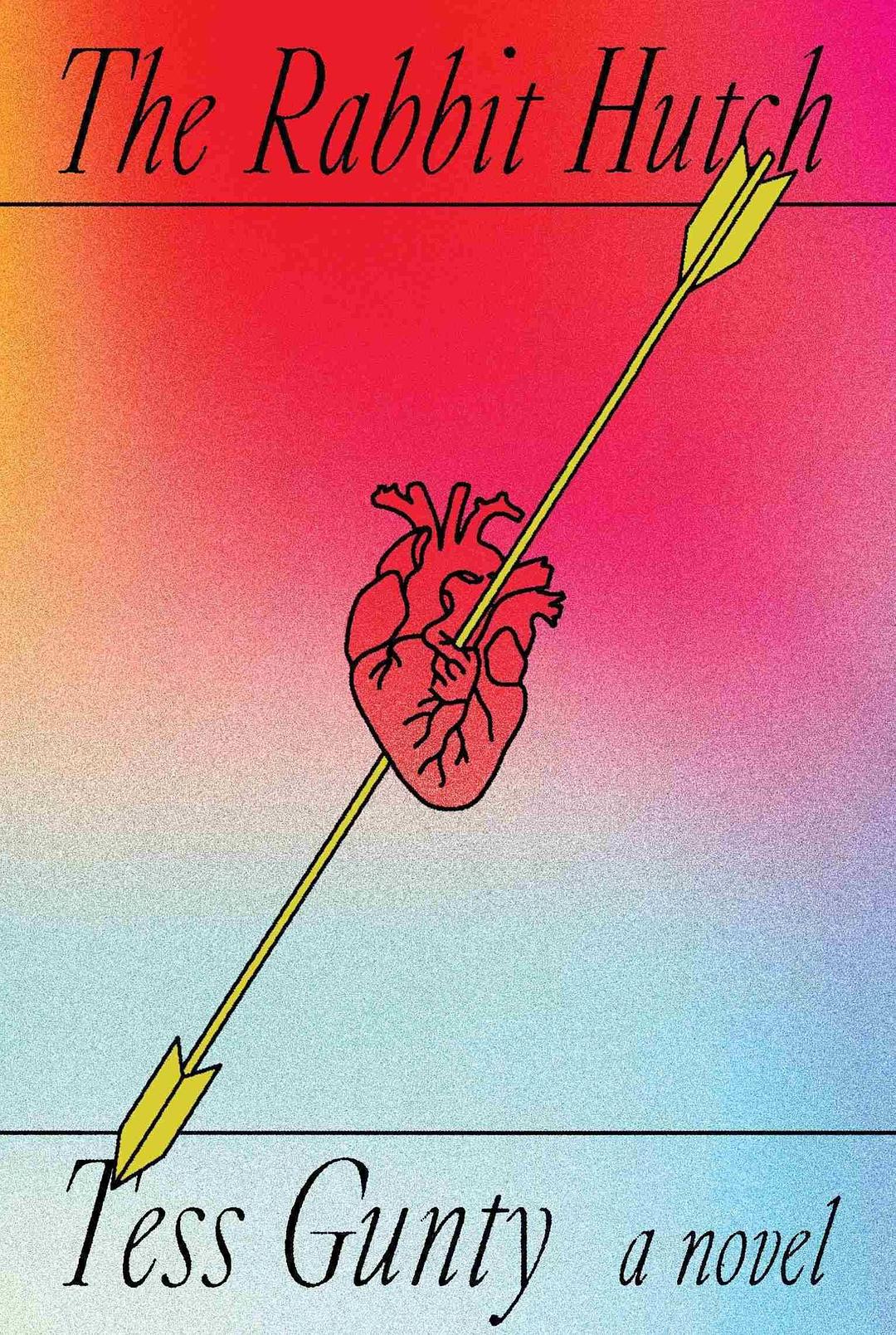
The Rabbit Hutch,[美] Tess Gunty著,2022年8月版
与沃利的非虚构作品可以比较的是,这部虚构作品同样也对所谓的复兴计划表示了怀疑。正当计划制定者们举杯庆祝时,餐厅的天窗突然爆裂,一堆污秽物从天而降,落到满桌的美酒佳肴上。人们有理由猜测这是一帮环境保护激进主义者的抗议行为。但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反对一个据说可以改善环境,甚至重现“中间地带”田园风光的复兴计划?原因可以从谁能从中得到利益这个简单的答案中找到。复兴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一个高档开发区,从世界各地招引一些创业者。当地人自然是被排除在利益获得的外围。但是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正如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女孩布兰汀的眼睛所看到的那样:“垃圾满地,但这算不上什么,只是创造了一种虚无的氛围。空的工厂,空的社区,空的许诺,空的面孔。空的感觉弥散开来,传染到了这里的每一个居住者。”(245页)这种空无感的情绪才是引发抗议者极端行为的背后原因。复兴计划能消除当地人的空无感吗?计划制定者言之凿凿,信心满满,恰如本地市长所言,这正是“表现了美国的精神”(31页),仿佛美国梦的复兴就在眼前。但是,如同沃利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芝加哥东南部工人阶级的身份困境,甘缇在这部小说中也触及了美国社会的阶层结构问题,特别是小说所聚焦的穷白人阶层。小说的题目《兔子窝》的象征意义直指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如同“兔子”,还集聚在一起。小说用很大篇幅写了一个伪浪漫故事,十七岁的中学生布兰汀与她的音乐教师间的不伦之恋,乍一看似乎与小说的背景没有多大关系,细想之下会发现他们都来自相差不大的同一阶层,只是音乐教师攀上了富家之女、左恩公司的后代。从布兰汀的角度,小说对欺骗了其青春梦想的男教师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十几岁女孩表现的逻辑之严密,语言之犀利,思想之深刻都让人刮目相看,从近年来的社会背景来看,再现了“米兔”的暴风骤雨般的批判精神。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男教师对女孩的甜言蜜语的许诺,又何尝不能看成是复兴计划者的话术翻版?
布兰汀是一个孤儿,从小就寄居在不同的家庭里。空荡情绪之于她似乎并非不正常,所幸她还可以去城镇边上的山谷,与自然的亲近带给她一些莫名的安慰。山谷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用其对照镇上环境的恶劣,也会让人起了遐想,“中间地带”田园风光的恢复或许还有可能。但很快作者让这种想象荡然无存。布兰汀在山谷里救了一只受伤的小山羊,把它抱回“兔子窝”里的居室,与她同居一套房间的三个男孩协同作恶,要杀掉山羊。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方式向布兰汀示爱并从网上获得足够的流量。不出意外,最终的受伤者是布兰汀。这个情节貌似荒诞,但如果我们把山羊视为自然的象征,更准确地说,是人工自然的象征,因为山羊是被人工施放在山谷,用于清除疯长的野草,那么这颇带传统意味的与自然和谐的行为在这个荒诞情节中被击得粉碎,至少从象征意义而言。
从象征美国的“田园风光”意象,到“中间地带”概念的道德寓意的深化,再到对“花园里的机器”的矛盾的揭示与焦虑,从文学的象征描写到对现实中环境问题的拷问与行动干预,再到对环境与生活水平下降间的关系的质问,以及对阶级身份消弭带来的情感困境的疑惑,一条逆写环境的路线隐约可见,背后反映的是历史在这块曾经的“新世界”土地上镌刻的弯弯曲曲的沟壑,这条路线会指向哪儿,有出口吗?有意思的是,《兔子窝》开篇说的是布兰汀要“脱离她的身躯”,用的英文词就是exit。在甘缇这里,取其动词之意,在沃利那里,用的是名词。不管怎样,都是一个词,意味深长。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