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希望医生带着个人情感为你诊疗吗?
也许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医生应该冷静、客观、理性,诊疗过程不应该掺杂个人情感。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医生对你的痛苦无动于衷,只是“客观理性”地检查、开药,你会不会觉得他/她过于冷漠?一个边做手术边和护士轻松交谈的医生和一个满脸严肃甚至让病人也跟着紧张起来的医生,你更愿意相信哪个?对于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医学生在医学院接受的教育,要求“医务人员对患者只能同情而不能动情,应当将自己的感情与患者的感情分开,在情感上保持中立。”(王明旭、赵明杰,2018)但显然,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中立”,因为感情本身就意味着“主观”和“非理性”。所以,与其玩“同情”或“动情”的文字游戏,不如首先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医生只是一群掌握了医学知识和技术的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医生要面对自己的情绪。比如:如何处理自己的厌恶、恐慌、焦虑,让它们不会影响对患者的诊疗?如何对待自己犯的小到微不足道,大到导致患者受到伤害的错误?如何面对患者的质疑甚至起诉?如何不让行政事务磨灭心中的医学理想?……
纽约大学医学院临床学教授丹尼尔·奥弗里(Danielle Ofri)在《医生的愧与怕:情感如何影响医疗》(What Doctors Feel: How Emotions Affect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中描述了医生常常要面对的七种情绪状态。奥弗里曾在美国最早的公立医院——贝尔维尤医院——担任内科医生近30年。在经历了从医学生到住院医生再到主治医生的身份转变之后,她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日常观察加以总结梳理,让我们看到了“白衣天使”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也提供了一些解读情感的新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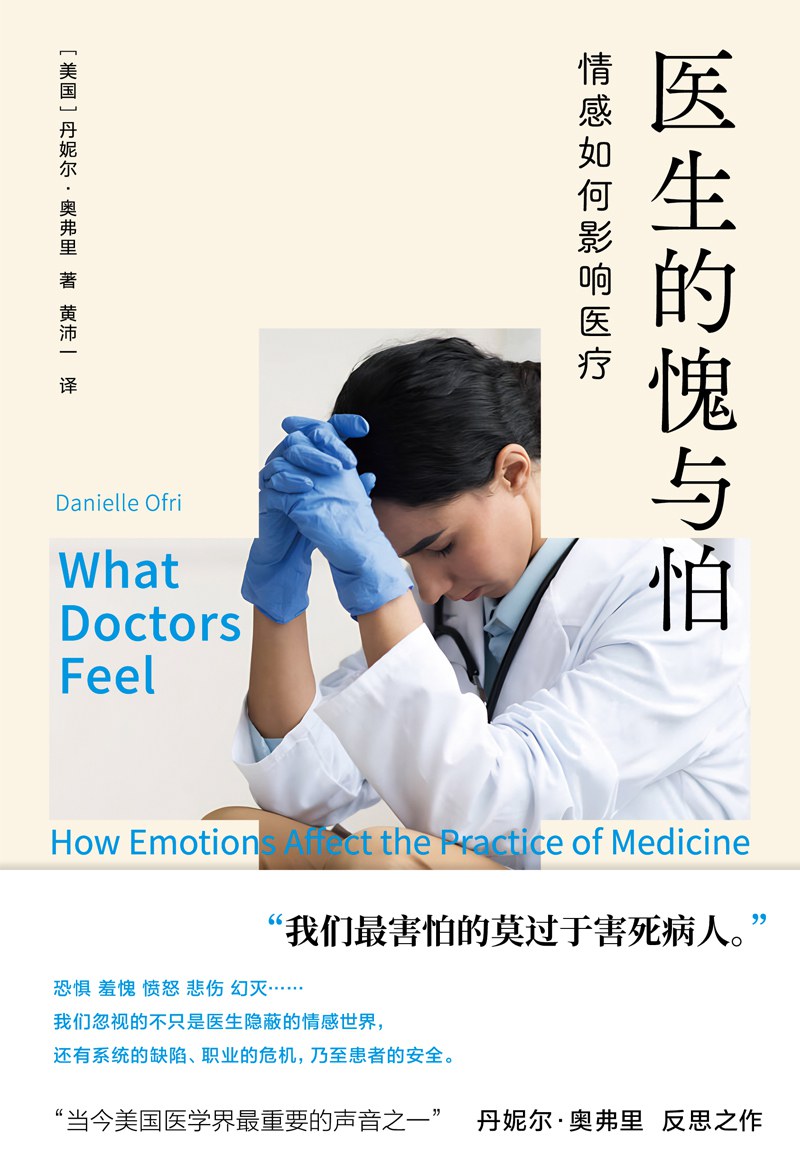
一、嫌弃:愿我在患者身上只看到痛苦,别无其它
奥弗里在第一章就毫不避讳地记录了自己从嫌弃、厌恶到坦然面对脏兮兮的病人和他们身上感染化脓的伤口的过程,真实反映出自己从医学生到合格医生的转变。其实,类似的情节常常出现在电视剧里:第一次上解剖课的医学生,第一次看到命案现场的年轻警员,或者第一次面对灾后惨状的志愿者……巨大的视听触嗅觉冲击让人眩晕、呕吐甚至昏厥。但最终,他们成长为合格的从业人员。这并非因为他们得到了什么法宝,只是因为工作职责使然。
除此之外,当接诊一些成瘾或肥胖的患者时,尽管医生明白先天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许仍不免将这些疾病的成因归咎于患者本身的懒惰、放纵、贪婪和消极。比如瘾君子,也许这样的人在其所生活的社区只是个不招人喜欢的邻居,但对于将勤奋、自律作为基本品质的医学生来说,这样的病人实在很难被同情:首先,他一手造成了自己当下的痛苦;其次,他占用了医疗资源;最后,是病人放弃了自己,又怎能强求医生尊重和理解他以及他所遭受的痛苦呢?
当卡雷洛第57次被送进医院的时候,所有接诊医生都显得麻木,甚至跟诊的学生们每日查房到此都感到不耐烦。因为患者是一个“放纵”的瘾君子。但奥弗里决定挑战一下自己。于是她别出心裁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卡雷洛先生,你能否告诉我们,具体在什么时间知道自己上瘾了?
在场的医学生们本以为这个脏兮兮又坏脾气的瘾君子会拒绝回答,或者根本记不得这种问题的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卡雷洛清楚描述出自己当时的状态、心情、正在做的事以及突如其来的毒瘾让他的人生从此转向了一条不归路。这让在场的每个医护人员都不禁将自己代入到那种束手无策的状态里。这次的谈话让大家对这个已经入院近60次的患者终于有了一点点了解,而这也成了共情的起点。之后大家不再嫌弃他,还频繁找他聊天。“这些必定无法在一夜之间根除他多年的毒瘾,但如果没有共情,他的病情想要好转基本无望。”奥弗里写道。
二、共情:了解得病的病人,比了解病人的病更重要
奥弗里发现,医院里会发展出一套“医学语言”。它不是医学专业术语,而更像是某种私下里的“黑话”。比如给病人起外号,或者调侃某个人的病情。有些笑话开得不合时宜,如果被公之于众,无疑会成为医患冲突的导火索。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其实是医生们缓解压力并让自己共情的能力不被日常琐事消磨掉的一种方式。
医学生在入学宣誓的那一刻起,就应当树立救死扶伤的远大理想,然而随着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实际参与治疗、终于可以做医生做的事之后,共情的能力却可能非但没有被激发,反而受到了严峻挑战:越坚持自己的医学理想、完美主义和职业责任感,就越要面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妥协。因为高压的工作环境难免让医生“把每一个新入院的病人当额外的负担,把每一个病人的需求当作完成工作的又一个阻碍,把每一次与病人的闲聊当作睡眠时间的减少。所以在临床医学的世界里,共情会被击倒”。 (奥弗里,2024)
这让我想到自己有个刚刚轮转到儿科实习的同学,抱怨说自己经常刚把书放在桌上,低头系鞋带的工夫,书签就被不知道哪家小宝贝给顺走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她已经丢了3、4个书签。这让她非常不理解:小朋友不懂事,难道家长也不管吗?
但医生们仍然要共情,因为这对患者来说非常重要。奥弗里引用了一项面向242个医生和20000多名糖尿病患者的调查,其结果显示:共情能力高的医生,其病人罹患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概率比共情能力低的医生低40%,几乎可以媲美高强度糖尿病药物治疗所达到的效果。她还引用了著名的加拿大病理学家威廉·奥斯勒爵士的话:了解得病的是怎样病人比了解病人得了什么样的病重要得多。
三、恐慌:是压力也是动力
每个人都会面对恐慌,恐慌的内容可能是投资失败、计划流产、失恋或其他对将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这就是生活中的悖论,正如在《拒斥死亡》这部经典存在主义著作中,贝克尔所说的那样:“人之处境的讽刺在于:最深刻的需要是要摆脱死亡和毁灭的焦虑;但是,是生活自己唤醒了这种需要,因而我们必须从充分的生的状态退缩回来。”(恩斯特·贝克尔,2001)
医生当然也要面临恐惧的情绪。但在医生眼里,上述这些都不足以和生命相提并论。奥弗里认为,医生对伤害病人的恐慌是一种“笼罩我们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东西”。她第一次在临床上独立面对某个心搏骤停的患者时,整个人都被吓呆了。住院医师给她汇报了病人的病史和现状,但她的大脑却因为恐慌而成了一团浆糊。幸好另一位高级研究员出现在现场,才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几十年过去了,她仍然对当时自己的所作所为(或者说“不作为”)而感到羞愧。
医生往往要面对垂危的病人,而对死亡的恐惧并不会因为身上的白大褂而烟消云散。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医生必备的心理素质,只有这样才能让医生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谦卑。确实,恐惧和其他情绪一样,没有好坏之分。对于医生来说,恐慌不仅包括在日常护理中对于是否有所遗漏的低级焦虑,也包括紧要关头的高度紧张。适当的恐惧对医生和患者都有益处,是患者在接受诊疗时候的某种生命保障。但如果医生被恐惧击垮,那么患者的生命安全同样也将受到威胁。
医生和患者都要意识到自己的恐惧,但医生要主动面对它,解决它。这可能是医生的一项重要技能,也是医患关系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医生只可以恐,不可以慌。
四、悲悯:悲伤和哀恸永远不会离开医疗,也不应该离开
如果说每个职业都避免不了受到某些伤害的话,那么对于医生来说,“伤心”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创伤。
奥弗里采访了一个儿科的同事伊娃,记录了她经历的很多悲痛时刻。比如,垂死的婴儿,哀悼的父母,变成植物人的孩子……有一次,伊娃接手了一个刚出生不久就被诊断波特综合征的新生儿。这对于新生儿来说几乎是必死的恶性疾病,然而这次的新情况是:出于各种原因,父母并不想看到这个婴儿。作为医生,伊娃学习了大量抢救患者的知识和技术,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这一次却只能在储物间看着这个刚刚降生就要离世的女婴在自己手上慢慢停止呼吸,自己无能为力。
在高死亡率的科室中,这种情绪就更加明显。比如奥弗里采访了肿瘤科医生,得到的答案是:悲伤无处不在。这种悲伤不仅来自病故的病人,还来自那些已经确诊并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病人。病痛折磨着患者,而悲伤折磨着医生,这让医生不再与病人进行情感交流。而这样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可能也会让病人更加难过,如此恶性循环。更麻烦的是悲伤带来的过度医疗。一个“失败”的死亡病例可能会影响医生未来的治疗思路,让他们过度治疗接下来的患者,或者为了避免患者遭受更多痛苦而采取更加保守的治疗方案——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是医患双方所不愿看到的。
哀恸贯穿在日常的医疗工作中,而这不是医生可以凭借一己之力独立承担的感情负担。奥弗里列举了美国医疗界做出的尝试:通过支持小组、会议和心理疏导等方式,医生们向工作人员倾诉自己的情绪,大家一起为病人默哀。应对悲伤没有完美的公式,但悲伤引发的辛酸也许可以成为医生治疗下一个病人的动力。哀恸也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生命观和健康观,很多医生在哀恸中找到力量、加倍投入医疗事业中。这需要医生和周围世界共同努力。
五、羞愧:反思错误,成为更谨慎、更优秀的医生
医学生很容易产生羞愧感。比如周围的人都在忙着抢救病人,而刚刚接触临床的你却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这就足够让一名医学生感到沮丧。就更不要说因为自己的失误而让伤害了患者的身体、精神或哪怕仅仅是浪费了对方的时间。
每个人都会犯错,医生只是一群掌握了医学知识的普通人,出错不可避免。大众却往往对医生更加苛刻,似乎医生的错误很难被社会接受。对患者和家属来说,错了就是错了;但对于医生来说,为了避免同样的错误再犯,就必须要勇敢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奥弗里在她的另一本书《当医疗出错时:一位医生的痛与思》(When we do Harm: A Doctor Confronts Medical Error)里专门讨论了“犯错”的问题。为了避免犯错,美国医院曾借鉴航空领域的“错误表格”,在医疗操作过程中逐一勾选,以避免漏掉或重复操作某个关键步骤。但即便如此,错误仍然不可避免。错误来自于护士的意见未得到重视,或医护人员沟通不当,甚至可能因为医院内网的操作系统不够合理,或者其他任何看似不起眼却最终导致严重后果的细节。所以,让医生自己身陷愧疚并独立承担错误的后果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这样也不能避免错误的再次发生。
她引用了1999年美国医学研究院发表的开创性报告《犯错乃人之常情》。在这份被视作现代患者安全运动的创始文件里,强调了让医疗系统变得更安全的方法在于加强系统性工作,而非仅仅在错误发生之后指责犯错的医生。同时,立法也显得很重要。奥弗里认为,“尽管法律不能消除患者和家属的情绪,但我们仍然应该用法律来保护那些承认错误并道歉的医生,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医生站出来承认他们的错误或险些造成的伤害。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奥弗里,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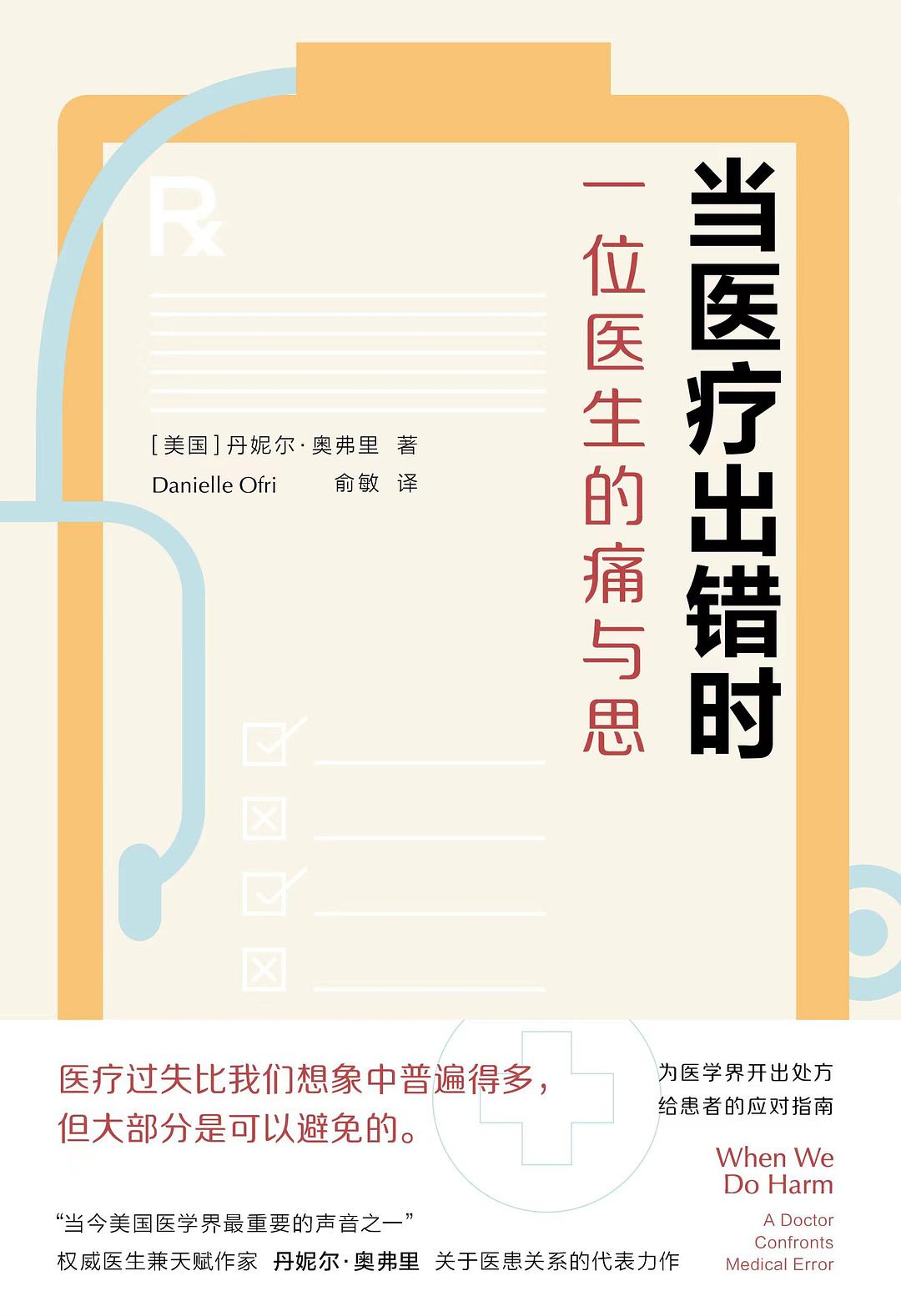
六、沉沦:当医学理想幻灭之后,谁来救助医生
病人不会只在医生上班的时候才生病,这使得医生这个职业在很多时候成了一份24小时全天候的工作。我们很难要求一位会计师或律师免费为客户提供工作时间以外的服务,但医生如果也这么“斤斤计较”,在工作时间以外“见死不救”,就难免被社会大众指责为失职。所以,当电话响起的时候,即便你在睡觉,或等待接送子女上学,或自己身体不舒服,大多数医生也会选择面对召唤而非视而不见。
奥弗里在书中举了琼安医生的例子来说明医生在职业生涯里面对的困境。琼安是一名优秀的急诊科医生。为了工作,她成了单亲妈妈,一边疲于面对无休止的加班,一边还要独力照顾年幼的孩子。她尝试过调换到一些不那么忙碌的科室,但医学理想让她最终回到了急诊的岗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酒精成为她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她开始依赖酒精,只有在酒后她才能享受到片刻的放松与惬意。终于有一天,她醉醺醺地出诊,被领导及时叫停,并因此丢了工作。
医学理想的幻灭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丢掉工作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一种。对于很多医生来说,即便他们还没沉沦于香烟、酒精或药物带来的虚幻享受中,却也和曾在医学院里不断提升知识的那个自己相去甚远。连续工作24小时甚至更久之后,谁还有心思去听讲座、了解医学界最新动态呢?奥弗里发现,普通内科医生的离职率高于专科医生,因为医疗行政体制对前者要求更多,而后者有权选择自己的患者。即便没有药物滥用,压力本身也会对医生造成伤害,并使他们效率降低,甚至发生医疗事故。
这同样不是可以依靠个人力量解决的问题。奥弗里关注到佛罗里达医院的健康计划,即由心理学家介入,为医生提供及时的咨询服务,并在行政方面对医生“网开一面”——其实仅仅是把例会的时间推迟十五分钟,就可以让很多医生有时间吃上午饭。
七、失望:我救了他,却得到了“差评”
在《医生的愧与怕》的最后一章,奥弗里以一个家庭医生的例子提出了一个看似与医学无关,但却与医患关系息息相关的问题:信任。
这名家庭医生曾接生了一个脑瘫婴儿,之后与这个家庭保持了长达20年的良好的医患关系,没想到在孩子即将21岁时候(也就是诉讼时效即将到期的时候)被这家人以医疗事故为由起诉,说由于她的不当操作导致孩子脑瘫。医生感到崩溃,不敢相信20年来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背后竟然是虚情假意。她猜测或许是出于经济原因,比如父母担心自己去世后孩子没有经济来源,才出此下策。但无论如何,这都让医生感到沮丧和难过。
医疗诉讼对医患双方都有伤害。对患者来说,诉讼即意味着患者预后不良;对医生来说,诉讼带来的情感伤害会导致医生为保险起见而在之后的治疗中采取更加保守的方式。与此类似的评判医生的方式还有很多,除了医院内部的会议和质量指标之外,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给医生打分也成了很多问诊平台的内容。当然,这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医生,鞭策其提升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但医术难以被量化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如果一个医生业务娴熟但不善言辞,宁愿把精力放在治病而非解说病情上,那么尽管治好了病,却难免得到患者的差评。这是让人无奈的现状,应该如何解决,作者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本书的另一条主线是关于一位需要心脏移植的女性患者茱莉亚的故事。茱莉亚是非法移民,不能被列入到器官移植名单中。但奥弗里和同事们想尽一切办法帮她争取机会,并最终让她成功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这个历尽千辛万苦救人性命的故事最终却仍然以悲剧收场:尽管接受了心脏移植,但由于茱莉亚由于大脑和血管不能承受一颗健康的心脏所供应的血流而在术后突发中风,最终离世。这个故事让我们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医患双方不能共同努力,那么患者将命悬一线;但即便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死神也仍然会挥着它的镰刀带走脆弱的生命。所以,医生的努力到底有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或许,医生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1. [美] 恩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林和生 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
2. 王明旭、赵明杰主编:《医学伦理学》(第5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9月
3.[美]丹妮尔·奥弗里:《当医疗出错时:一位医生的痛与思》,俞敏 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3月
4.[美]丹妮尔·奥弗里:《医生的愧与怕:情感如何影响医疗》,黄沛一 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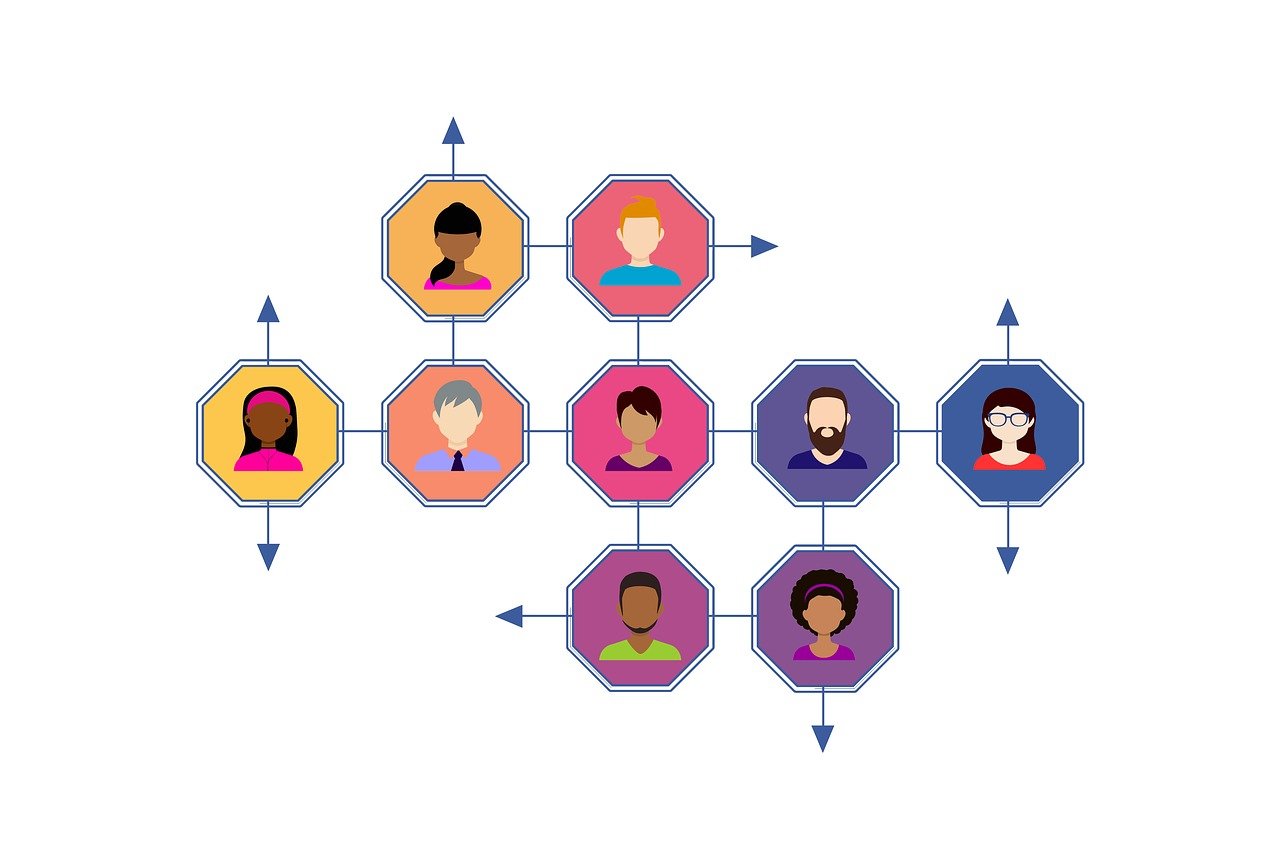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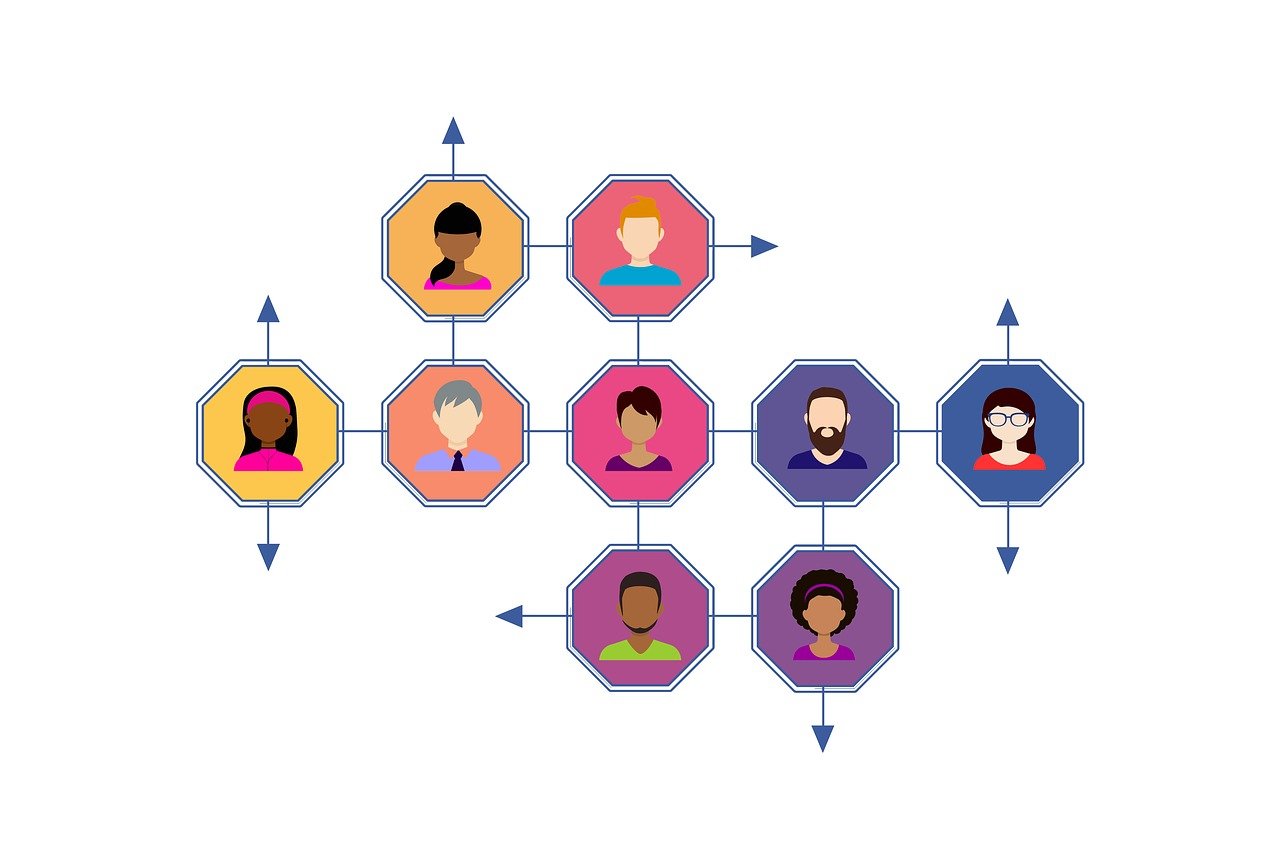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