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皮埃尔·布迪厄的《学术人》是一部揭示学术界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的作品,探讨了学术界的社会结构和学者的社会位置,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学术研究和学术人的职业生涯。布迪厄认为,学术界并非一个纯粹的知识和真理追求的领域,而是一个充满权力斗争和利益交换的社会场域。学者们在其中争夺资源、地位和认可,而这些争夺往往受到他们的出身背景、教育背景和个人关系网络等因素的影响。作者还通过具体分析指出,学术界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的整体结构紧密相连,学术界的层级和分布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结构。他强调,要理解学术界的运作,就必须超越表面的学术成果,深入探究背后的社会力量和文化资本的运作机制。本文摘自该书第一章《一本“焚书”?》,澎湃新闻经新行思授权发布。
他们不想书写历史学家们的历史。他们很想穷尽一切历史细节。但他们并不想亲身踏入历史细节的无限之中。他们不愿处于历史序列之中,就像不愿生病或不愿死去的医生。
——夏尔·贝玑,《金钱(续)》(L'Argent, suite)
若是把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世界当作研究对象,我们就不得不在一种可以称为戏剧性的形式之下,遭遇某些根本性的认识论难题,它们与实践知识和学术知识之间的差异问题有关,并且尤其与某种特殊的困难有关,这种困难既来自与原初经验(expérience indigène)之间的断裂,也来自以此断裂为代价而得到的知识重组。我们知道,过度的接近或疏离都会阻碍科学知识的获得;我们也知道,要建立这种曾被中断又被修复的邻接关系非常困难——为此,不仅需要研究对象付出长期工作的代价,对研究主体而言也是如此。而这种邻接关系,也使我们能够纳入所有因我们身处其中才知道的东西,以及所有因我们身处其中而不能或者不愿知道的东西。但我们也许不太清楚,为了传递关于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而做的努力,尤其是书写形式的努力,也会使诸多困难涌现,而这在举例说明时尤为明显:这种修辞策略的目的本是“使人理解”,但它通过刺激读者回忆自身经验,也就偷偷让读者将一种不受控制的信息加入了他们的阅读之中。这一策略将会带来几乎无法避免的后果:它会使科学性的建构降至一般知识的水平,而我们获取前者,正是为了避免后者。同样,一旦我们引入某些专有名词(noms propres)——并且当该领域的关键目标(enjeux)之一即是“让自己出名”(se faire un nom)时,我们怎能完全放弃这一做法呢?——就有可能会鼓励读者把被建构的个体降格为某个具体的、各种要素相互混合的个体。而被建构的个体只存在于理论空间之中,它体现了“由其属性明确定义的集合”和“依据同样的原则去描述其他个体属性的集合”这两者之间相同或相异的关系。
但是,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以去除所有可能影响日常逻辑运作的标记(notations),都将是徒劳的。如今,那些流言、诽谤、中伤、抨击文章或是小册子,往往会被伪装成分析,它们不浪费任何一桩逸事、任何一段俏皮话、任何一个词语,只是为了得到中伤他人或博人眼球的乐趣。哪怕我们像在本书中一样,系统性地避开那些众所周知的纠葛,即学术界同媒体之间的公开接触(liaisons déclarées),或是那些历史学家以名誉担保要去披露的秘密关系(liaisons cachées)——不论是家庭关系还是其他关系——我们都免不了会被怀疑进行了某种揭发活动(dénonciation),但实际上应对此负责的是读者:正是读者,在字里行间的阅读中,通过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填充分析的空白,或者只是“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通过考虑自己的情况”,便改变了经过有意审查的科学调查的价值与意义。社会学家缺乏能力去写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而那些最敏锐的读者所知道的往往比社会学家还多,甚至会披露社会学家们的“揭发活动”,但读者们的认知处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中。所以社会学家的研究是有一定风险的,他有可能显得像在迎合那些最久经考验的论辩策略,例如影射(insinuation)、暗示(allusion)、半截话(demi-mot)、言外之意(sous-entendu)等学术修辞尤其钟爱的方式。然而,比起由知名或不知名的特殊主体的所作所为组成的逸事性叙述(新旧历史学是如此心甘情愿地去迎合这种叙述),被社会学家简化的没有专有名词的历史并不更符合历史真实:该场域结构必然性的各种效应,只有通过个体关系明显的偶然性才能实现,而这些关系既建立在由共同的相遇和交往在社会层面所铺展的偶然性之上,也建立在各种习性(habitus)的相似性之上,这一相似性则被体验为同感或者反感。如果说,通过充分利用从属关系——这种关系使人们把通过科学调查的客观技术所收集到的信息与从亲缘性中所获得的内在直觉结合起来——所固有的优势,而使我相信某种东西正是历史行动的真实逻辑或是真正的历史哲学,却发现这种东西在社会层面上无法得到证明和检验,这怎会不让人遗憾呢?
因此,社会学知识始终处于这样的状况之下:通过一种致力于逸事和个人细节的、“有利害关系的”解读,它很有可能被理解为某种粗浅之见。并且,由于缺乏抽象形式主义的制止,这种解读会使那些为学术语言和日常语言所共享的词汇降格为它们的一般含义。这种几乎不可避免的片面解读会招致一种错误的理解,它建立在对所有定义了何为科学知识的东西的无知之上,即对解释性系统结构本身的无知。这种解读破坏了科学建构所创造的东西:它把已经分离的东西又混合起来,尤其把被建构的个体(individu construit)与经验的个体(individu empirique)混淆起来,而前者(无论是个人或机构)只存在于科学研究所制定的关系网络之中,后者则直接将自身纳入一般直觉。这种解读也消解了所有使科学客观化区别于常识(connaissance commune)和半学术知识(connaissance demi-savante)的东西。从大多数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种半学术知识,与其说是解密,不如说是愚弄与欺骗。它几乎以一种我们可以称为忒尔西忒斯(Thersites)式的观点作为准则: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ïlus et Cressida)中,忒尔西忒斯正是那个充满嫉妒、一心想要诽谤伟大人物的普通士兵。抑或,若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马拉(Marat)式的观点,我们忘记了马拉也是,或者说首先是一个糟糕的物理学家:怨恨会带来简化,简化的需求则会让清醒变得片面,并会导致一种天真的历史目的论(finaliste de l'histoire)观念,这种观念无法触及各种实践的隐秘原则,它只是揭发了那些表面责任者的逸事,并最终夸大了某些人物的重要性,他们被假定为发起了某些应当被谴责的“阴谋”,而且是一切可鄙行为的厚颜无耻的始作俑者,并且这些行为本身的重要性首先也被夸大了。
此外,还有一些人处在学术知识和常识的边界上,诸如随笔作家(essayiste)、记者、记者型学者和学者型记者,他们最大的兴趣在于模糊这一边界,并且把那些实际上牵涉整个场域结构的各种效应,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个游说团体(lobby),例如某位文学电视节目主持人,或是与《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周刊有关联的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的成员们,从而否认甚或取消了科学分析与片面的客观化之间的区别。他们在阅读本书时,会沉溺于单纯的好奇性解读,并使各种例子和特殊案例按照流俗的八卦或文学小册子的逻辑运作,从而会把为科学所固有的系统性和关系性的解释模式,降格为最普通的、论战式的手段,即通过诉诸人身的论据(arguments ad hominem)而进行的特定解释(explication ad hoc)。
读者们会在附录3中找到对授予新闻界以声望之过程(甚至可以说是诉讼)的分析。此分析的首要目的,是揭示所有诉诸人身的揭发的天真性:在使这场游戏客观化的幌子下,这些揭发仍然全面参与其中,因为它们试图以进行分析为表象,来服务于与它们在该游戏中所处位置有关的各种利益。文学排行榜的技术主体既不是某个个体中介(这里指的是贝尔纳·皮沃),无论他多么有影响力,多么老练;也不是一个特定机构(电视节目、杂志);甚至不是那些能够在文化生产场域(champ de production culturelle)施行某种权力的新闻机关的集合;而是构成这一场域中各种客观关系的集合,尤其是那些建立在生产者的生产场域和大规模生产场域(champ de grande production)之间的各种关系的集合。科学分析所得出的逻辑,远远超越了最明智、最有力的行动者(他们被指定去寻找“责任者们”)的个体性或集体性的意图或意志(阴谋)。也就是说,最大的错误,便在于从这些分析中提取论据,以解除每一个行动者都身处其中的客观关系网络的责任。与那些试图在社会法则的陈述中,为自己的放弃行为寻找某种宿命论或犬儒主义式的托词,并将那些陈述视为命运的人相反,我们必须记住,提供理解、甚至是辩解方法的科学解释,也可能让改变发生。对支配着知识分子世界的机制的进一步认识,不应该(我有意使用这套含混的语言)使“个体从道德责任性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就像雅克·布维尔斯所担忧的那样。与之相反,这种认识应该教会每个个体,如何在自由之中承担责任;如何坚定地拒绝一切最微小的松懈与软弱,它们使个体的全部力量屈从于社会的必然性;如何在自我和他者身上,与机会主义式的冷漠或不抱任何期望的盲从主义作斗争,否则它们就会给予社会世界它所要求的东西:对一切微不足道的小事的顺从奉承和屈从同谋。
我们知道,各种团体都不喜欢那些“告密的家伙”,当违抗或背叛是他们所倚仗的最高价值时尤甚。对这些人而言,如果客观的工作被应用在外部、敌对的团体时,他们会毫不吝啬地称赞这一举动是“勇敢的”或“明智的”;与此同时,他们却会怀疑,在分析自己所在的团体时,是否一定需要某种特殊的清醒。学徒巫师会冒着风险,寻找当地的巫术与崇拜,而不是前往遥远的热带寻找使人安心的异域魔法,他定会预料到,他引起的暴力会反过来与他对抗。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很好地阐述了这样一条法则:如果客观化的应用对象在社会空间(espace social)中处在更远的位置,那么客观化便更有可能在“亲属的圈子”中被承认和称赞为“勇敢的”;在由他创办的杂志《火炬》(Die Fackel)的创刊号中,克劳斯表明,谁若是拒绝远距离批判所带来的乐趣和易得的利益,专心于一切都被视为神圣的眼前环境上,谁就应该早早预料到“主观上的迫害”所带来的折磨。也正因此,我借用了中国异端思想家李贽的著作《焚书》(Livre à brûler)作为本章标题。他之所以给自己这本自毁式的著作取了这一名字,是因为他在其中揭露了学阀的游戏规则。我们不是为了挑战这些人:尽管他们会迅速谴责所有真正的焚书行为,却想“焚毁”一切在他们看来亵渎性地攻击了他们自身信仰的作品。我们只是想说明,当小团体的秘密泄露时,会有某种矛盾烙印其中,并且这种矛盾之所以让人如此痛苦,是因为最隐私之事的公布(哪怕只是部分的),也带有某种公开忏悔的性质。
社会学并不足以产生某种幻觉,使社会学家在某个瞬间自认为扮演了解放英雄的角色。然而,尽管如此,社会学家的确有提供某种自由的可能性:他可以动员一切可用的科研成果,试图将社会世界客观化,而并非像人们有时所宣称的那样,采取某种暴力还原或总体支配的手段,尤其是当他的研究对象追求客观化,却不想被客观化时。社会学家至少可以期盼,他那饱含学术激情的论著,不管对别人还是对他自己而言,都可以是一种社会分析的手段。

《学术人》,[法]皮埃尔·布迪厄著,王睿琦、钟牧辰译,拜德雅|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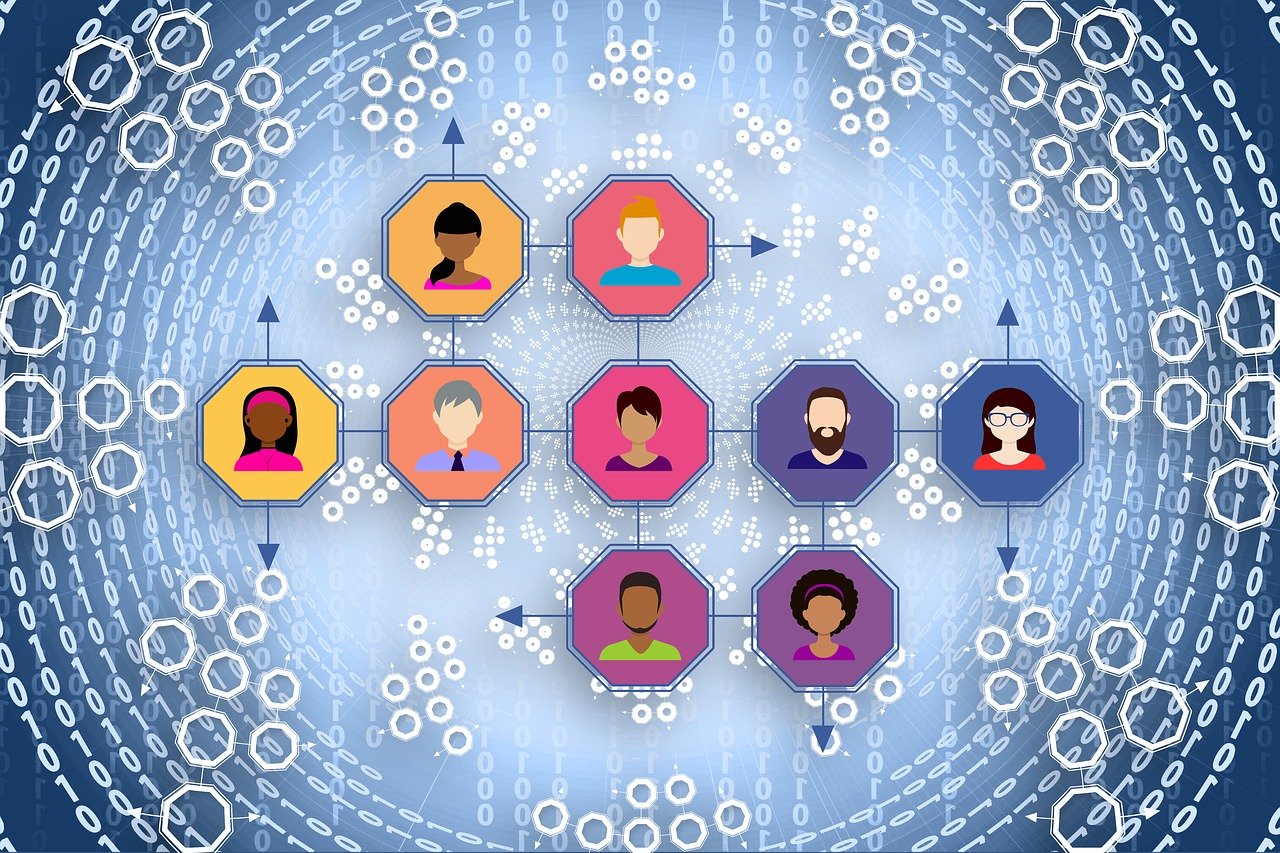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