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不见的城市》里,马可波罗对忽必烈说,“人在旅行时会发现城市差异正在消失,每座城市都与其他城市相像,它们彼此调换形态、秩序和距离,形态不定的尘埃入侵各个大陆。”
这段话其实代表着卡尔维诺自己的意见。作为游客,抱怨城市的千篇一律是上个世纪以来才兴起的流行话语,然而必须承认,出于各种原因,我们确实很容易发现某个城市的某个街角跟其他城市的某个街角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在研究经济学的朋友们眼里,城市的趋同性是必然且必要的。
有天傍晚,我从地铁站往朋友公司走,被导航带入一个小小的步道。步道在一片绿地和一堵墙之间,像极了现代小区的内部路。
顺着这堵私立幼儿园的围墙,穿过这片不大但精致的街心绿地,眼前赫然出现一条破落的窄巷子。巷子宽不足一米,两边是倚着老建筑搭出来的层层叠叠的简易房屋。再往不远处看,某座知名的写字楼正闪耀着低调的霓虹灯。此时,这条安静的、低饱和度的巷子如此寂寞,好像是被遗忘在了这里,也像是被造物主放错了位置。
正当我站在原地犹豫要不要走下台阶,闯入这片安静的时候,一辆黄色的外卖电瓶车从我身后疾驰而来,很快消失在巷子尽头。
我带着好奇和一丝丝歉意,走下台阶,走过每一扇敞开和紧闭的门。
巷子实在太窄了,房子面积实在太小了,只需要经过门口或窗子的时候随意一瞥,这屋里的所有人、所有家当便尽收眼底。真是对窥探欲的极大满足啊,我满怀歉意地想。
与其说是一条巷子,这里更像一个老弄堂。公用的水龙头和水泥台子暴露在户外,可以想象半小时之后的喧闹:一些人洗菜、一些人洗衣,或说笑或争吵。
一台老式双桶洗衣机正在路边工作,从我看到它到我走远,它一直在有节奏地转动,发出并不很响的轰隆声——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脱水的声音一定撼天动地,就像小时候我爸妈的那台洗衣机。一位老阿姨倚着水槽,认真看着洗衣机里的漩涡,若有所思。我低头快速走过,很怕惊扰了她。
我以同样的速度经过一扇敞开着的门,房间被一个上下铺的床和一个餐桌挤满,穿着红色背心的男人躺在下铺背对着门,并不很薄的被子盖到腰部,女人在帮他擦身体。上铺堆满了衣服和杂物。
隔壁是一个杂货店,门口堆着油漆桶、劳保鞋、雨衣雨伞和几捆被压扁的硬纸箱。透过门帘,可以看到房间里摆着饮料的货柜,和一张麻将桌。电视机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播着某个省的新闻。
巷尾这家扬州扦脚店应该是新开的,雪白的墙上没有什么装饰,门外灯牌一闪一闪的,显得有点着急。隔壁的老式理发店倒像是开了很多年的样子,喷绘的门头有点褪色,卷发老板娘坐在镜子前玩手机。
从朋友公司出来,我又走进这条巷子。扦脚和理发店依然没生意,电视机还在响着,那个帮男人擦完身体的女人坐在餐桌前发呆。洗衣机不见了。
我走上台阶,最后回头看一眼这里,近处的阁楼里,一个长发女人在不慌不忙地收衣服叠衣服,像是在等人回家。屋子里有暖黄色的光,她黑色的影子投在窗上。除了那个呼啸而过的外卖骑手,我再没碰到其他路人……
这条巷子并非这个城市的典型面貌,但借用国木田独步《难忘的人》里的话说,却是一道独特的、“难忘的风景”。
城市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城市里每一扇门、每一扇门后面的人,才是城市的真正面目。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大概也很难说踏足过这里的每一个街区。更多的情况是,在不经意间闯入某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惊叹这个熟悉的城市里还有如此陌生的风景,于是,早已消失殆尽的对这个地方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再次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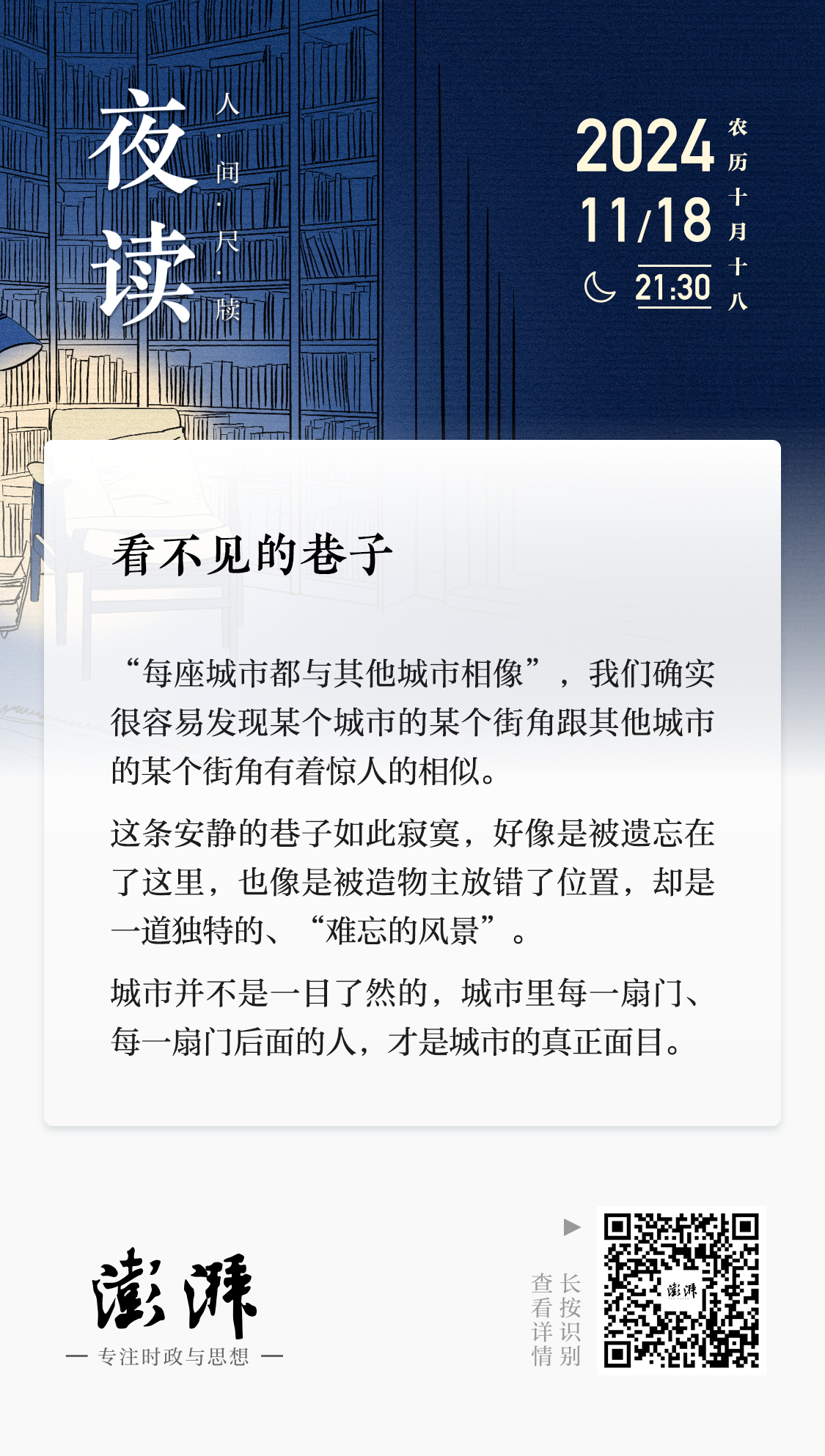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