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艺术小史:从史前岩画到当代艺术》是一本艺术史入门书。作者夏洛特·马林斯讲述了从洞穴绘画起源,到印象派、立体主义等流派轮番登场,再到当代艺术百花齐放,成为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的历程……本文摘自该书,原题为《艺术家的坚持》。澎湃新闻经理想国授权发布。

1878年11月26日,美国人詹姆斯·阿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昂首阔步地走入伦敦的法庭,手中挥舞着手杖。这位四十四岁的艺术家,留着一头卷曲的黑发,戴着单片眼镜,身着紧身外套,脚踩漆皮鞋,显得格外潇洒。这一天是惠斯勒诉罗斯金案审判的第二天。他起诉了约翰·罗斯金的一篇负面评论,前来法庭捍卫自己的声誉。(他申请了1000英镑的赔偿金,而且确实需要用这笔钱来偿还日益增长的债务。)
罗斯金此时已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惠斯勒的最新展览狠狠批了一通。罗斯金长期以来一直倡导认真研究自然,看到惠斯勒的作品《黑与金之夜景:坠落的烟火》(Nocturne in Black and Gold: The Falling Rocket)后,他感到愤怒难抑。这幅画描绘了泰晤士河上空烟火绽放的瞬间。
他称惠斯勒为“狂妄自负之徒”(coxcomb),并激愤地指出,惠斯勒竟敢“向公众脸上泼一罐油漆,要价200基尼(约合今15000英镑)”。然而,惠斯勒绘制《黑与金之夜景》的目的并非追求写实。他想捕捉的,是火花在夜空中绘就的图案和那个夜晚的氛围。只不过,罗斯金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
惠斯勒走上证人席时,法庭内座无虚席。罗斯金已委托总检察长约翰·霍尔克爵士(Sir John Holker)为他担任辩护律师。霍尔克费力地审视着惠斯勒的画作,竭力想要理解它们。“您用了多少时间创作这幅《黑与金之夜景》?”他问道,“您多快画完的?”陪审团笑了起来。惠斯勒配合着回答:“可能几天就画完了。”霍尔克认为自己已经将惠斯勒逼入了绝境:“这就是你要价200基尼的劳动?”惠斯勒回答道,不,那是他一生知识积累的价值。掌声随之响起,惠斯勒仍然对胜利抱有希望。

詹姆斯·阿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黑与金之夜景:坠落的烟火》,1875年
惠斯勒最终的确打赢了这场19世纪最著名的诽谤官司,但他没有获得1000英镑的赔偿,赔偿金只有一个法寻(farthing),相当于四分之一便士。更糟的是,他还需支付自己的诉讼费。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表面上大功告捷,实际上却损失巨大。只能说明,法官对这两位成功人士为了几句话而争论不休的行为已经不耐烦了。审判对两人都造成了损害,但惠斯勒失去了一切:他新修的日式住宅“白宫”(White House)、里面的家具、他收藏的版画和瓷器,以及他特别建造的画室中的画作。他破产了。
惠斯勒出生于美国,但童年的一部分时光是在俄罗斯度过的,当时,他的父亲正在为俄罗斯的新铁路网提供咨询。后来,他先后在美国和法国学习艺术,汲取了两个国家不同的艺术氛围。惠斯勒与前拉斐尔派艺术家交好,最终定居英格兰,成为英国唯美主义运动(Aesthetic movement)的领军人物。参与这一运动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认为,颜色、形状和线条本身即可创造出美丽和谐的作品,无须依赖具象的主题。他们的信条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
惠斯勒对日本艺术中的和谐之美深有感触,并将其融入西方式的油画创作中。他的肖像画多是以白色或灰色为基调的习作,而他笔下的河景则营造出简约的灰色、蓝色和黑色的氛围。他的艺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绘画从对现实世界的描绘转移到对绘画语言本身的探索。他就像一位用音符和音调来创造情绪和氛围的古典音乐家(而非演唱流行旋律的歌手)。正如惠斯勒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所言:“大自然蕴含了画作的所有元素,无论是色彩还是形式,就像键盘包含了所有音乐的音符一样。但艺术家天生就是要去挑选和甄别……直到他从混沌中创造出辉煌的和谐。”他的作品为20世纪初的艺术家带来了信心,鼓励他们走得更远,完全摒弃具象主题,创造出西方艺术中最早的一批抽象画作。
在美国东海岸生活和工作的艺术家们,其艺术风格则与同代人惠斯勒迥然不同。温斯洛·霍默(Winslow Homer,1836—1910)描绘的是人们在经历了1861年至1865年残酷的内战(超过60万军人在这场战争中阵亡)后所渴望的美国风景。出生于波士顿的霍默曾接受过版画训练,并为著名杂志《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报道过战争。但他很快便放弃了战争的题材,转而描绘乡村生活的怀旧场景。在19世纪70年代漫长的经济衰退期,他笔下的人物却在骑马、游泳、钓鱼、学习航海,如1873年至1876年创作的作品《微风徐徐》(Breezing Up),原名《顺风》(A Fair Wind)。在1876年的《吃西瓜的男孩》(Watermelon Boys)中,三个男孩正享用偷来的西瓜,其中一名男孩拿着长长的西瓜皮,紧张地向左侧望去,充当了望风的角色。另外两个男孩则趴在地上,尽情地大快朵颐。霍默通过描绘黑人和白人男孩一起玩耍的场景,暗示了一种与当时美国的现实相去甚远的种族融合程度。尽管奴隶制已经于1863年废除,但美国社会的种族隔离问题依然严重。
来自费城的托马斯·埃金斯(Thomas Eakins,1844—1916)试图向美国人展示,肤色深浅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在他1875年创作的作品《格罗斯诊所》(The Gross Clinic)中,著名外科医生塞缪尔·格罗斯(Samuel Gross)在一群求知若渴的学生面前解剖一名男子的腿,这展示了埃金斯在解剖学方面的训练成果。画面中,四名男子正在协助这位外科医生。格罗斯一手拿着沾血的手术刀,一边向学生讲解他是如何切除一块坏死的骨刺,以挽救患者的腿使其免遭截肢的。这种高度写实的手法令许多人感到不适。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百年纪念展览”(Centennial Exhibition)甚至拒绝让这幅画参加,理由是它暴力、丑陋而淫秽。在格罗斯的争取下,这幅画最终得以展出,但也只是挂在医学馆的墙上。它被作为一幅外科手术插图来展示,而不是作为一幅描绘人体内外结构的肖像画。
埃金斯坚信身体的平等,他观察黑人和白人的身体特征时几乎不带偏见。如果说美国的平等之战主要集中于种族问题,那么在俄罗斯,斗争的焦点则是阶级问题。1861年,也就是美国总统林肯宣布废除奴隶制的两年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Tsar AlexanderⅡ)将所有农奴从农奴制(一种奴隶制形式)中解放出来,但他们的生活依然异常艰辛。俄罗斯的艺术家们越来越感到他们有责任创作具有社会目的的艺术。于是,十三名艺术家脱离了主导俄罗斯艺术界的圣彼得堡艺术学院——一个依然推崇新古典主义的学院。这群人自称为“巡回画派”(Wanderers),因为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小城镇举办展览,将他们现实主义、表现民族文化的艺术带给人民。惠斯勒仅仅为自己的名誉而战,而巡回画派则为受压迫、受迫害的人们奔走呼号。
伊利亚·列宾(Ilya Repin),原名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Il’ia Efimovich Repin,1844—1930)。乍一看,他似乎不太像一个巡回画派画家——他曾在巴黎待了三年,正逢印象派画家聚集的时候——但在1878年他也加入了这个团体。他成了一个重要的成员,受到其他艺术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高度赞赏,并多次为后者画肖像。就像法国的库尔贝一样,列宾和其他巡回画派画家用他们的艺术来评论社会,描绘了最低收入者的苦难,如列宾1870年的作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Barge Haulers on the Volga)。在他1884年的大型画作《意外归来》(They Did Not Expect Him)中,他描绘了一位纳罗德尼克(Narodnik,意为改革运动人士)被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后返回家中的场景。这个男人静静地站在客厅里,仍然穿着外套,像一个陌生人。他的脸几乎隐藏在阴影中,眼睛犹如漆黑的空洞。他的孩子们看向他,仿佛他是个见所未见的奇人,没有认出他。只有他的母亲穿着寡妇的服装,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向他。光秃秃的地板暗示着,他不在的日子里,一家人的生活是多么艰难。
艺术家们为何选择描绘这样的人物?巡回画派想要将这些人物带入光明,赋予他们声音,就像法国的库尔贝曾经所做的那般。他们也想要纪念这些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意识到,现代世界正在逐渐湮没那些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的传统。为了在这些古老的生活方式消失之前将其捕捉下来,艺术家们沿着新铺设的铁路前往陆地与大海交会的边境地带,如布列塔尼的蓬塔旺(Pont-Aven)、荷兰的赞德福特(Zandvoort)和英格兰的纽林(Newlyn)。这些沿海村落提供了实惠的住宿和丰富的素材——渔夫和渔妇、身着传统服装去教堂做礼拜的村民,以及如诗如画的乡村环境。这里远离了印象派画家所痴迷的现代城市生活的喧嚣,让艺术家能够捕捉更加传统的生活方式。
伊丽莎白·福布斯(Elizabeth Forbes),原名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1859—1912),是一位出生于加拿大的艺术家,在前往蓬塔旺和赞德福特之前,她曾在伦敦和纽约学习。1884年,她创作了《赞德福特的渔女》(A Zandvoort Fishergirl)。画中的年轻女子站立着,一手叉腰,右臂托着一个装着鱼的托盘。福布斯将她置于一面毫不起眼的墙前,让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她坚定的目光上。她直视着我们,清晨的阳光在她的发丝和围裙上映射出一层光晕。
福布斯的母亲陪同她一起四处旅行,后来她们一同定居在英格兰康沃尔郡的纽林。在那里,她的画室里堆满了渔网。正是在康沃尔生活期间,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斯坦诺普·福布斯(Stanhope Forbes,1857—1947)。斯坦诺普在1884年到1885年间创作的《康沃尔海滩上的鱼类卖场》(A Fish Sale on a Cornish Beach)是一张展现沿海生活繁忙场景的生动快照。渔船抵达靠岸,渔获即将被拍卖。画面中,两位年轻女子的脚下散落着鳐鱼、鲭鱼和其他鱼类,她们正在与一名须发灰白、戴着防风帽的渔夫交谈。其他妇女肩扛着装满渔获的沉重篮子,灰色的波浪拍击着她们的脚。斯坦诺普·福布斯的作品在伦敦展出后,很快人们就相信存在着一个“纽林画派”(Newlyn School)。斯坦诺普和伊丽莎白创立了一家美术馆,现称为纽林美术馆(Newlyn Art Gallery),还创办了一所绘画学校。纽林画派为该地区强大的艺术影响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许多法国艺术家选择不去国外旅行,因为他们意识到,艺术领域一些最令人激动的新动向就发生在他们的家门口——巴黎。印象派画家描绘这座首都,并于1886年在此举办了他们的最后一次展览。展出的作品包括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1859—1891)在1884年至1886年间创作的《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A 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La Grande Jatte),这幅画采用了一种开创性的新风格。修拉使用了与印象派相似的科学色彩理论,但对其进行了颠覆。他意识到,如果将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会得到一种新的颜色,例如将红色和黄色混合,会形成橙色。但是如果你在画布上不混合这些颜料,而是交叉涂上红点和黄点,让颜色在你的眼中混合,会怎样?如果在这些点上叠加覆盖互补色的点,让颜色更加耀眼生动呢?结果便是《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一幅超过3米宽的巨幅画作。

乔治·修拉,《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1884—1886年
大碗岛是巴黎市郊塞纳河中的一座大岛。在修拉的画中,一对中产阶级夫妇穿着周日的盛装,直挺挺、一本正经地站在树荫下,凝视着波光粼粼的河面。他们周围有宠物猴和宠物狗,孩子们在奔跑,妇女们在制作花束,工人们在放松身心。评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Félix Fénéon)赞叹不已:“画中的氛围异常清澈,充满活力;画作的表面似乎在微微颤动。”修拉使用点彩来绘制整个画布和画框。画框上的红色点彩与画中的草地相邻,使绿色表面显得更加跳跃和闪烁,仿佛它是活的。相比之下,画中人物显得静止而毫无生气。他们大多是以侧面形象示人,仿佛浮雕带上的人物,独自坐着或站着,孤立在自己的一片阴凉处,这也反映了现代城市生活的枯燥无味。
修拉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风格,被称为点彩派(Pointillism),标志着与印象派的彻底决裂,并激励了许多追随者。费内翁称赞它是一场新艺术运动的开端,并将其命名为新印象派(Neo-Impressionism)。他认为这是对印象派所描绘的“瞬时表象”的否定,并体现了捕捉场景永恒本质的愿望。追随修拉的艺术家,我们现在称之为后印象派画家(Post-Impressionists):凡·高、高更、塞尚。他们的作品跻身世界上最受推崇的艺术品之列。然而,在有生之年,他们几乎没卖出过几幅画。缺乏来自公众的支持,他们对艺术的献身有时是危险,甚至致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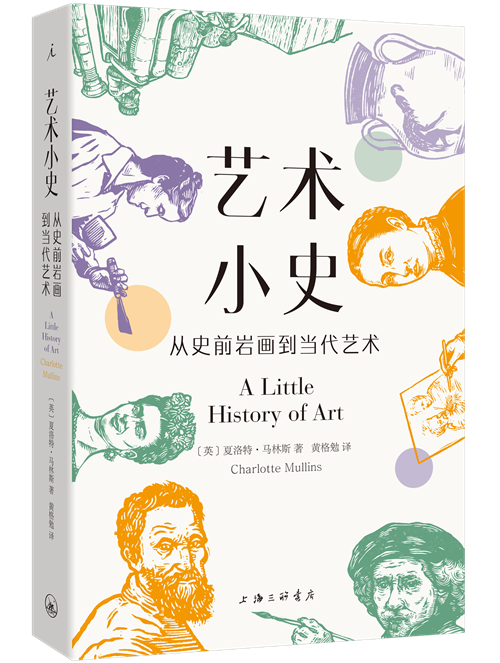
《艺术小史:从史前岩画到当代艺术》,[英]夏洛特·马林斯著,黄格勉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