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英国布克小说奖于11月12日晚在伦敦颁发,包括华人作家李翊云在内的六位奖项评委,一致将选票投给了英国小说家萨曼莎·哈维(Samantha Harvey)的“太空田园诗”《轨道》(Orbital)。评委会主席埃德蒙·德瓦尔在公布得奖小说之前表示:“作为评委,我们一心要找到一本打动我们的书……那是以思想为栖息之所、而非对问题发出宣言的小说,它并不是为寻求答案,而是会改变我们想要探索的问题。”

萨曼莎·哈维
生于1975年的萨曼莎是今年5位最终入围的女性作家之一,《轨道》是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只有132页,也是布克小说奖史上篇幅最短的得奖作品之一。萨曼莎学哲学出身,毕业后曾旅居日本,2009年出版首部小说《荒野》(The Wilderness),并入围布克小说奖初选名单。在获得今年的布克奖之前,萨曼莎的小说已多次获得英国多项文学奖提名。她唯一的非虚构作品是《无形的不安》(The Shapeless Unease),写的是她当时患上失眠症的经历。萨曼莎如今在巴斯大学教创意写作,其创作的散文和书评作品常见诸英美主流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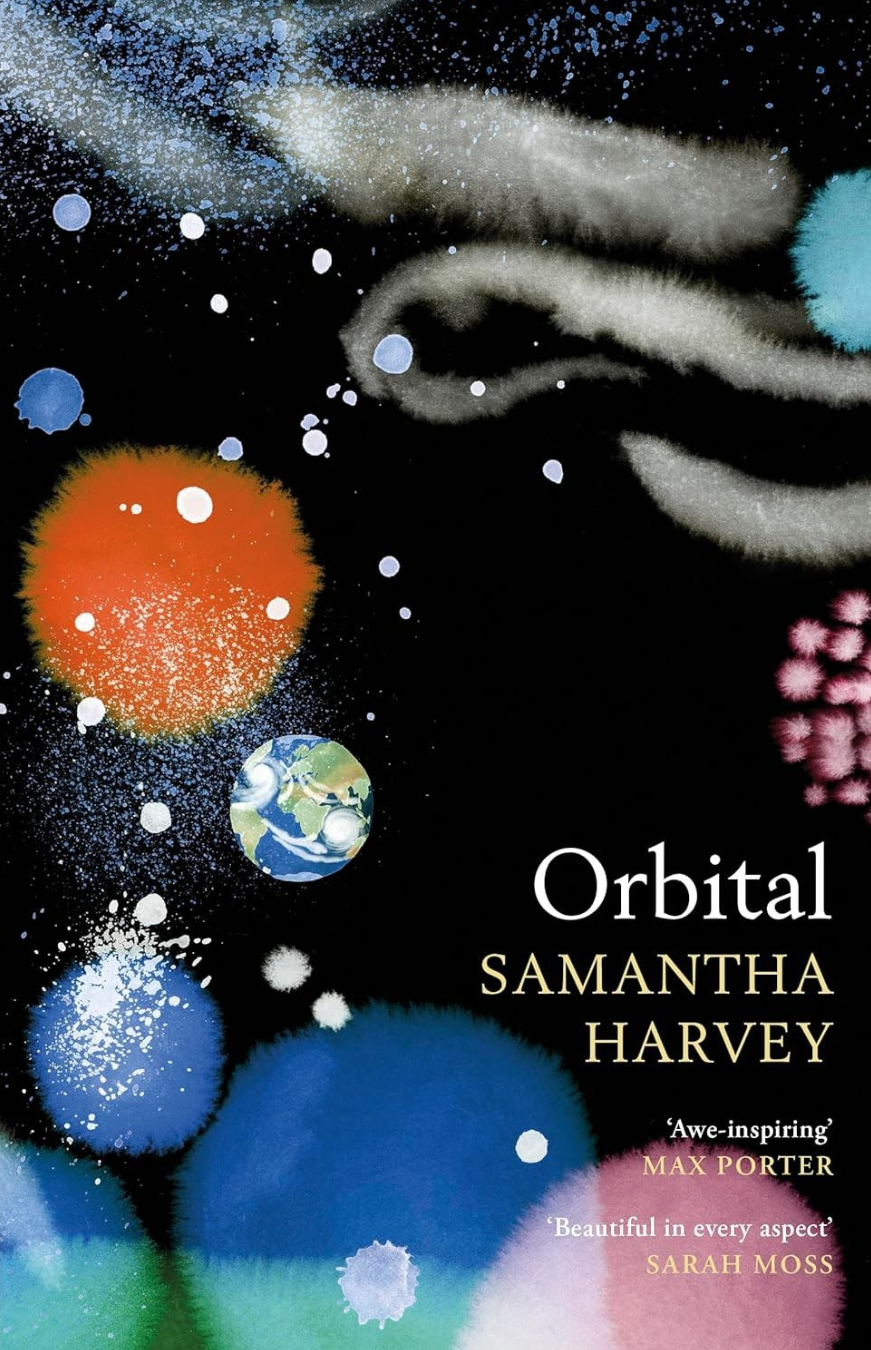
《轨道》书影
《轨道》的故事设在空间站上,六位不同国籍的宇航员需要在离地球250英里(约402千米)之外的近地轨道上共处数月,书中角色包括两位俄罗斯宇航员安东与罗曼,美国人尚恩、意大利人皮埃特罗、英国人内尔和日本人千惠。各人是彼此赖以生存的依靠。他们不停绕着地球飞行,每天看16次日出与日落。各人自己的故事穿插全书。
皮埃特罗与内尔安装了一套地球辐射测量系统,“它在航天器绕行地球时,扫过七十公里宽的地带,从一个大洲到另一个大洲,南北移动,像一只执着的眼睛在观察、收集、校准光线。”彼埃特罗每天都会想着光谱仪,想通过它确定地球是否在变暗。“它的镜头朝向三个方向——地球、太阳和月亮,测量反射自地球表面和云层的光线。”“地球表面在变暗,那是因为空气中的污染物颗粒将太阳的光反射回太空;如果冰盖融化和高亮云层减少,意味着更多的太阳光被地球吸收,那则是在变亮。”
皮埃特罗出发前,他十多岁的女儿问他:你认为进步是美好的事吗?是的,他回答道,毫不犹豫。但皮埃特罗接下去说:“你没问进步是不是一件好事。”“人之所以美好并非善良,而是因为活着本身,就像一个孩子。活着,好奇,焦躁不安。别管是否善良。人之美好,因为眼中有光。有时伤人,有时自私,而进步就是这样的,本质上是活的。”这个关于进步的提问缠绕了他很久,后来皮埃特罗又想,他本该说:“谁能看着人类对地球的神经质攻击,还觉得它是一种美呢?人类的傲慢。……而这些插入太空的男性象征般的飞船,肯定是最具傲慢的,它们是一个物种因自恋而疯狂的图腾。”
尚恩和内尔经常争持不下:内尔的宇宙是大自然的偶然,尚恩的宇宙是精心设计的艺术品。内尔记得小时候走在树林里,她“从一棵树旁走过,直到意识到那是一棵人造的树,一座由成千上万根枝条粘合、编织而成的雕塑……你无法将它与其他光秃秃的冬季树木区分开,除非你知道它是件艺术品,一旦知道,你便能感受到它所散发出的与众不同的能量和氛围。“对内尔来说,这就是她和尚恩的宇宙之间的区别:一棵生长于大自然的树和一位艺术家之手造就的树。“几乎没什么区别,却又有着世上最深刻的差异。”

书中每一个章节都以轨道的数字分隔开,最终止于一个开放的结尾。小说里充满了大段大段对时间、对“生而为人”的默想,从宇航员独有的“神性视角”而描述的地球景观,例如“北极光在大气层内弯曲变幻,绿色与红色交织,像被困住之物,焦躁而壮丽……”,又如“我们现正生活在生命与意识的短暂绽放中,这只是奋力生存的一瞬,弹指一挥间,这便是一切。这段充满生机的时光更像是炸弹而非花蕾。这些丰饶的时光正在飞速流逝”等等,瑰丽又感伤。布克奖基金会文学总监盖比·伍德(Gabby Wood)提及,《轨道》的文风很容易会令人联想到伍尔芙的风格。
关于宇航员在空间站观看地球的视角,萨曼莎做了各种比照。尚恩带着青梅竹马的妻子送他的第一张明信片,上面是西班牙画家迭戈·委拉斯奎兹的作品《宫娥》:“谁在看谁?画家在看国王和王后;国王和王后在看镜子里的自己;观众在看镜子中的国王和王后;观众在看画家;画家在看观众;观众在看公主;观众在看侍女们?欢迎来到这个镜子的迷宫,正是人类的生活。”而人类这个充满不安全感的物种,永远在凝视自我。
后来,宇航员尚恩准备动笔写下:“在这个太空旅行的时代,如何书写人类的未来?” 然而他又突然意识到,这场空间站的旅行,不啻是“一次动物的迁徙,一次生存的尝试”;“选取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生物,它的故事便是地球的故事。它能告诉你一切,那个生物。整个世界的历史,整个世界的未来。”
在获奖之后后,11月14日,萨曼莎在伦敦接受我的专访。她告诉我,她从来没拥有过手机,在写《轨道》之前,她常翻的资料之中,最实用的是国际空间站(ISS)的维护手册。

【对话】
在英格兰乡间写作《轨道》
澎湃新闻:你大学专业是哲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呢?
萨曼莎:那时我没想好将来要做什么,本来想朝哲学学术方向发展,于是去读研究生,但学着学着发现这根本不适合我,哲学的学术世界太奇怪了。后来我就去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在当地教英语,一边开始陆续写一些短篇小说。然后就决定,赚点钱回英格兰,今后专心写作。但那部小说从没有出版。写了第二部小说才有机会出版。那时我并没有“B计划”,只是庆幸自从我决定全心写作以来,一直很顺利,遇到很多支持和机会。
澎湃新闻:我听说你至今没有使用手机?社交媒体就更不用说了。
萨曼莎:我从来没有过手机,希望以后也不会有,但看来是越来越难坚持下去了。但我对科技也并不是彻底抵触,大部分时间我对科技还是很依赖的。
澎湃新闻:你写作时是用电脑的吧?
萨曼莎:对,虽说我也想拿着本子和笔坐到草坪上,这可是小说家该有的形象,可惜手写稿我做不到。
澎湃新闻:写《轨道》时,你就一直身处乡间,接近自然世界对吗?
萨曼莎:没错,我住在英格兰西南部,在一座老房子里,我的工作室很久没装修过了,比较残旧,冬天还很冷。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写地球
澎湃新闻:开始是怎么设定“太空”这个背景的呢?
萨曼莎:对于在太空里远眺地球的人类体验,我一向十分感兴趣,过去也收集过许多国际空间站以及早期登月宇航员对自己旅行经历的记录。这些哲学化或感伤的视角,提醒了我们这座星球有多么完美,多么瑰丽。到了2019年,有段时间我很想以自然世界为主题,用虚构的方式去呈现我与大自然的关系,写下自己对于自然世界被逐渐破坏的感受。后来有一天,我意识到可以把这两个兴趣点结合到一起,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写地球。“近地轨道”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虽然是在太空,但与地球之间只隔了250英里,因此你从国际空间站无法看到整个地球,只能看到一侧。那是如此亲切而又壮丽的景象。一旦决定了这是我想做的事,那接下来我需要的是一个地点。好的,就用空间站,这个背景当然是以“国际空间站”为基础。一切就从这里起步。
澎湃新闻:书中的意大利宇航员皮埃特罗有一个想法,他认为假如能够离地球足够远,最终就能理解它。
萨曼莎:这本书很大一部分就是从情感出发,源自我从过去延续至今的感觉。当我观看地球的图片和影像,随着宇航员的视角移动,俯瞰地球时,地球好像就在你脚下慢慢消失,接着你会看到那美得不可思议的大气层;然后夜晚降临,迅速铺满了整个星球,一切都太不真实,然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试图表达的就是当我看到这一切时的惊叹。
澎湃新闻:那六位宇航员,你是如何确定他们各自的国籍和性格的呢?我知道部分情节是基于美国和苏联两个舱段而设计的,还安排了“美国厕所”与“俄罗斯厕所”这样的细节,然而与此产生强烈反差的是六位宇航员在空间站内的乌托邦式共处。我还特别喜欢你对俄罗斯宇航员安东的描写:他看片会大哭,也会为了不影响同事前途,刻意隐瞒自己的健康状况。看得出你对人性之善的点赞。
萨曼莎:我很高兴你提到了安东,我写着写着也很喜爱这个角色。小说里面有两位俄罗斯宇航员安东、罗曼,一个意大利人皮埃特罗、一个日本人千惠、一个英国人内尔,还有美国人尚恩。这个人员构成基于“国际空间站”,多少有现实依据。我不想美化宇航员之间的关系,说他们彼此相亲相爱,不分国籍身份。与此相反,当你在太空站,如果你是唯一的英国人,你就代表了整个国家,你会比在家时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民族身份。所以我不是想削弱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而是想强调我们如何能在差异中找到合作的力量,和平共处。我们是怎么聚在一起的,看到彼此的不同,学会互相协商、互相包容。我还觉得,在我小说中的太空站,假设是在国际空间站,人类必须学会好好相处,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不满或者让人烦的事,最终你们都被困在太空里,必须和这些人好好相处。所以我想深入探讨的是,协作和与人为善是多么重要,彼此宽容、彼此体谅,这也许就是我们在地球上该有的生存方式。
“写作期间我并没有跟宇航员交谈过”
澎湃新闻:写本书,估计需要做许多搜集资料等案头研究工作吧?
萨曼莎:是的,在动笔前我做了许多准备工作。2019年动笔,到2022年3月交稿,到去年底出版,中间隔了一年半时间。写作之前,我对太空站的了解很不充分,甚至不知道如何在空间站上定位我的角色。开始写之前,我先拟出所有角色,研究清楚他们需要在什么地方出现、平时需要做什么,理清了我想写的内容,然后就开始写,但在写作过程中我还一直在做研究,直到最后一稿我还不断要查资料。
澎湃新闻:有找过宇航员聊一聊吗?
萨曼莎:写作期间我并没有跟宇航员交谈过,因为我不希望小说角色套用任何一位宇航员的亲身经历。不过,许多宇航员都写过关于太空旅行的书,而且写得很直接、很动人。这一批书我读了不少,不断翻书划重点,从中借用了不少信息和视角。
写作是一种相当“悬浮”的状态
澎湃新闻:当读到飞船开始自由落体时,我心里一沉。六位宇航员是否一直就这样半睡半醒,而我们不会知道结局?
萨曼莎:确实,我想要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结尾,既不是充满希望,也不是绝望,就是开放的,最终结束于一片声响景观之中,读者自行去揣摩。
澎湃新闻:甚至能否理解成是一次关于生存尝试的失败,而暗示地球之于人类的唯一性?
萨曼莎:没错。我们是擅长适应的物种,即使是在一个不太友好、我们不习惯的环境中,比如说地球之外。然而通过在太空中的生活,我们反过来明白了人类与地球的联系有多紧密。我们对地球,无论从生物力学、生理节律、我们的呼吸、骨骼和血液循环中,都有着深深的依赖。然后大家似乎都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想要挣脱这样的联系。我们是好奇而富于创新的物种,这我接受,我们当然想看看外面还有什么,但到火星上生活这个想法,对我来说一直很可怕。
澎湃新闻:差不多到结尾时,俄罗斯宇航员罗曼与同在太空中的陌生宇航员通话,对方说,人在太空,想家、孤独、疲惫这些感觉肯定都有,但垂头丧气是绝对不会有的。我想象在你代入到宇航员的视角中去时,这段描写是不是也能说是你写作时的状态?
萨曼莎:问得有趣。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相当“悬浮”的状态,或许就像你在这个问题中所做出的类比。然而事实是,我在写作中,有时会感到灰心。写作的时候,我整个人会处于一种屏息凝神的“悬浮”状态,与此同时,我也试图将读者置于这种悬浮和屏住呼吸的状态,就像进入一种梦境,或是魔咒。我指的不仅仅是这本书,无论写的是什么,你都在试图不让读者脱离出这种状态,直到整本书的结尾。在那样的“悬浮”状态里,我感到充满力量、内心平静,并且充满信任。我可以完全信任自己写下的内容,即使当时可能看起来还有改善空间,但最终会有解决办法。所以,是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类比。也许可以说,写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写作本身的隐喻。
澎湃新闻:书中的太空生活,虽然每日能观看16场日出日落,但当你代入宇航员的视角去描述单调的日复一日,是否也会像远离地球之外的宇航员那样,有过自我怀疑?
萨曼莎:怀疑自己的创作能力是常有的事,但这回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去写这样一个故事,因为我没去过太空,也永远不会去太空,本质上跟“宇航员”完全是两路人。这种自我怀疑出现之后,我的写作停顿了好几个月。后来回过头继续写下去,也只是因为同时开展的其他小说写作都没找到方向。那段时间我有点迷茫,当我重新翻开《轨道》的书稿时,发现了其中的某些真实感。没错,书里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可当时我的感觉是里面有些情感值得表达。
澎湃新闻:我想起你刚才说,从完稿到出版之间隔了一年半时间,那段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如果有机会,你会补充或改动一些内容吗?换句话说,社会时局跟你写作的关系有多紧密?
萨曼莎: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俄乌战争还没爆发,但那时我已经想写一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裂痕,实际上两者关系在战争爆发前早已开始破裂。“国际空间站”这个项目也快要结束了,一部分原因是它的使用年限快到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关系越变越脆弱。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太空船上才出现了裂痕,国际空间站本身也出现过类似的裂痕,这也是一种象征。我还在小说里加上了“带国籍的厕所”这一小段,用来暗示地球上的某些冲突。但也就到此为止,我不想让小说依附于特定的时间点和日新月异的社会时局。尽管我私底下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观点,但我真不想在小说里深入探讨。与此恰好对立,这本书只想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来看待地球,跟读者说‘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至于读者怎么理解,那是他们的事。我不想写一本过分政治化的小说。
澎湃新闻:意大利宇航员皮埃特罗的女儿向他提出问题:进步到底是不是一件美好的事?你借皮埃特罗之口,在书中呈现了对“发展”的思考与质疑。这估计也是你自己会反复琢磨的问题吧?
萨曼莎:我绝对看得到自己对“进步”在某种程度上的抵触;同时我也看得到这当中的讽刺:我能够在这个富足的世界上健康地活着、我所拥有的一切,完全得益于某处某人的创新精神,得益于他们对“发展”的接受。因此我并不想贬低它,进步确实很美好,一切都离不开进步。但它也很有破坏性、很暴力,能引发不公,甚至危险。然而这就是我们一直所面对的挣扎:正因为有人通过创新带来了发展,我们才有谈论这一切的奢侈。
澎湃新闻:你现在睡眠好吗?
萨曼莎:我已经没有写《无形的不安》那时的失眠症了,但也从来没睡过真正的好觉。不过昨晚(布克奖颁布之夜)睡得挺好的。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