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面临口碑危机的迷雾剧场,总算等来一部救市之作。《漂白》14号下证,17号定档即开播,6小时后热度破6000,24小时破8000,开播五天刷新迷雾剧场历史最高数据,开播六天成为迷雾剧场首部破万剧集。

《漂白》热度破纪录
2002年,雪城发生一起残忍的杀人碎尸案,“犯罪四人组”邓立钢(王千源 饰)、石毕(任重 饰)、宋红玉(王佳佳 饰)、吉大顺(宗俊涛 饰)逃之夭夭,刑警队长彭兆林(郭京飞 饰)开启艰难的追凶之路。

“犯罪四人组”

彭兆林(郭京飞 饰)
邓立钢等人专挑女性下手,作案手法残忍且反侦查意识强。2003年时险些被犯罪四人组杀害的甄珍(赵今麦 饰),死里逃生后成为警校学员。她与彭兆林携手逐渐揭开真相,终于在2011年将“漂白”身份的犯罪四人组绳之以法。

甄珍(赵今麦 饰)
《漂白》何以这么爆?
“大尺度”是一大原因。开局就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分尸案,受害女性被宋红玉用锤子杀害,随后被肢解,尸块还被用粉碎机捣碎倒入马桶,导致下水道堵塞。修理工掏出的竟是人肉和断指。
两年后,罪犯们绑架勒索两名受害女性邱枫(方圆圆 饰)和甄珍,对她们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
他们将受害者囚禁在封闭的空间里,用绳索将她们紧紧捆绑,限制其行动自由,不给她们足够的食物与水,让她们处于极度的饥饿与口渴状态。宋红玉对甄珍拳打脚踢,她反复用锅铲砸向甄珍的脸部,还用老虎钳捏掐甄珍的身体……

锅铲、老虎钳和铁锤
这些大尺度血腥暴力桥段,迅速在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上疯狂传播,成为一个巨大的“噱头”。
客观地说,在悬疑剧扎堆、悬疑剧也越来越卷的当下,“大尺度”的确是一种突围方式。
观众天生具有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很容易对常规剧情兴味索然,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带来强烈刺激与冲击的作品。大尺度的情节设置正好满足这一点。《漂白》通过展现极端残忍的场景,如马桶堵塞下水道后维修人员发现人体组织,瞬间抓住观众眼球,满足观众内心对独特刺激体验的追求。
从剧情呈现角度看,犯罪悬疑剧中的大尺度场景极大地增强故事的真实感与冲击力。《漂白》对犯罪手段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详细到凶手如何挑选作案工具、如何设计作案流程、如何诱捕女性受害者等,这些细节让观众身临其境,深刻体会那如影随形、令人毛骨悚然的悬疑氛围。

挑选作案工具:绞肉机、刀具以及一次性塑料服
大尺度并不必然会给观众带来“消极”的情绪体验,相反,适度暴露于负面信息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源。在安全可控环境下接触某些令人不安但又不至于造成实际伤害的情境,如《漂白》的血腥暴力场景,为观众提供一个宣泄内心压抑情绪的出口。这有点类似于我们观看惊悚或恐怖电影。
从这几年国产犯罪悬疑剧来看,《漂白》的尺度是数一数二的,观众被吸引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上面“格外开恩”,或许以后悬疑剧会开始卷“尺度”。
《漂白》能爆,王佳佳饰演的宋红玉也阙功至伟。
在国产犯罪悬疑剧的创作历程中,不难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杀人凶手或者行为残暴的人物,几乎被男性所垄断。这种性别设定,有现实的依据,也有创作的惯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确实会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
比如《漂白》中的邓立钢,从演技层面而言,王千源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将邓立钢的冷酷、阴鸷刻画得入木三分,角色极具压迫感,让观众看得不寒而栗。但邓立钢与王千源以往所塑造的反派形象如《解救吾先生》中的张华,并未展现出太大的差异化。
并且,这种反社会人格很容易单薄化。他们的行为动机常被单一设定为对金钱、权力的欲望,或是单纯的心理扭曲,缺乏对角色成长背景、内心深层矛盾的挖掘,角色行为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撑,更像是平面化的符号,只能依靠夸张的暴力和疯狂来吸引眼球。
《漂白》的犯罪四人组,真正有突破的是宋红玉。

邓立钢(王千源 饰)与宋红玉(王佳佳 饰)
冷酷而残忍的宋红玉,打破观众对于女性角色的固有印象,提醒着观众犯罪和残忍并非某一性别的专属,而是人性在特定环境下的扭曲和变异。
宋红玉也令观众不禁追问:她何以堕落至此?
宋红玉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角色,她从受害者的身份逐渐转变为施暴者,隐藏着复杂的成因和深层的女性困境。这一堕落过程既可怜,更可恨。
14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家庭因此背负沉重债务,宋红玉在15岁就开始外出打工还债,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过早地接触社会的冷酷。18岁时被煤老板包养后又被无情抛弃的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她内心的创伤。她在酒吧推销酒水时被邓立钢绑架,为了自保最终加入犯罪团伙,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机智诱骗无辜女性,参与绑架和谋杀。

宋红玉曾经被邓立钢绑架
面对同为女性的受害者,宋红玉甚至比其他男性团伙下手更狠。一方面,宋红玉从小到大经历无数次背叛与挫折,这些经历塑造了她坚韧但又冷酷的性格。加入犯罪组织之后,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加,她的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对女性的伤害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冷酷和随意。

宋玉红逐渐变得“无德无情”
另一方面,在宋红玉所处的犯罪环境中,邓立钢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她曾经作为受害者的记忆并没有消失,而转化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面对同为女性的受害者时,她将自己曾经遭受的痛苦和恐惧施加在她们身上、将曾经的苦难转化为对她们的恶意,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强大,获得在犯罪团伙中的生存空间。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变体:认同并模仿压迫者的行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与安全。宋红玉内心深处的创伤与脆弱却被深深地隐藏起来,只有在某些特定时刻才会偶尔闪现,却又很快被她用更残忍的行为所掩盖。
这样的女性加害者让我们心生憎恨的同时,也不得不检讨背后的社会与心理成因,反思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扭曲与异化,警示我们关注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灵魂,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
《漂白》成为爆款还有一个不得不正视的因素,即它对受害者受虐情节的聚焦与放大,特别是“虐女”,虽然存在价值观上的偏差,却又畸形地促成了它的超高热度。
比如甄珍遭受身体上的摧残,被锅铲扇脸、老虎钳夹肉、铁锤砸腿等,这些残忍的画面被详尽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是对受害者痛苦的放大和渲染,违背了保护受害者的基本原则。
更关键的是,当镜头过多地对准受害者的痛苦与无助,而非加害者的狰狞、可怖与不可原谅,其实是对加害者的某种淡化处理,观众虽然记住受害者的苦难,却对加害者的恶劣行径和丑陋嘴脸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批判。比如宋红玉竟然被一些观众认为很“飒”,演员的魅力轻易就遮掩了角色的恐怖。
而在社交媒体上和短视频平台上,剧中的犯罪四人组甚至被娱乐化了。比如他们被冠以“肉联厂F4”的称号,将严肃的犯罪事件与轻松娱乐的偶像概念相融合,剥离了犯罪行为的恶劣本质与沉重后果,使得大众以一种戏谑、调侃的态度看待犯罪者;宋红玉拿着锅铲凌虐甄珍的动作也做成各种表情包,在评论区里广泛出没。

“犯罪四人组”拍得像画报,这种宣发方式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很残酷的一个事实是,价值观存在偏差的“虐女”桥段,反而是一些观众爱看的。除了观众本身对于非常规、极端的情节和画面抱有好奇心以外,背后隐藏着一种扭曲的心理机制。
在部分观众那里,目睹女性遭受虐待的情节时,竟能从中获得一种特殊的“快感”。这种“快感”的来源并非基于人性中对女性应有的同情,亦非源自对正义本能的伸张,而是深深扎根于一种对弱者痛苦的扭曲认知与满足。他们在潜意识里对权力/性别的不平等有着敏锐感知,当看到女性这一相对弱势的群体承受痛苦时,内心深处对权力/性别不平等的潜意识认同被悄然唤起。在这种强弱鲜明对比的极端场景中,他们找到一种虚幻的掌控感,通过见证弱者的痛苦来凸显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优势,尽管这种优势是建立在对他人痛苦的漠视之上。
从这个层面看,《漂白》虽然以它的大尺度成功创下迷雾剧场的各项纪录,却不意味着它就是一部多好的剧集。影视作品中到底该如何更合理地处理暴力镜头,是需要好好复盘和思考的议题。
值得一提的是,《漂白》改编自真实发生的“哈尔滨连环碎尸案”。一个四人犯罪团伙自1998年至2004年期间,在多地流窜作案,实施针对女性的抢劫、杀人、碎尸等恶性犯罪行为。2011年,该案件被警方成功破获,犯罪团伙成员相继落网。2012年,《南方都市报》据此刊发的深度调查报告《漂白》,让案件广泛进入公众视野。
这篇深度调查报道的重心并不是犯罪四人组如何作恶,而是他们如何“漂白”——作恶多端的他们,怎么摇身一变拥有了全新的、干净的身份?“漂白”的背后暴露了多方面的机制漏洞。比如在户籍管理层面,部分地区存在审核不严的情况,仅凭村委会证明和副所长签字即可落户,为不法分子创造了可乘之机;信息管理系统存在缺陷,此前一些地方的户籍系统档案遗失、有易被利用的特殊模块等,导致身份信息被恶意篡改却难以追溯;基层执法人员的监管缺失,个别警察与犯罪分子勾结,严重破坏法律秩序,让这些身负命案的逃犯能逍遥法外长达十年,凸显完善户籍管理及执法监督机制的紧迫性……

犯罪四人组成功“漂白”身份
相形之下,根据同一案件改编的《漂白》,在主题表达上有很大的欠缺。剧集没有着重反思“漂白”这一关键行为背后所暴露出的制度漏洞,更多地将重点放在犯罪四人组的犯罪过程,以刺激的情节和动作场面来吸引观众眼球,忽视对案件核心问题的深度剖析。
总之,《漂白》的火爆充分说明了:只要把关的尺度放松一点,创作者便能从那些被尘封的真实事件中挖掘素材,在情节铺陈与人物刻画上拥有更广阔的发挥余地,创作出更具噱头和更有市场号召力的作品。
只不过,作品的火爆程度与作品本身的好坏,并不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越是火爆的作品,它的效仿者也会越多,如果它已经出现一些不良的苗头,就尤其值得我们审慎对待、理性探讨。既要避免上纲上线,避免好不容易放宽的尺度再度紧缩,也要避免爆款至上,好像只要是爆款,各类不足就可以视而不见、放任自流。我们应在这两者间找到平衡,既尊重艺术表达的自由,也不放弃对高质量内容和正向社会效应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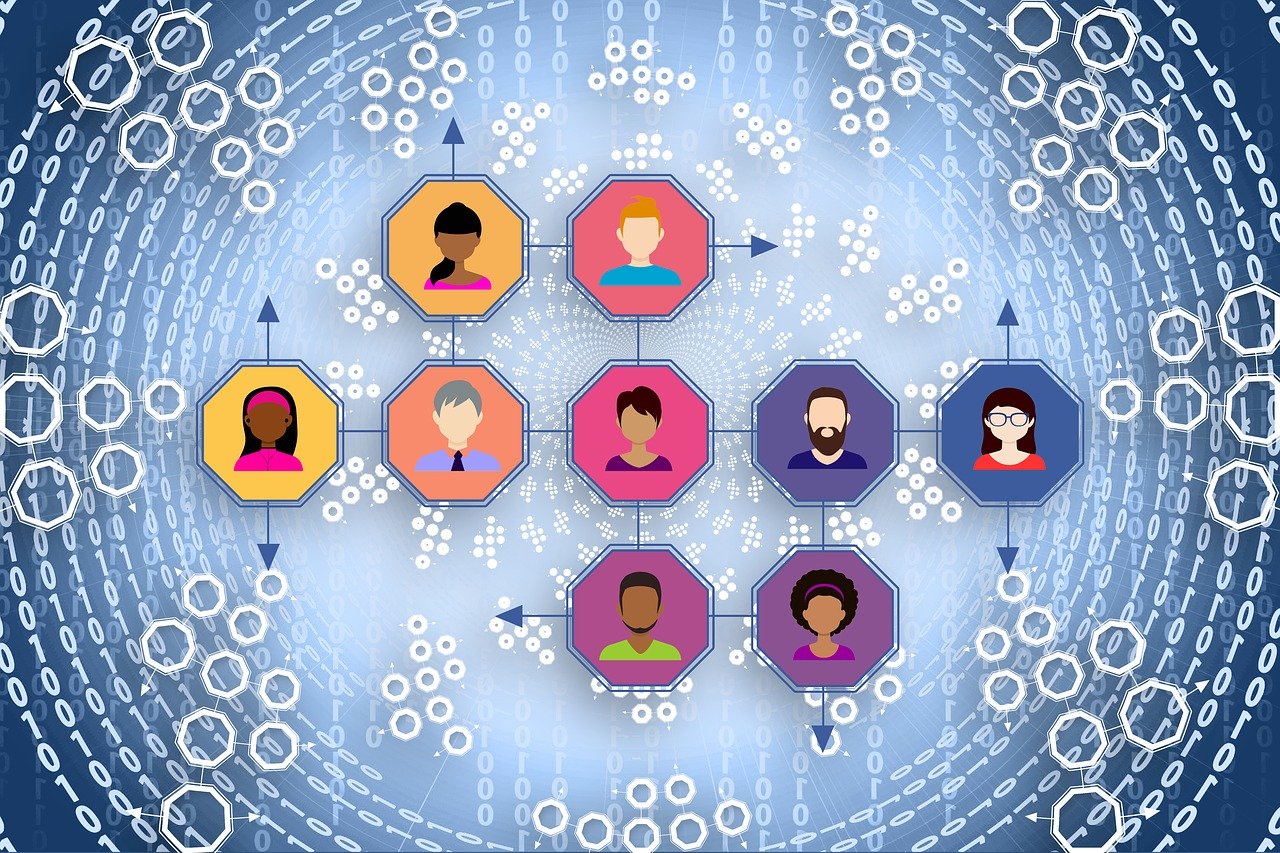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