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大学名誉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唐史学家、碑刻专家,他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故而亦是陕西师范大学知名校友。值此陕西师范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之际,今日请毕业于唐史研究所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王坤先生翻译这篇气贺泽先生当年回国后撰写的随笔文字,并附上当年照片两帧,以志庆贺。原文刊登于日本神保町著名的中国学研究专门书店东方书店的店刊《东方》第76号(1987年)。
结束了长达二十二个小时的北京至西安的火车行程,我一个人站在了西安站的出口,时间是一年前的一月三十一日清晨八点多。
冬季西安的早晨来得晚,太阳还未露头,空气也很冷。映入眼帘的是站前的拥挤、飘落的树叶、灰色笼罩着的街景、布满尘土的道路,以及弓着背来来往往的黑色人群,令人感觉是到了一个寒冷的乡下城镇。这是西安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离开北京之时,老师们曾提醒我,西安无论是在研究还是生活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长期逗留会很辛苦,建议我适时返回。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想起那些嘱咐的话语和生活了四个多月的北京大都市的情景。
就这样,我在西安的生活在一种并非美好中开始了。但是,从不久的春节之后我就融入了人群,蹬着自行车出没其间,变成了地道的西安人了,以至于七月末返京日期迫近之时,我竟然祈望能多呆些时日。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了我呢?或许正是那些纯朴善良、温暖如春的人们,用他们最朴实的情感,触动了我的内心。
我受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从1985年9月开始为期一年的中国访学之旅,主要求学目的地是北京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前者暂且不说,而之所以选择后者,一是缘于陕师大所在是笔者的专攻领域隋唐都城长安,二是我经常联系的一位尊敬的学者黄永年教授执鞭于此。陕师大坐落在西安南郊,从宿舍窗户就能远望大雁塔和终南山。其间,我经常往先生的研究室和府上拜访,或者是在讲座等时机聆听到了先生恳切而富深意的教诲。

1986年2月春节时于陕西师范大学,左起为牛致功、史念海、黄永年三位先生。
先生出生于1925年,原籍江苏省江阴县北乡,成长于武进县(现常州市)。先生矢志史学研究的直接机缘是在1942年的中学时代。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生幸遇当时为躲避日军进驻上海而暂居常州的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其中一位就是隋唐史研究大家,光华大学的吕思勉。为了聆听吕思勉先生在青云中学(实际为苏州中学分校)的讲授,先生专意转学于此,并为吕先生的“国史”课程所深深折服。另一位则是顾颉刚的高足,后来担任山东大学教授的古文献学权威童书业。与执教于常州惠林中学的童先生的相识,据说是经由吕先生介绍的。后来童黄两位在学问上成为师徒传承的同时,也结成翁婿关系。先生中学毕业之后,一度入学南京中央大学,后于1946年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后为历史系),1950年毕业后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执教,后来又随着交大部分西迁,先生也一同来到了西安。“文革”后,承蒙由顾颉刚先生所创立的禹贡学会资深会员史念海教授的引荐,而转入现在的大学。先生自陕师大历史系转入唐史研究所,同时兼任古籍研究所教授,讲授唐代政治史与碑刻学,并且担任初创期的唐史学会秘书长。
黄先生还有一件趣事。某日在研究室,先生拿出一套开明书店版的正史说道:“这是我求学时期在上海霞飞路(现淮海路)的老书店上海修文堂买的,其中还有日本牧田谛亮的藏书印。按此说来,我与牧田先生也可算是学问上的兄弟了”。我听说牧田先生曾就职东亚同文书院,战后在接收战争财产时,其个人藏书也被没收。在归国后某次学会上,我告诉了牧田先生关于黄先生的这件趣事,牧田先生曾感慨那些藏书遭遇的不幸,未曾想幸归著名学者之手而发挥作用,在惊喜之余,又有几分感激之情。
四月,我结束了历时一个月的河南、湖北、四川三省之旅,回到西安打开报纸一则新闻映入眼帘。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已经着手椁室开启。在离开北京时,任《朝日新闻》特派员的加藤千洋先生曾有所托,便立即给他打了电话,他回复说可以的话想来西安。于是,对该项发掘一直很感兴趣的我又进一步进行了细致了解。首先当然是想去发掘现场看看,便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但都未获得批准。于是我直接拜访了以研究农民战争史而闻名,曾任陕师大副教授,现为省文化方面负责人的孙达人副省长,但仍然被以对外国人尚未开放为由拒绝了。

1986年5月于陕西师范大学,从左往右为赵吉惠、何清谷、气贺泽保规、赵文润。
于是,我想到了平日对我多有关照的西北大学林剑鸣老师。林老师曾于1985年受关西大学邀请而赴日交流,去年被推举为秦汉史学会会长,关于林会长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在此就不必赘述了。林老师让我见了西北大学研究生,并与秦公大墓发掘工作有关的马振智先生。马先生从古雍城全貌到墓室构造,一一给我做了详细讲解。当时他告诉我,《光明日报》驻西安办事处的记者白建钢所采写的有关报道是可信的,因为其曾在西北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考古学。之后,我与白记者在宿舍谋面,了解到了很多实际情况。他们年龄在三十岁上下,都是年青的研究翘楚。顺便说一下,在西北地区能够开设考古学课程的只有西北大学,活跃在博物馆以及研究所的许多学者都是出自该大学。
尽管我对于秦公大墓的实际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但是仍然无法进入现场。此前我对于陕西等地严格限制外国人活动范围的情况有所经历。于是在七月中旬,我决定假装为中国人外出考察。途中经过了周朝兴起的岐山和周原,直到中午时分才抵达凤翔县。我朝着古雍城遗址南侧的田地望去,来到了发掘现场。幸运的是,那时正值午睡时间,只有几名解放军士兵在值守。由于前几天的大雨,古墓的南侧斜坡已经坍塌了很多,但其规模仍让我感到震撼。出土的椁木露天堆放在墓坑外,站在宽广的黄土高原上,近距离观察宏伟的秦公大墓,让我不禁联想到当时秦朝的强大与文化的辉煌。
在西安逗留期间,听闻报道说,对唐皇城含光门(朱雀门西侧)的考古发掘已经结束了。于是我立刻前往现位于南城墙与甜水井街交叉口的含光门发掘现场。始于隋而扩于唐的砖砌基础、门柱及车辙的痕迹清晰可见,紧邻的东侧还有宋代的通道。看来唐长安城的皇城与如今的城墙南侧部分重合是显然的事实。
名义上负责此次发掘的是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分所,但是大部分的发掘工作是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省社会科学院不同系统)组织的考古队实施的。例如秦兵马俑坑和雍城的发掘便是如此。以上情况是陕西省考古所隋唐研究室的贠安志主任向笔者提供的。另外,在黄先生的指引下,我还得以一窥正在发掘中的唐太宗昭陵陪葬墓中的程知节墓及襄阳公主与窦诞合葬墓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墓葬的破坏情况较为严重,但仍有壁画保存下来,期待日后的详细报告。此外,据说长乐公主墓也将于近期开始发掘。
说起来,每个到西安旅游的人或许都会感受到这里的生活水平与沿海地区相比有着很大差距,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也比较多。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当前西安正在重新规划观光旅游事业,其中之一就是全面修缮明代城墙,以及疏浚护城河。这些工作正在加快推进。未来游客可以在城墙上骑自行车,在河上乘船游览,享受古都的美景。大雁塔周边也将发展为文化旅游区,东侧将建成仿唐长安西市的设施——西安影城游乐中心,而西侧则计划建设与故宫、南京博物院比肩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而且已经给陕西历史博物馆预留有五万平方米的广阔用地,并由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宋史的杨德泉教授担任主任,组建了筹备工作室,已完成了蓝图绘制。杨教授表示,这座博物馆将配备现代化的设施,展出省内一流的历史文物,同时还将设有外国研究者的住宿设施,为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活动提供方便。目前,该项目正朝着1989年秋季竣工的目标积极推进。
西安人经常提到本地的文化传统。尽管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我的确能感受到其他地方没有的历史趣味。西安在历史研究方面也非常活跃。像在前文未曾提到大名的贺梓城、孙浮生两位老先生都健在。尤其是贺先生,以卧病之身根据中央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计划,准备出版《陕西出土唐墓志考释》。陕师大的牛志平、贾宪宝,还有西北大学的胡戟等中坚力量都在坚实地开展研究。我想,今后要格外关注西安学界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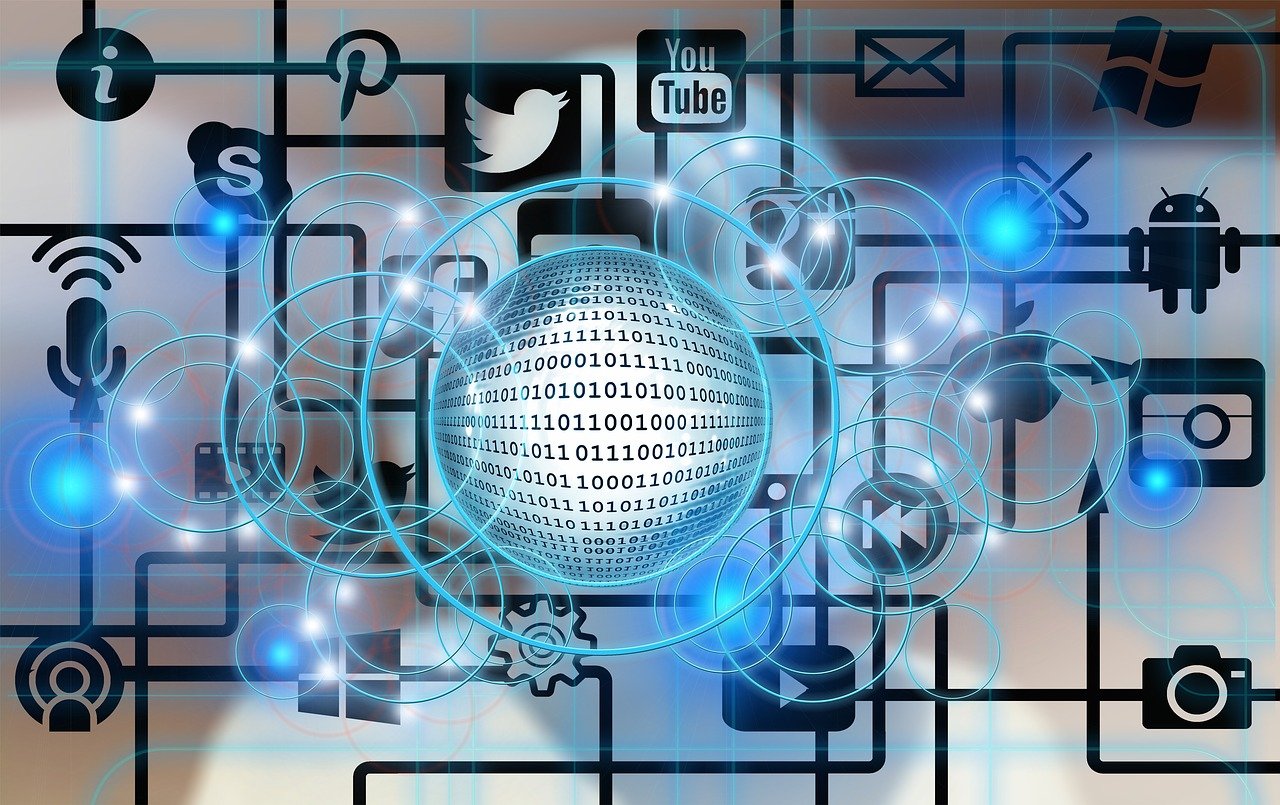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