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戈达尔在瑞士安乐死与台湾地区女作家琼瑶的离世都掀起热烈讨论,安乐死一再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反映了这个问题复杂的本质。2024年10月16日工党后座议员金姆·里德彼特(Kim Leadbeater)提出《绝症成人(生命终结)议案》,这项议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英国人——毕竟,死亡是唯一确定的事情,只是时间和方式不确定——因此引起极大关注。
1942年瑞士将辅助死亡(安乐死)合法化。瑞士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公民“死亡权”的国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允许外国人来瑞士安乐死的国家之一。2001年和2002年荷兰和比利时也都将安乐死合法化,适用于因患不治之症(包括心理健康问题)而遭受难以忍受痛苦的患者。此后,在比利时,这一法案已适用于儿童——这是欧洲唯一一个允许法案扩展到包括儿童的国家。在英国,自2010年以来,保守党主导的议会七次否决了一项又一项关于安乐死的议案。议员们上一次投票决定是否将安乐死合法化是在2015年,当时的议案以330票对118票被否决。

2024年11月29日,议员们对议案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辩论。工党议员玛丽·蒂德博尔(Mary Tidball)出生时患有先天性残疾。她表示,她将投票支持该法案,但会在后期推动进行重大修订。她回忆起自己六岁时接受大手术时所经历的极度痛苦。“我从胸部到脚踝都打着石膏,非常痛苦,需要大量吗啡,我的皮肤开始发痒。我清楚地记得躺在谢菲尔德儿童医院的病床上对父母说:‘我想死,请让我死吧!’”她说,“那一刻让我懂了,我希望自己可以选择死亡……”提出该议案的里德彼特议员谈到,目前英国每年有600名绝症患者自杀,那些负担得起的人会去瑞士安乐死。在过去的20年里,有500多名英国人在瑞士安乐死,其中包括2023年的40人。他们通常独自一人,而且为了不让亲人受到牵连,他们比预计情况下更早死去。这怎么会比医学上认可的在家中死亡更人道呢?媒体上也有大量支持此议案的声音,如莫琳·安德森(Maureen Anderson)是一名育儿顾问,她说:“我不希望我的家人成为全职护理人员。我会举办一个‘告别派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有尊严地死去。”她认为,老一代人,特别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可能会反对这一做法,但下一代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就像火葬在历史上不被人们接受,但目前已经被普遍接受一样。
支持议案的议员们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包括:规定辅助死亡绝不能由医务人员提出,而只能由患者主导;引入审查或撤销程序,否则人们担心受到胁迫的受害者将无处求助。目前的议案规定,辅助死亡的请求必须由两名医生和一名高等法院法官签署,有人呼吁议案应明确规定医务人员和法官所需的培训,特别是让他们能够识别胁迫的迹象。此外,一些人提出批准使用辅助死亡药物的医生应该拥有特殊执照。
反对意见主要包括:一是大多数医生认为很难准确预测一个人何时会死于绝症,因此六个月的时限很难把握。二是人们担心弱势群体,特别是残疾人,可能会选择安乐死以避免成为家庭的负担——包括护理费用。三是人们担心临终的人会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四是有人认为此议案对医疗和司法监督的要求不够。五是有人担心该议案不可避免地导致的结果是,一旦引入辅助死亡,它将在公众和议员眼中成为常态,并且不可避免地会被扩展或滥用,类似比利时法案适用于儿童的情况。
财政委员会主席梅格·希利尔(Meg Hillier)持反对意见。她讲述她十几岁的女儿因急性胰腺炎入院的经历时哭了起来。“五天里,事实上是几个月里,我都不知道她是生是死……但我看到了好的药物能减轻疼痛。”她敦促议员们否决该法案,她说:“如果我们对允许国家拥有这种权力有一丝怀疑,我们今天就应该投反对票。”前内政部长詹姆斯·克莱夫列(James Cleverly)问道:“如果这是缓解痛苦和折磨的好事,这是我们应该自豪地赋予民众的权利,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推广于儿童?”同样,网络上也有反对的声音,如查理·科克(Charlie Corke)教授认为议案要求进行司法审查,这将构成重大障碍——法院已经不堪重负——同时不太可能使这一过程更安全。
即使是投票支持此议案的人也有反对意见,但这些反对意见集中在议案的细节和可操作性上。有人认为这个议案太过狭隘,并质疑为什么不应该扩大,如扩大到包括患有绝症且生命比六个月更长的人,以及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没有绝症的人。
在议会的辩论中,无论支持和反对议案的议员们都提出英国目前对临终关怀投入的严重不足。根据英国临终关怀协会的数据,2022-2023年,在200多个临终关怀医院中,约有30万人获得了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其费用是每年16亿英镑,但只有5亿英镑来自政府,其余11亿英镑来自捐款、遗产、慈善商店的收入和其他筹款活动。虽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没有包含在议案中,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必须与之同时解决的问题,以确保如果辅助死亡合法化,人们不会仅仅因为无法获得适当的临终关怀而选择它——虽然这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雷切尔·克拉克(Rachel Clarke)——一名姑息治疗医生,也是《惊心动魄:大流行时期的NHS内部》一书的作者——认为2024年英国政府对姑息治疗、社会护理和医疗保健资金的投入严重不足,以至于身患绝症的人被一个声称关心他们的社会所忽视,“眼不见,心不烦,任其腐烂”。
在投票前,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表示“这将是一次自由投票(也称为根据自己良心的投票,a conscience issue,即不是按党派的立场投票——笔者),我是认真的。每位议员都可以自己决定如何投票。我不会对工党议员施加任何压力。他们会像我一样自己做决定。”2024年11月29日,议案二读后议员们进行投票,投票结果是330票赞成,275票反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议案得以进入下一阶段的讨论。
《绝症成人(生命终结)议案》在成为法律之前仍需克服许多障碍,其中五个阶段由议员处理,另外五个阶段由同僚处理,并会再次投票。现在此议案进入委员会审查阶段,由一些议员逐行审查。然后是报告阶段,允许任何议员提出修正案。下议院议长将决定对哪些议案进行辩论和表决。此后,议员们将有最后一次机会在三读后投票——有些议员可能会改变主意。之后,五个阶段都将在上院重复。如果上院的议员们不提出任何进一步的修改意见,该议案将送交国王批准,国王签署后该议案将正式成为议会法案。所以即使乐观地看,这个议案成为法律也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提出该议案的里德彼特告诉BBC,对该法案能在议会通过她感到有点意外,她现在将专注于在该议案成为法律之前完善它,因为“把事情做好比迅速完成更重要”。
我一直支持有条件的安乐死,即得了绝症、没有治愈的希望,同时又遭受极大的痛苦,那么安乐死一定是一种解脱。古今思想家都表述了类似的看法,如英国著名思想家、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发表于1516年的《乌托邦》中写道:“如果某一病症不但无从治好,而且痛苦缠绵,那么,教士和官长都来劝告病人,他现在既已不能履行人生的任何义务,拖累自己,烦扰别人,是早就应该死去而活过了期限的,所以他应决心不让这种瘟病拖下去,不要在死亡前犹豫,生命对他只是折磨,而应垓怀着热切的希望,从苦难的今生求得解脱,如同逃出监禁和拷刑一般。或者他可以自愿地容许别人解脱他。在这样的道路上他有所行动将是明智的,因为他的死不是断送了享受,而是结束掉痛苦……但乌托邦人决不在这种病人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夺去他的生命,也绝不因此对他的护理有丝毫的松懈。他们相信,经过这样劝告的死是表示荣誉的。”
再如美籍匈牙利心理学家托马斯·萨斯(Thomas S. Szasz)教授在《自杀的权利——自杀的伦理和政治问题》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必须将“自愿性死亡”(以这个新词代替自杀这个具谴责意味的词)去医学化、去污名化,接受这是一直以来、在未来也将会存在于人类情境中的一种行为。他认为要找到答案无须借重任何特殊的医学知识,只需要一种面对死亡的意愿与勇气,他写道:“最终,我们将让它变成自己的选择,不管教会或宪法或医学预备要告诉我们什么。”每个人都应有选择的自由,一些人可以选择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也有人可以选择在自己年老体衰时有尊严地离世,这种行为不构成犯罪。
人生苦短。人必有一死,死亡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死亡不应是消极的防御,而是主动谋划的任务”。谈论死是为了更好地生,生命因为是有限的所以才有意义。因此,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利用自己的才智、时间,让自己的生命价值最大化。向死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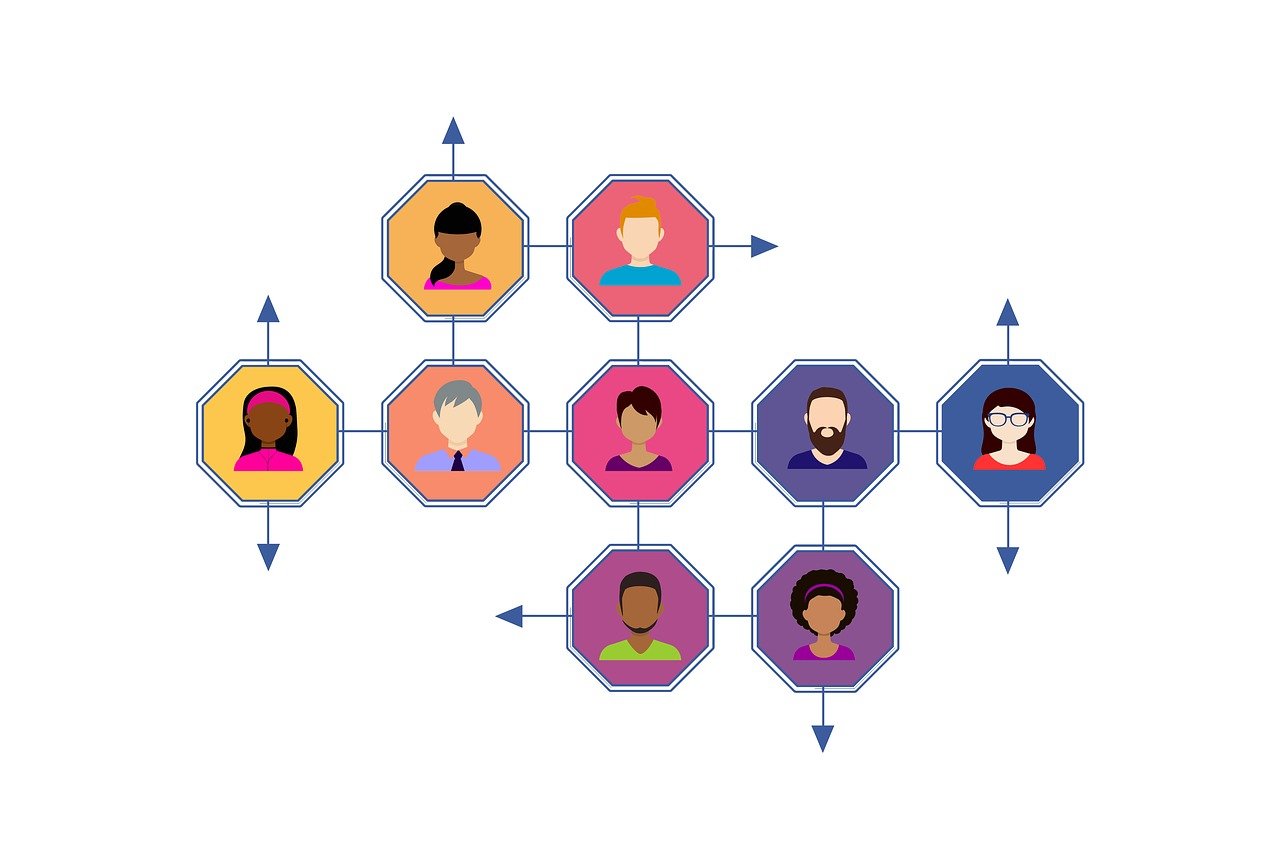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