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诗人、学者戴潍娜推出新书《学坏》,书中,她选取鲍勃·迪伦、普希金、乔伊斯、波伏瓦、玛丽莲·弗伦奇、伊藤诗织、林奕含、赫胥黎、泰戈尔九位作家,展开自己的阅读与分享,从一位诗人的视野出发,理解属于他们身上“反派”又“迷人”的部分。
值此书出版,本书作者戴潍娜、作家许知远、历史作家李礼以“历史与文学之间”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分享活动,从戴潍娜的新作《学坏》谈到李礼的新作《失败》,从19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谈到人文经典在历史上呈现出的闪耀光辉。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打捞出那些激动人心的、令人深思的瞬间,并透过它们,看到更远的未来。

新书《失败》
戴潍娜从大家最近的一部作品谈起,她谈道,自己的新书《学坏》、李礼的新书《失败》和许知远的新书《梁启超:亡命(1898—1903)》,这一组书名让人想到约翰尚利的《怀疑》,“这部戏剧甫一开场,牧师就对信众们说,‘将你们连接在一起的是你们的绝望,这是一种公众的体验,由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分享着。’我们共同分担着这样一份时代里的绝望,《怀疑》当中的对白也可以称为这些书名的精神注解。”

新书《梁启超:亡命(1898—1903)》
谈到自己的《学坏》,戴潍娜介绍:“我在这部书里面在寻求一个‘诱惑’和‘觉醒’的双螺旋结构——人类所有反思和争论其实都来自于诱惑。伟大的诱惑者,和令整个世界不安的觉醒者,构成了文学世界的阴阳两极。我希望通过这部书展现出人类精神成长历史中的这层隐秘动力。”
在《学坏》中,戴潍娜写作的就是一系列让她着迷的伟大的诱惑者们,比如鲍勃·迪伦、乔伊斯、赫胥黎……他们都是一些贩卖思想禁品的人物,思想才是最大的违禁品。这些伟大的引诱者身上,都饱含一种撒旦的能量,他们用一场场黑弥撒般的突袭,去冲击当时的社会制度、风俗、礼教,引发认知与审美领域的革命,掀开了一场场延续至今的广泛变革。在这些杰出个体与时代的摩擦当中,他们将原本仅属于自己的风华正茂和独特风范,渗透到时代性格之中;以自己的个性,拓宽和延展了世界的边界,诱惑着时代去往新的方向。追踪这些诱惑者,也是在追索时代心灵成长过程中的隐秘线索。
除了这些引诱者,戴潍娜也在书中着意突出了她所定义的一系列伟大的“受害者们”。“比如像林奕含、玛丽莲·弗伦奇等一系列女性主义作者。过往人类书写的历史,可以被称作诱惑者的叙事。那些受害者的声音,从来都是缺席的,而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毫无想象力。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用受害者的声音,去反写了一个洛丽塔的故事。想象一下,有一天如果洛丽塔自己拿起笔来,她写出的可能就是林奕含那样的小说——那是一个为女性精编细织的地狱。男权社会通过摧毁女性的自信、人格,漠视其创造力价值,从而实现控制和奴役。我们的整套文明,建立在一半人沉默的历史上。”戴潍娜谈道。
戴潍娜认为,女性主义代表着一种至高的解放力,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是一种思想能量,女性主义必然要创造新的价值、新的话语、新的权力。
“但是,我们也悲哀地看到女性主义革命最终总是走向乌托邦之途,抑或走向禁忌之地。今天,一方面中国社会貌似迎来了女性意识的普遍觉醒,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革命成果正在遭遇最卑劣的窃取和篡改,可以说,中国的女性运动走到了最为危机四伏的关口。”
基于这样的现实,在《学坏》中,戴潍娜写到了波伏瓦这样的先驱,但是没有写她在女性主义革命中的硕果与那些荣耀时刻,而是特意去写了革命之后,她如何面对那个日渐走样的自己一手创造的世界。“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中意气风发地写道:‘总的来说,我们赢了这一局’,但到了她老年的自传当中,她突然发现‘我上当受骗了’,曾经轰轰烈烈的女权革命,到最后还是陷入到了旧有叙事当中,从而进入一种混乱、不可控,乃至走向更多的撕裂和极端。我想这也是此时此刻这个世界抛给每个人的无法回避的时代议题。”
戴潍娜表示,希望在这本小书里,通过这些伟大的诱惑者和伟大的受害者(或者说觉醒者),去共同创造一个性感的历史时间。
许知远谈道,戴潍娜的新书《学坏》非常有感受力,可以清晰看到她思想的脉络。“潍娜最初被更多人关注是她翻译的《天鹅绒监狱: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非常棒的一本书,是我当时从剑桥图书馆偷出来,送给她,翻译出版了。米克洛什·哈拉兹蒂被她翻译得很漂亮,短句子非常干脆利落,不容置疑的判断,对于那种模糊的社会现实一下子戳破的感觉。”

新书《学坏》
许知远谈道,自己和戴潍娜都很迷恋具有反叛精神的时代,“这个反叛不仅是思想上的,也是语言上或者精神状态上的。那种反叛可以撕开沉闷的现实,让新风吹进来,新风很快变成陈旧的风,很快那个窗口关起来。新风吹进来一瞬间就让人抖擞,潍娜抓住了新风吹入的时刻。”
李礼认为:“我们几个人不管写文学、写历史,似乎都在追求‘写空气’,写空气当中的荷尔蒙,而不是传统地写历史史实。”
许知远从一部名为《再见,总有一天》的电影谈起,“我被那个非常迷蒙的、潮湿的曼谷迷住了,故事里看起来非常不正确的一段恋情,最终却成为两个人一生中最正确、最持久的事情,在曼谷的那个短暂的时空,构成他们一生最大浓度的一个时空。人生也好,写作也好,我觉得好像经常是为了那个短暂时刻的到来,它可能会蔓延到你非常漫长的生命空间里去。”

《再见,总有一天》剧照
戴潍娜分享到,自己也和许知远一样,“迷恋即兴的、有情感强度的生活”,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量”,人需要高纯度、高浓度的moment,“可悲的是我们此刻的生活是一个消解性的生活,共享就意味着一种稀释,随着生活和本我在不断稀释,好像只有创造才能够带来那凝聚性的、高强度的时刻,某种意义上挽回生命时时刻刻的流逝,将生命用另一种方式抓住,把永恒钉死在白纸上。
戴潍娜也谈到,多媒介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新型自然”中——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充满了森林、阳光、雨水、大猩猩的自然,而是活在由WiFi,电子屏构建的“自然”当中,一个完全是被信息包裹,被社交网络,被各种媒介所包裹的新型自然。“于是,在考量人的亲密链接时,它可能确实不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的抵达,而是人跟一个流动的、杂糅的,多媒介信息世界的一种新型交互。”
对此,许知远认为:“我觉得包括要对个体本身有信念,我们总是迷恋统计数字或者时代结构、历史框架,总认为历史规律能够治愈我们的症候,不是的,我觉得个体可以发生某种改变。即使个体不能够改变更大的结构,你也可以改变自己生存的一个小空间。我们其实可以给自己创造非常多的逃离眼前世界,然后重新看看自己的机会。创造这些无穷的小时刻,包括友情小团体,创造无穷的小时刻,你就可以对抗时代的风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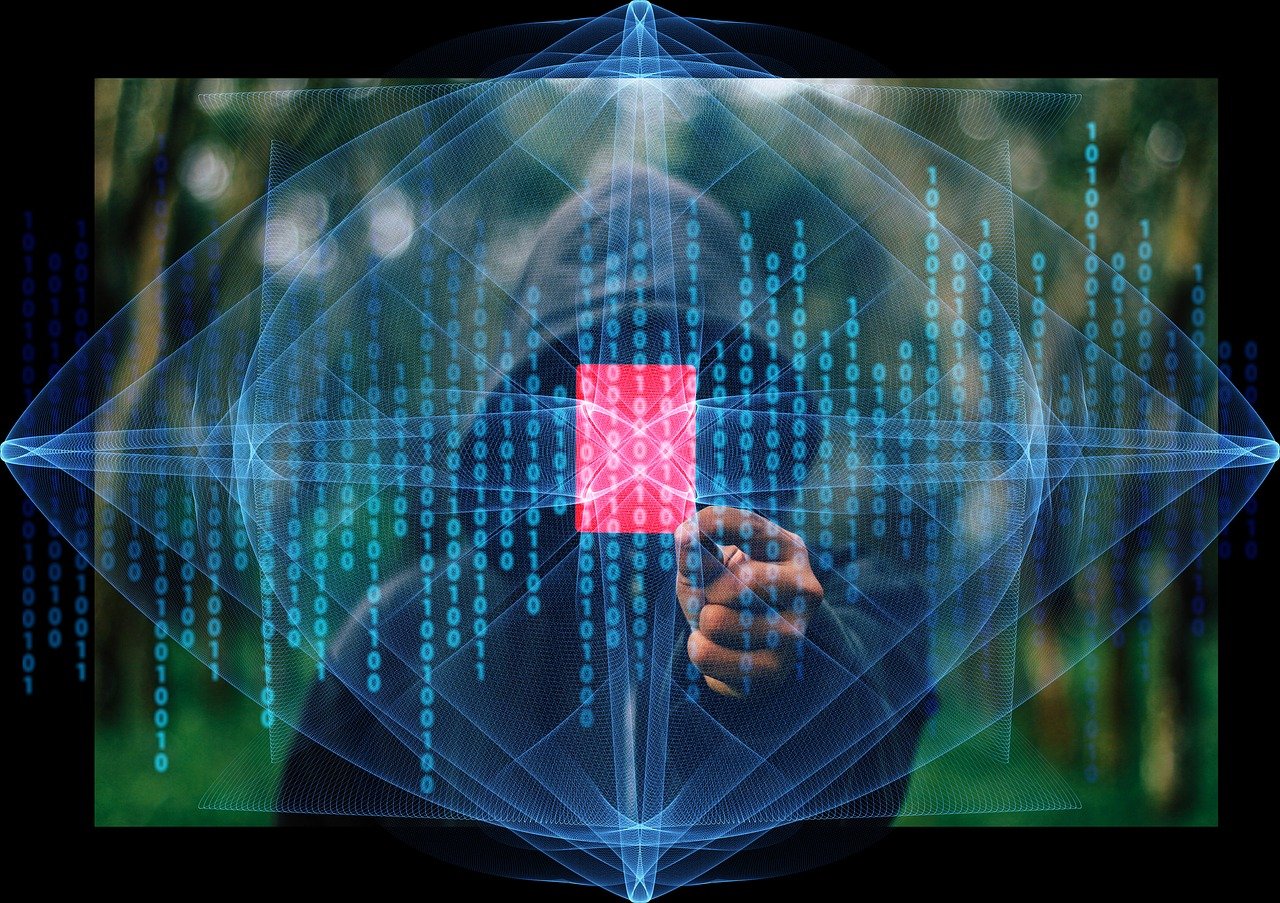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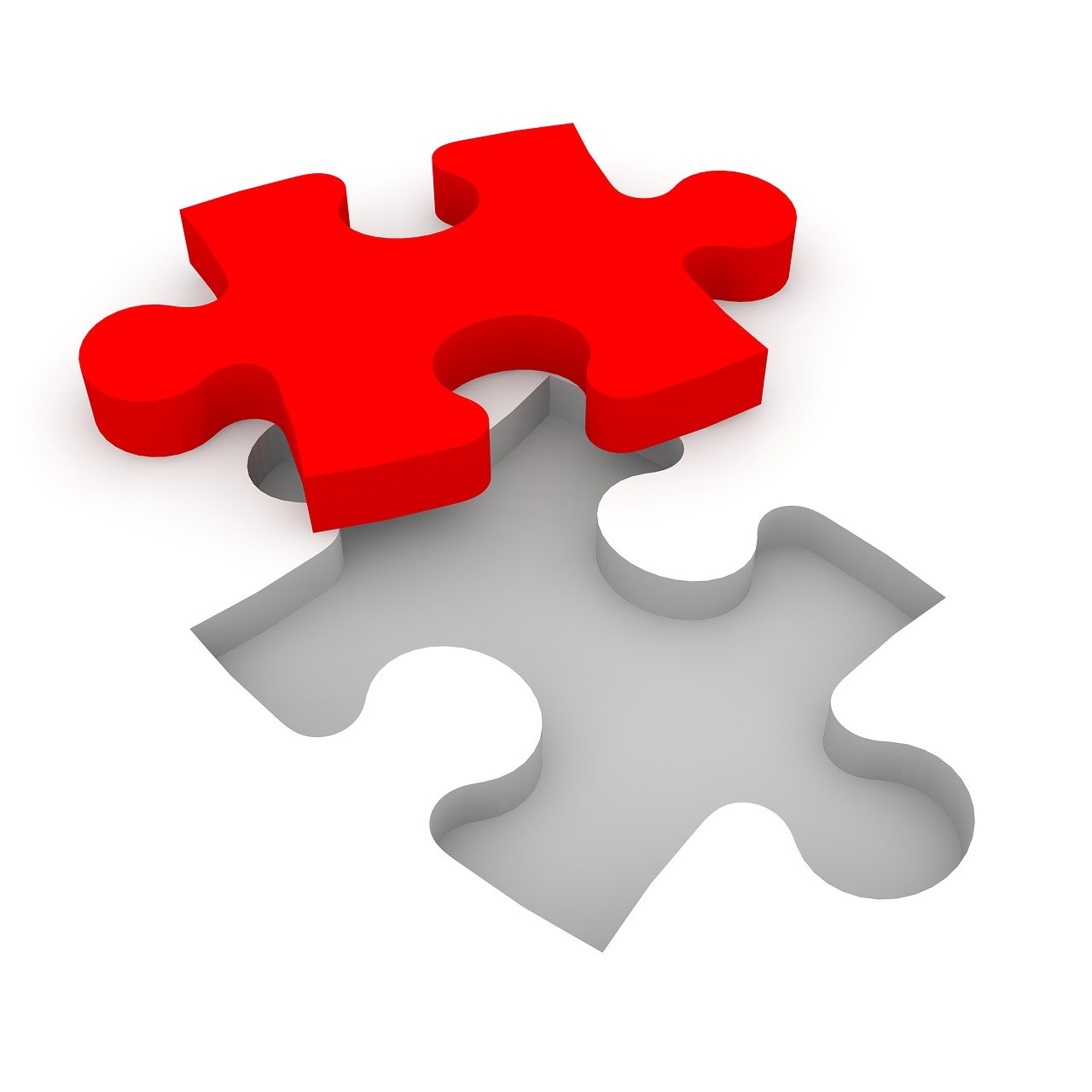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