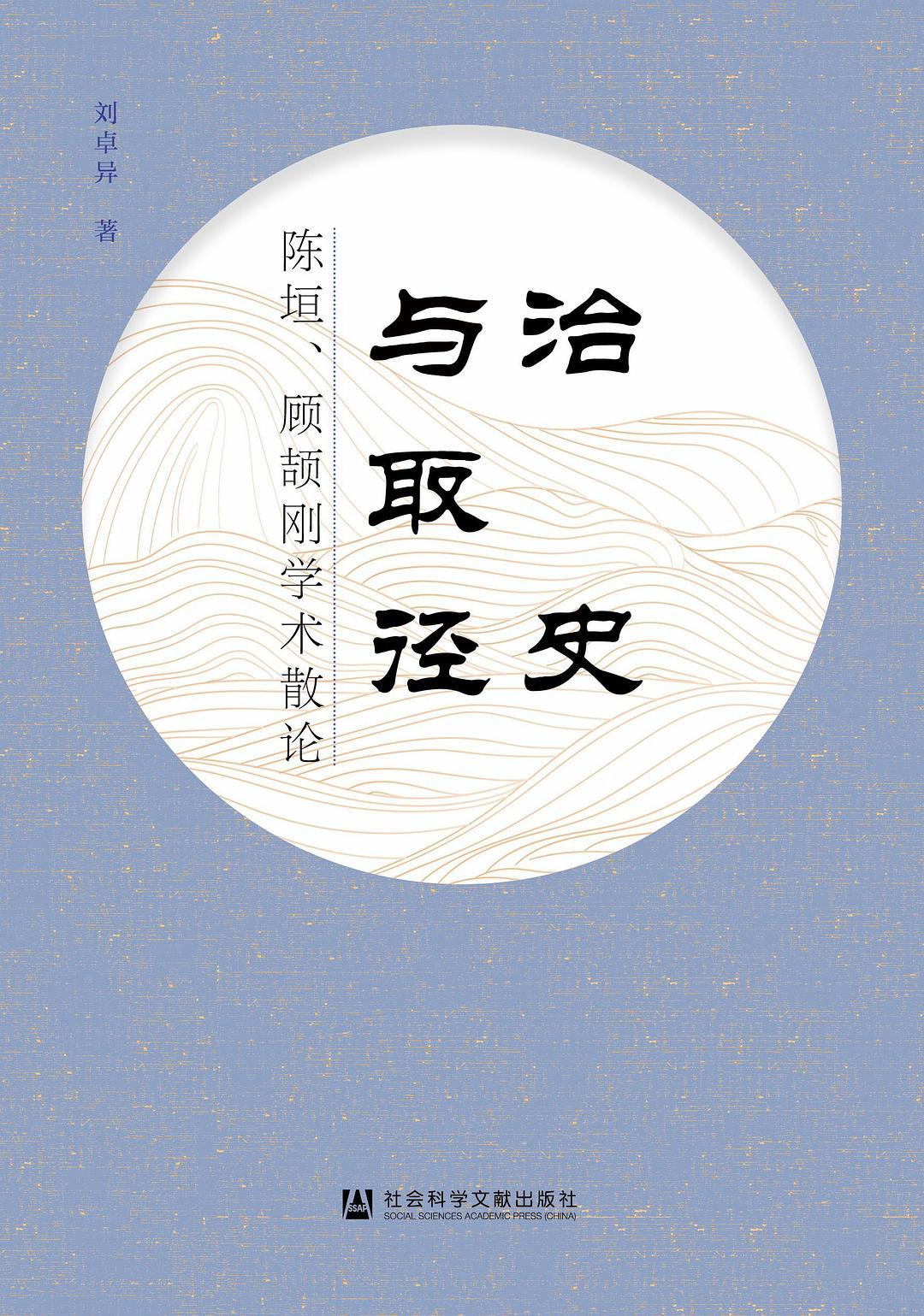
《治史与取径——陈垣、顾颉刚学术散论》,刘卓异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6月,212页,79.00元
谈起中国学术的古今变革,学者往往首推以罗振玉、王国维等前辈利用出土文献为传统学术打开的新格局,即陈寅恪所谓“新时代”“新学术”的“新资料”“新方法”。新出史料对革新研究观念与方法的推动作用诚然不假,但在我看来,学术发展的关键,在于突破过时的、不合理的思想束缚,引入具有启发性的观念和理论。只有以这个标准衡量学术史,才会看到,先秦诸子突破巫史桎梏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底色,魏晋隋唐理性高涨,最终“造极于赵宋之世”,晚近注重实证和典范,乾嘉学术和桐城选学作为传统学术的双子星座,以不同方式推动中国学术从“家学”向“分科之学”的转变。学术思想永远是观念的冒险,在这个意义上,陈垣、顾颉刚作为二十世纪史学的两座高峰,有着毋庸置疑的典型意义。
本书的核心人物,一位是陈垣先生,字援庵,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次长,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元史学家、文献学家,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另一位,顾先生讳诵坤,字铭坚,以号行。以古史层累学说和古史地域扩张学说名世,是思想家、教育家、古史专家,尤其为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奠基人,虽较援庵先生稍晚一辈,却在当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两位先生,前者是旧式学者,谦逊温和、沉稳内敛的老派作风,后者是学生运动先锋、新学风和新思想的传播者,二人虽同为历史学家,元史和上古史却已然有隔山之叹;虽同时供职燕大,但二人的交往罕被关注,甚至连一张合影都难见到,就像同为翰林供奉的王维与李白,如果不特意钩稽,很难描述他们的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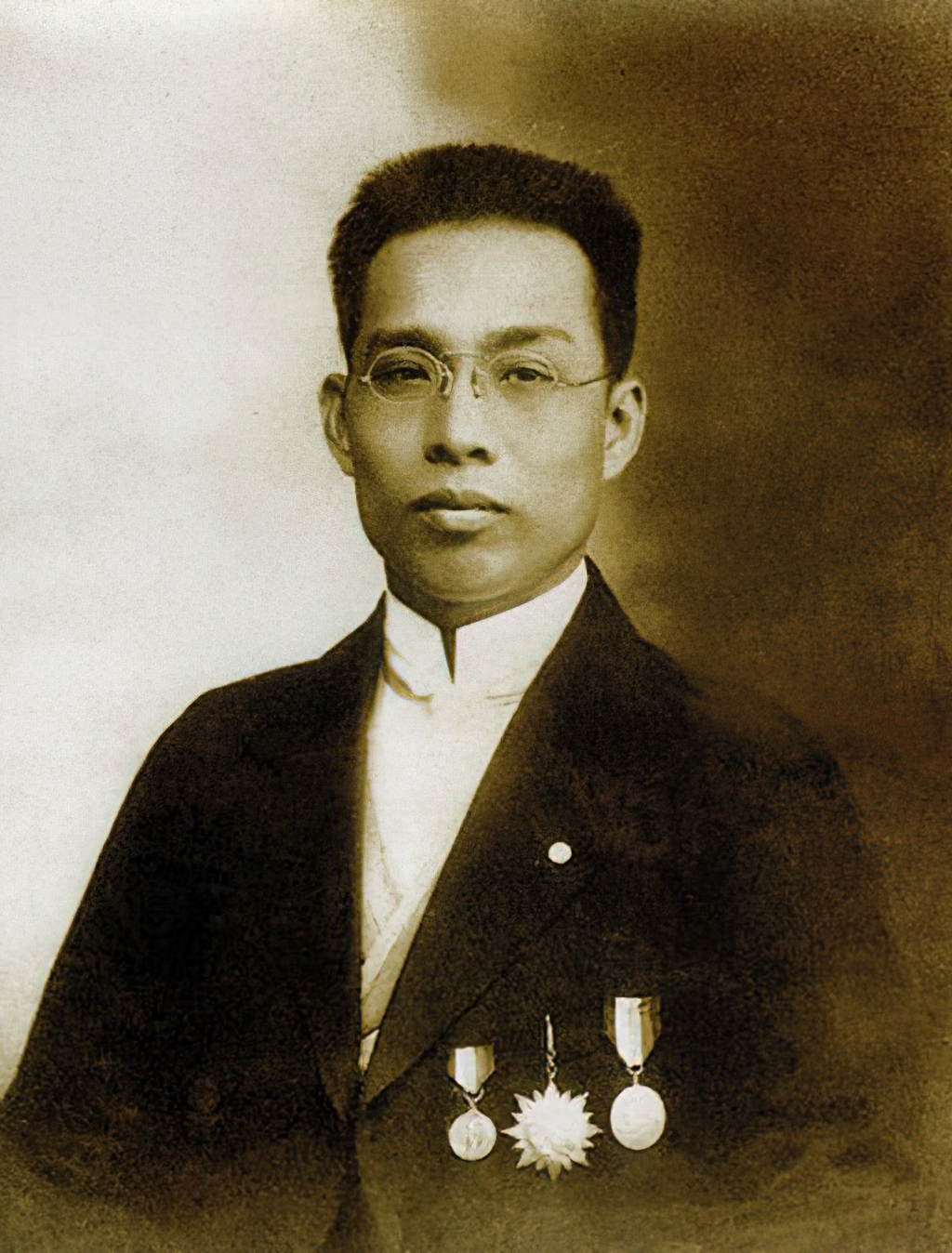
陈垣
“坊间”传闻,围绕两位先生,长期以来有不少误解。人们印象中援庵先生是守旧的,哪怕北平中央研究院同仁都用铅字小字排印著作,援庵先生却坚持用雕版刻印自己的著作,然而援庵先生用蒙语研治元代史学却是舶来的语文学(philology)方法,并为当时西方学者广泛关注。人们认为顾先生是“疑古派”领袖,常诟病他把太多文献指为“伪书”,但究其实,顾先生只揭示了这些东周秦汉史籍的生成层次,未做价值贬黜。如今,刘卓异的《治史与取径——陈垣、顾颉刚学术散论》,以要而不繁的严谨考证展现了两位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及后学的交互影响。
刘卓异师从晁福林教授,2019年以《两周列国族姓存灭考》获得博士学位。晁老师是援庵先生得意门生赵光贤教授的硕士,也就是说,作者是援庵先生的直系后学。而作为先秦史学者,谁也不可能脱离疑古思潮的影响。正如作者自云,本书所关怀的是不以经学名世的援庵先生,何以教出像赵光贤先生这样的先秦史家;两支风格迥异学派在北师大历史系如何相互影响。作者在为自己寻根的同时,也展开了一幅久违的学术史画卷。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钩稽史实,梳理了援庵先生与顾先生的交往与矛盾,并粗略描述了二人学术旨趣和风格的异同;第二、三章分别讨论了援庵先生和顾先生的古史观,尤其强调援庵先生的经学素养及对疑古派的看法,还原了顾先生疑古学说的真义和旨趣;第四章分析援庵先生弟子赵光贤先生对顾先生疑古思想和古史考证方法的接受,评述了赵先生曾用作授课讲义却并未正式出版的油印本《中国考古学大纲》;第五章综述顾门弟子赵贞信先生与顾先生的交往始末,及其在援庵先生身边工作的际遇与贡献。全书可谓结构均衡、富于巧思,体现了两系传承相互缠绕和影响的学术关系。

顾颉刚
由于流传至今的上古史料数量不多,先秦史研究者往往练就了精读文本和爬疏史料的专长,作者将这种专长移植到学术史研究中,不仅细读了前辈学者的相关著作,更系统研读了大量相关档案,哪怕脚注中也时出精见。例如,有学者依据商周时期并不大量使用金属生产工具,认为当时的君主并不是王,而是部落酋长。赵光贤先生对这种观点提出批评,却并未点名。为确定赵先生批评的对象,作者翻阅了大量著作,最终确定出自尚钺先生的《中国历史纲要》。这样的爬疏在第五章为赵贞信先生作传时得到了充分发扬,甚至为搜寻这位“终身”讲师的生平,作者竟查阅了今人撰写并于1993年出版的《富阳县志》,从中发现了四百字重要文献,并根据与此看似毫无关联的《富春茶话——诗书画文颂安顶云雾茶专辑》,进一步确定这则文献出自赵贞信同村族人夏家鼐之笔。这一考索信而有征,但我们无法计数为找这则文献作者下了多少苦功。只有这样的精雕细琢,才能保证学术史研究的切实可靠。
正如张政烺先生经常利用清人著作研治先秦史,据此做出了深入肯綮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本书也是作者对疑古思潮长期思考的结果。对具体问题做过深入探讨的专家撰写学术史,其优长恰在于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并能对具体问题做深入的讨论,这是学界所深切期望的。
然而,毕竟也不能回避作者在知识面上的局限,例如全书的重点完全侧向了先秦文献,而似乎从未深论援庵先生研治元史的具体方法,以至于在比较顾先生《尚书》学与援庵先生元史研究方法时,只发现二人研究计划都由“编工具书”“整理典籍”和“问题研究”组成及两者都从中年开始学习语言(古文字和蒙文)却都不够深入。这两点结论着实让读者感到意犹未尽。当然,对先秦史学者而言,在评定《封氏闻见录校注》的价值时作者非常内行地征引了黄永年先生的《唐史史料学》,可见作者文献视野已经很宽阔了,要求一位学者同时掌握先秦和元代文献,并有具体研究体验,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如果一定要以“文人的刻薄”提出书中我不甚同意的观点,大概也有。作者据援庵先生1919年发表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有“犹太族何时始至中国,据弘治碑则言来自宋,据正德碑则言来自汉,据康熙碑则来自周”,认为“这是典型的对于层累现象的表述”,这种挖掘未免失之过深。援庵先生只是对三个碑所记史事做了类比,而恰好暗合了“记载早事的材料晚出”这一情况,如此说来,顾炎武《日知录》谈“九州”称“禹画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后”岂不抢夺了顾先生关于层累学说的“创造权”?衡量学术贡献,关键要看是否以清醒的意识和严谨的逻辑完成了对一个问题的深入论证,除此之外,“猜想”“涉及”“言外之意”都不算数。
十年前我认识晁福林教授,却一直不知晁老师有收藏旧书的爱好,晁老师写文章引用的文献也未见雕印精美的珍稀善本。作者在后记提到晁老师购得赵光贤先生手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原来晁老师也有收藏旧书的喜好,这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个颇感意外消息。
2020年是援庵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晁老师作为援庵先生的隔辈传人,今年八十岁了,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目前研讨和传承援庵先生学术思想的学者在减少;同样,随着顾先生的学生辈的相继谢世和隔辈学生的逐渐老去,“古史辨”也不再如上世纪末般堪称文史研究的显要方法。学术史研究不是“论资排辈”,彰显“自家高贵的学术统序”,而是回首来时路,通过重复常识与探索新知检视以往研究中忽视的面向,促进学术观念的交融与更新并校正未来的学术方向。刘卓异此书立足扎实的先秦史研究经验,考述援庵先生与顾先生及二人后学的学术交谊与分歧,考索和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史问题,虽篇幅不大,却卓有实绩。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