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有较为严重的电量焦虑和死机焦虑。我本来以为,这种焦虑是源于与外界失去连接的恐慌,直到某个周六的傍晚,我才发现,有比跟外界失去连接更值得恐慌的东西。
那天我刚和朋友见完面,婉拒了他们的晚餐邀请,从咖啡馆走回家。刚进家门,拿起手机要看时间,发现手机死机了。我把手机插上电源,开始在电脑上搜索手机死机的各种解决办法,从百度到谷歌,试遍了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组合键重启方式,手机依然倔强地黑着屏幕。我的焦虑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了顶峰。
但是,抛物线规律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适用的。“还好电脑还在正常工作”,我心想,而且今天好像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跟人联系。于是,我从焦虑变得认命,甚至感觉到了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莫名其妙的轻松。我试图理解这种不合时宜的轻松感,好像是手机毫无征兆的死机,让我理所应当地把自己放在一个无任何社交干扰的空间里,可以安静地专心地做一些事情,不需要再被手机控制。
“社交过载”,我脑子里出现这么一个短语,用以总结现代人无时无刻不在人群中的生活状态。不管主动还是被动、线上还是线下,我好像处于这种状态很久了。
客观来看,高频度社交确实让我们与一些人建立了亲密关系,我们是互相信任的好朋友,是合作很久的工作伙伴,是伴侣。哪怕现实中不会每天见面,但线上仍能时刻保持联系。然而,时不时地,在推杯换盏间、在看着对面的人不断述说着什么时,内心会升起疑惑,我是谁?他是谁?他们是谁?在手机死机、被动抽离社交活动的现在,我终于有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偶尔觉得跟任何人都没有特别的亲近感和亲密感,以及由此产生对所谓的“社交”的质疑。
不得不承认似乎真实存在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我自己好像对别人并没有发自内心的亲近和关心,这也应该导致了另一种完全不客观的情况——我觉得别人对我的关心、友善、帮助等等行为,也是出于角色和礼貌。
这难道也是一种“现代病”吗?是一种“大都市病”吗?抑或是,从古至今在人类社群里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想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了索尔斯塔《第11部小说,第18本书》里主人公最后那荒诞的行为。
当意识到这种莫名的或者说原始存在的虚无感时,我们必然会本能地感到不适,于是有了质疑,有了思考,然后试图采取一些行动来反抗这种虚无感。这些行动可能是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交关系、重新审视自己,也可能是更激进的、更戏剧性的,比如主动切断一些联系,比如像索尔斯塔的小说里主人公把自己变成残疾人。但是之后呢?我们是否可以在切断联系这个行为的过程中发现什么真谛?这种激烈的扭转社交虚无的荒诞行为是否真的如想象般有效?在自己人为制造的社交真空或其他荒诞的状态中,我们是否真的会感觉更加接近真实、更加舒适?
不难预测的是,无论是哪种方式和哪种意义的“切断”,可能都难以持续。有两方面的原因大概可以解释这种必然的失败:第一,熟悉的日常生活状态的惯性实在太大;第二,为了解决社交的虚无从而选择进入只有自己存在的状态里,但随即便被完全面对自我时那种更深的虚无吓退,再次回到那个熟悉的人群。
傍晚,窗外层楼之后的夕阳已落下大半,呈现出鲜亮的橘色,周围的云也被一层一层地染成橘色、浓粉色、浅粉色,再是调色盘很难调出的粉蓝色。我看着黑着屏幕的手机感到一丝惋惜,想着如果手机没有死机的话,就可以把这漂亮的落日晚霞拍下来了,发到群里、发到朋友圈、发到微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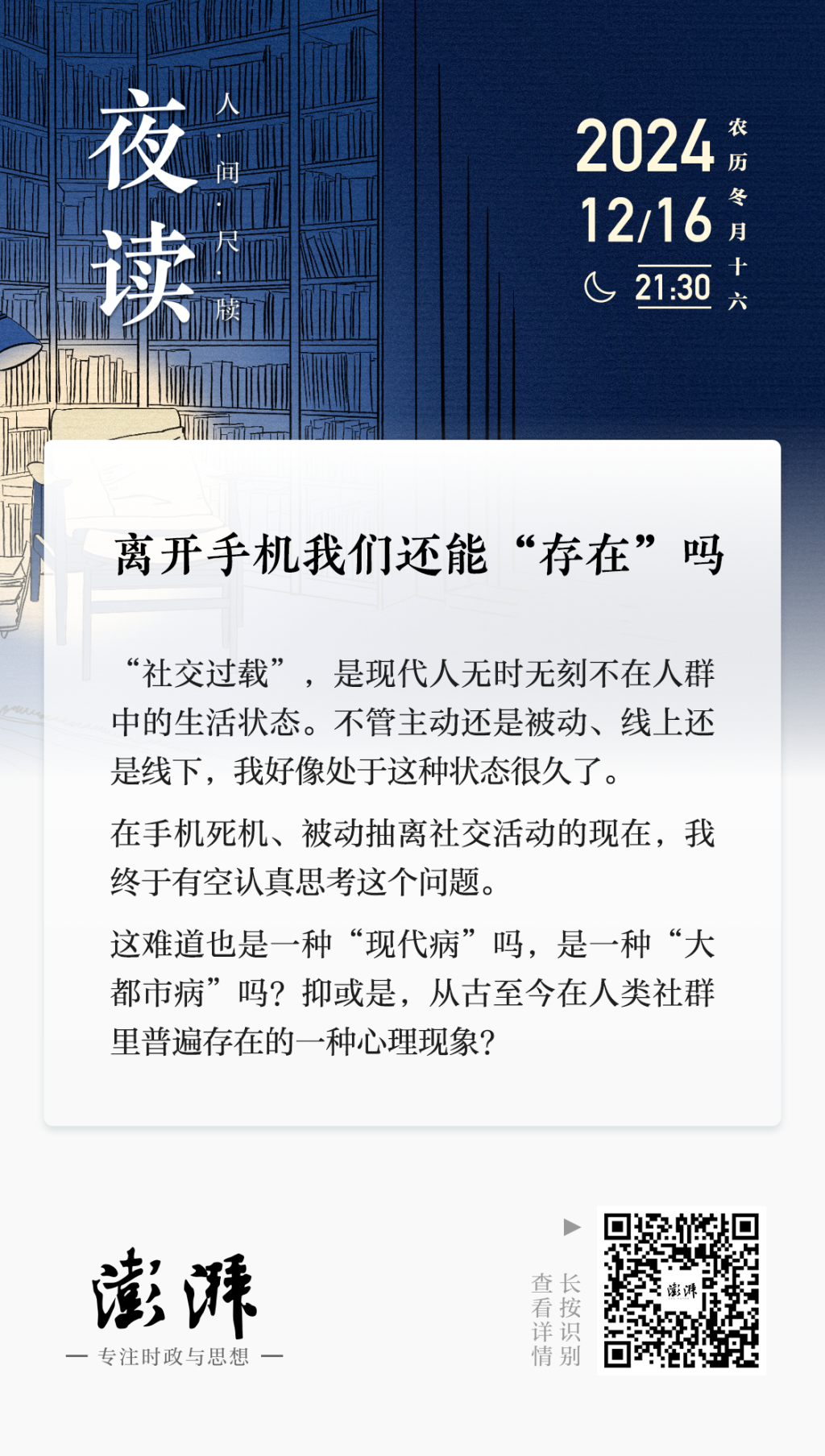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