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方纳教授的《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以下简称《重建》)是一部关于美国人在内战之后“再造国家、重建社会”的历史经历的著作,原著于1988年出版,2014年,该书出了25周年纪念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经典著作。在原著首版36年之后,今年4月《重建》的中文版问世。翻译这本书有何意义?译者王希教授谈了三点:知识的补充,知识的深化,方法论的启示。
“第一,《重建》为我们提供一种视野全面、内容丰富、具有深度的重建史叙事,这是对美国史知识的补充。虽然重建是美国史的重要一段经历,但在美国史研究和写作的中文文献中,国内一直没有一本关于重建史的通史著作。第二,阅读《重建》可帮助我们加深对当今许多美国问题的思考,包括公民权利的界定、新旧种族关系的博弈、联邦制的羁绊与优势、良性与恶性的政党政治、恩惠制的滥用、资本势力与政治的联姻、美国保守主义的激化、政治恐怖主义的泛滥等。这些现代美国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重建时代。重建时代制定的三条宪法修正案——第十三、十四、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是美国“第二次建国”的宪政成果,也是今天美国政治运作的重要基础。了解重建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困扰当今美国政治的原因所在,也能帮助观察美国政治改革的走向与动力。第三,《重建》从方法论方面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如何用综述的方式来处理宏大叙事,如何解读草根政治史并将其融入到意识形态和立法政治的历史叙事中,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书写中国的革命故事和改革故事。”
近日,北大文研院组织了《重建》一书的读书会,题目为“美国有‘翻身’和‘土改’吗?——《重建》的中国视角”,希望将美国史问题的讨论带出专业之外,将其他专业的学者带入到对美国史问题的讨论中来。本文内容系王希教授在读书会上的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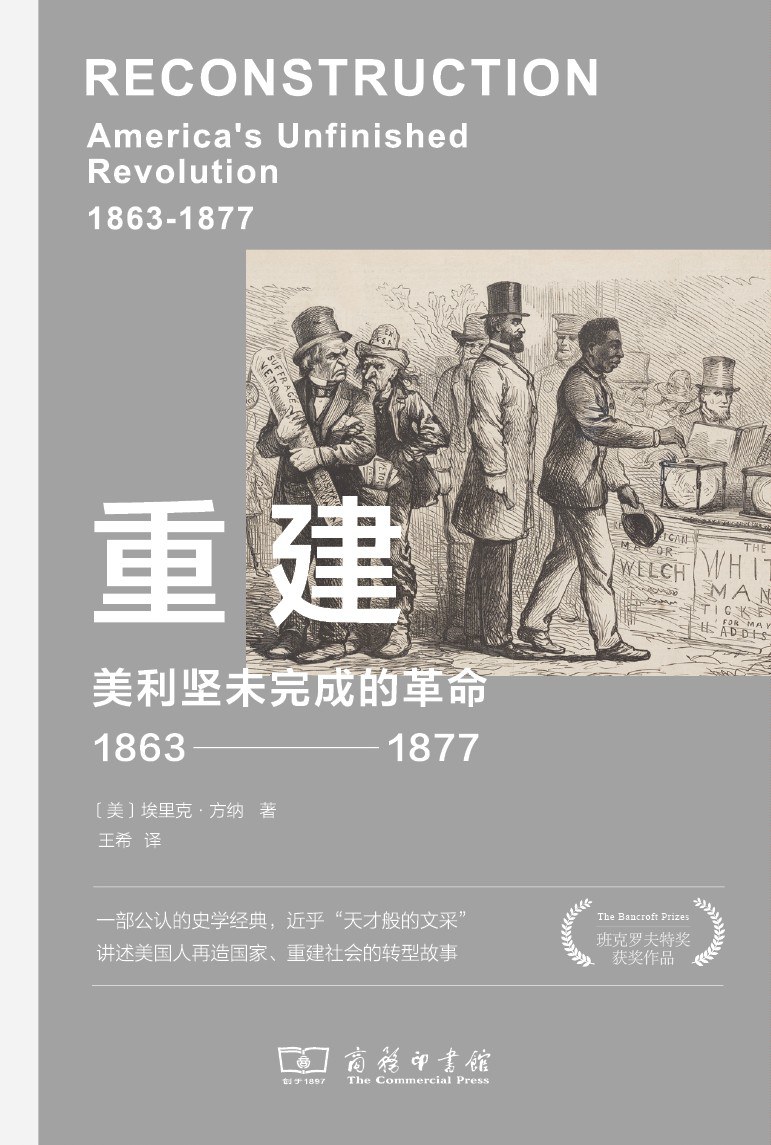
本次读书会的题目叫“美国有‘翻身’和‘土改’吗?——《重建》的中国视角”。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题目,看起来简单,细读一下,觉得含义很深。看来,组织人是鼓励我们从非传统的美国史视角来阅读或解读美国史。这对我很有吸引力。今年七月,我在上海参加过陈恒教授组织的一场关于《重建》的讨论会,会上几位研究拉美、欧洲和非洲史的学者对《重建》的评论给我印象颇深,启发也很大。我很喜欢这种跨领域的思想碰撞。
我也感到这个题目很有挑战性。组织人似乎在暗示我们将美国重建史与中国革命史进行比较,这一点对我有极大的压力。“翻身”与“土改”都是中国革命史的经典题目,而我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薄弱,对“土改”史的了解停留在普通读者的水平上。
我同时也意识到做比较史学的潜在风险——即如何在背景和内容不同的历史进程之间找到可比性。换句话说,美国重建史是否可以与中国革命史相比?从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内战中获得解放的前奴隶的经历是否可以与二十世纪中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过“土改”的中国农民的经历相比较?此外,即便两者具有某种可比性,这样的比较对我们理解中国史和美国史有何启示?这些都是比较难的问题,而且我没有答案。但它们又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探讨。今天正好有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专家在场,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冒险尝试一下,抛砖引玉。
从可比性来讲,我觉得美国重建与中国“土改”是有可比之处的。我们不妨提出一种假设,重建和“土改”是中美各自国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刻,其核心内容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使众多的受压迫者获得普遍解放;如果我们将人的解放——尤其是受压迫者的普遍解放——视为一个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时刻,美国重建和中国“土改”的历史就有了一个可信、可行的比较研究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讨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比如什么是解放?解放的进程是什么,含义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等。为什么中国的“解放”(无地和少地农民在“解放”后获得了土地)比美国的“解放”(前奴隶没有获得土地)进行得更深入和彻底?美国的“解放”为何被局限在“路径依赖”的困境中而无法推进?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做这种比较研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所幸的是,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二十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部著作已经就中国农民与美国奴隶获得解放的历史时刻进行了比较。著作的作者专注于讲述二十世纪40年代末发生在中共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我相信在座的老师和一些同学已经猜到了这位作者是谁。
这位作者便是被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他的著作名叫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于1966年在美国出版。周恩来总理得知该书出版的消息后,曾敦促将其翻译成中文。中文版最终于1980年出版,名曰《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右为韩丁(William Hinton)
韩丁受埃德加·斯诺著作的影响,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1945年来到中国,最初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参与了重庆谈判,并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有过交谈。国共谈判破裂之后,他成为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于1947年到中国河北冀县,为解放区培养农机人员。[韩丁的行动也影响了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室友Sid (Irwin) Engst(阳早)和自己的妹妹Joan Hinton(寒春)。阳早是奶牛饲养专家,寒春曾是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核物理科学家,两人于1940年代末先后来到中国,在延安结婚,后进入解放区帮助发展奶牛养殖业,并将毕生献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韩丁的前妻史克也在早期来到中国,1954年与韩丁离婚后一直留在中国,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师,直至去世。]1948年,韩丁到暂时迁居山西长治的北方大学教英文,正好遇上《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与实施,他被批准以观察员身份到山西潞城县张庄村去观察“土改”运动。他和翻译在张庄待了6个多月,通过实地观察和采访,做了数千页的笔记,为后来创作《翻身》准备了基本素材。1953年,韩丁返回美国,正遇“麦卡锡主义”肆虐之时,他被冠以“叛国者”罪名,受到国会的调查,遭受政治厄运,无法获得教职,在宾夕法尼亚州务农十多年。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初,他通过申诉要回了被美国政府没收的张庄笔记,最终写出《翻身》一书。《翻身》出版后很快成为美国社会了解中国“土改”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极有价值的实录性著作,也成为美国大学中国史研究和教学中的必读书。
《翻身》讲述的是1948年春夏时期发生在张庄的“土改”故事。在韩丁看来,“土地改革”(land reform )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核心内容,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压迫之下的无数贫苦的中国农民而言,“土改”是帮助他们从旧社会中走出来,获得解放,成为新人的一个历史过程。韩丁在观察张庄的土改运动时,敏锐地捕捉到“翻身”这个汉语词,并将之用来作为他著作的主标题,而没有采用“自由”或者“解放”。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英语词汇中没有其他能够表达“翻身”的内涵的词汇吗?韩丁在其著作的开篇页对此作了解释。他写道:
Every revolution creates new word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reated a whole new vocabulary. A most important word in this vocabulary was fanshen. Literally, it means “to turn the body,” or “to turn over.” To China’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landless and land-poor peasants it meant to stand up, to throw off the landlord yoke, to gain land, stock, implements, and houses. But it meant much more than this. It meant to throw off superstition and study science, to abolish “word blindness” and learn to read, to cease considering women as chattels and establish equality between the sexes, to do away with appointed village magistrates and replace them with elected councils. It meant to enter a new world. That is why this book is called Fanshen. It is the story of how the peasants of Long Bow Village built a new world (William Hinton, Fanshen, p. vii)。
[每一次革命都会产生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全新的词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是“翻身”。字面意思是“将身体翻过来”或“翻转过来”。对中国数以亿计的无地和少地农民来说,“翻身”意味着站起来,摆脱地主的束缚,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意味着摆脱迷信,学习科学,摆脱“睁眼瞎”(愚昧)并学会读书识字,不再把妇女视为他人的财产,建立男女平等,废除被任命的村长,代之以经选举产生的农会。“翻身”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叫做《翻身》。它讲述了张庄村的农民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故事。]
韩丁对“翻身”的理解非常生动,也非常深刻。在他的理解中,在描述“土改”时期中国农民的经历时,用“翻身”比用“解放”(liberation)一词更好,也更准确。“翻身”和含义更深,更广,它不仅仅意味着受压迫的贫苦农民要获得“解放”,而且还要获得一系列能够支持和维护“解放”的能力,包括分得可以谋生的土地,摆脱地主阶级的控制,抛弃封建迷信的影响,学习文化与科学,建立男女平等,选举能够掌权的农会。在他对“翻身”的总结中,韩丁还指出,“翻身”追求的不只是农民个体的解放,而是整个农民群体和阶级的解放,而农民本身也需要通过“翻身”从旧社会的“被动的受害者变成新世界的积极建设者”(Hinton, Fanshen, p. 609)。
在韩丁的理解中,“土改”是中国农民得以翻身的核心进程,为此他在书中将1947年颁布实施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视为中共革命的最关键的文献,将其全文翻译成英文,将其中的第六、第八条视为核心之核心。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一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第二条),废除一切土改前的乡村债务(第四条),由乡村农会接受地主的一切土地及公地,并按乡村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第六条);乡村农会接受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和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并分给地主同样一份(第八条)。(Hinton, Fanshen, pp. 7-8, 615-618)。
韩丁在前页部分介绍了土地法大纲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将土地法大纲与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做了比较。他认为,1947年土地法大纲在国共内战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其重要性相当于“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对于1861-1865年美国内战的重要性”(Hinton, Fanshen, 8)。
为什么这样认为呢?韩丁写道:“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无偿没收了价值30亿美元的奴隶财产;终结了工业化的北部和蓄奴的南部在激烈的军事较量中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将奴隶制本身而不是南部追求的区域自治变成了南北冲突的核心问题;为招募数十万被解放的黑人加入联邦军队扫清了道路;并将战争蔓延到邦联领土的每个角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Hinton, Fanshen, p. 8)
土地法大纲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力。根据韩丁的分析:“毛泽东的土地法(草案)无偿没收了价值200亿美元的土地;终结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一切可能的妥协;将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地主和买办政权作为内战的主要目标,而不是只是保卫解放区:土地法敦促蒋介石军队中的大批壮丁士兵逃离和加入人民解放军;激发中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并推动国民党后方各中心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和专业人士举行抗议示威”(Hinton, Fanshen, pp. 8-9)。
韩丁强调,土地法大纲并不只是一份政治文献,而是为了配合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在军事上从战略防守转向战略进攻的一种战略决策。土地法大纲宣示了将“耕者有其田”作为“土改”的基本原则,这是一种对在农村人口中占大多数的亿万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政治承诺。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土地法大纲颁布后,随着“土改”运动的展开,解放区翻身农民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纷纷掀起“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先上战场、全家上阵支前忙”的热潮。“土改”运动同时也对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的“壮丁”士兵和国统区的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可以看出,韩丁之所以将中共的土地法大纲与林肯的解放宣言进行对比,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两个历史文献在中美两国的受压迫者寻求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相同的关键作用。韩丁的比较史学到此为止,停留在“翻身”的开始。他没有比较中国的“土改”与美国的重建。但他的比较却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或设置了一个问题:为何从中美两国看似类似的“转型革命”(transformative revolutions)中所产生的“受压迫者的解放”却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或者更直白地说,为什么美国的黑人奴隶只是获得了“解放”而没有获得“翻身”?
韩丁是对的,中共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与林肯的《解放宣言》的确有可比之处。两者都是在战争中产生的文献,都宣示一种普遍的“解放”——中国的贫农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下获得解放,美国奴隶将从种族奴隶制下获得解放。林肯在1863年1月1日生效的《解放奴隶宣言》宣示,所有生活在南部邦联各州和各地区内的奴隶“即刻地和永远地获得自由”,联邦政府与联邦军队将“承认和维护”前奴隶的“自由人”地位,允许获得自由的黑人在受到人身威胁时进行自卫,鼓励他们参加劳动并获取“合理的工资”,邀请身体条件合格者加入联邦军队,为联邦而战。林肯将他的行动称为是“一个正义之举(an act of justice)”。
正如方纳在《重建》中指出的,林肯在经历了最初的犹豫之后,认识到废奴已经不可避免,颁布了解放宣言,而这份文献将联邦的存活与奴隶制的废除连接起来,改变了内战的性质,并预示着联邦的胜利将在南部内部产生一场社会革命。1861年底,林肯曾告诫国会不能将内战变成一场“暴力和无情的革命斗争”,然而他的解放宣言却将内战变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暴力革命,最初没有预料的奴隶解放成了这场革命的最重要的结果。这里我们看到中美“解放”的关键不同:一个是有目的的“解放”行动,一个随机引发的、事先没有准备的“解放”行动。
方纳指出,《解放宣言》中最为激进的内容是征召获得解放的黑人加入联邦军队。这个举动成为后来“激进重建”的起点。正如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1863年7月指出的,当一个黑人穿上联邦军队的军服、扛起枪为捍卫联邦而战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否认他已经获得了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 然而,公民资格和平等权利并没有随着黑人的入伍而自动降临,送到黑人的手中。事实上,加入联邦军队的黑人士兵一开始没有得到与白人士兵的同等待遇,他们的每月军饷比白人士兵少3美元,并且不能晋升为军官。在遭到黑人士兵的抗议之后,国会在1864年修订法律,在所有联邦士兵中实施同等待遇制度。这应该是非裔美国人以集体抗议的方式向联邦政府争取平等待遇的最早实践。
林肯在1865年4月遇刺身亡之前已经意识到,仅仅“解放”黑人是不够的,为了让黑人有能力维护自己的自由,他们必须被赋予公民资格和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公民权利。废奴主义者与激进共和党人也竭力推动战后重建朝这一目标迈进。在国会讨论制定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时,最激进的方案是宣布所有前奴隶不仅拥有自由,而且拥有白人所拥有的所有权利。然而,最终通过和批准的修正案只是宣布在美国全国境内禁止奴隶制,对林肯的宣示的“普遍自由”(或奴隶的“普遍解放”)的原则进行了宪法上的确认,而将自由民(freed people)的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的赋予留给南部各州在“回归”联邦后去处理。不料在总统重建方案下回归联邦的南部各州白人政府拒绝给予黑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待遇,国会共和党人最终借“一党独大”的立法权势,通过了《1867年重建法》,强制性地将选举权赋予自由民,改组了南部的选民构成。新重建的南部州政府最终在1868年批准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黑人的美国公民资格和平等权利才得到州政府的承认。
如果说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普遍自由”的宪法原则,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则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随后通过的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实质上确认了男性黑人拥有投票权的原则。这三条宪法修正案构成了重建宪政革命的核心内容,也成为美国“第二次建国”的宪政成果。方纳的《重建》对这一过程有非常翔实、深入的讲述。
重建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核心问题是如何将400万前奴隶变成拥有平等权利、经济上自主的公民,以及如何将普遍自由、种族平等和跨种族民主等新宪政原则付诸实践。重建时期最激烈的政治冲突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光有“自由”和“解放”是远远不够的。自由和解放的维护必须依靠政治参与、公民资格的平等、经济正义以及社会权利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建构黑人自己的社区、知识、文化和认同等。获得解放的黑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此刻马克思主义尚未成型),但他们拥有一种朴素的认知:没有经济上的解放,不会有真正的解放。
这种认知在黑人领袖与联邦军队谢尔曼将军在1865年1月12日的对话中表现出来。谢尔曼佐治亚州的一群黑人领袖他们理解的自由是什么,黑人代表加里森·弗雷泽(Garrison Frazier)回答说,自由就是“把我们放在我们可以收获自己劳动果实的地方,由我们自己来照顾自己”(placing us where we could reap the fruit of our own labor, take care of ourselves),而实现这自由要求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拥有土地,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来耕种它”(the way we can best take care of ourselves is to have land, and turn it and till it by our own labor)。这是有证可查的黑人对土地分配的要求。所以,耕者有其田,不仅是中国贫苦农民的要求,同样也是从奴隶制中走出来的前奴隶们的要求。
与黑人领袖会谈四天之后,谢尔曼将军发布了第15号特别战区命令,将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至佛罗里达三州沿海领土的一部分划分出来,将这个范围内的被种植园主抛弃的土地用来安置尾随他军队的黑人,每户黑人家庭可以获得40英亩的土地,并可借用军队的骡子,作为耕种之用。于是“四十英亩土地加一头骡子”(forty acres and a mule)的说法由此而起,响彻南部,激发起获得解放的黑人对经济上做到独立自主的无限想象。一位弗吉尼亚的黑人士兵甚至认为他将生活在“一个伟大而进步的时代”之中。
然而,这个“伟大而进步”的时代最终没有到来,土地分配最终并没有成为现实。正如方纳所讲述的,安德鲁·约翰逊在林肯遇刺、接任总统之后,否定了自由民局将种植园主弃置的土地分配给自由民的提议,并下令让获得谢尔曼分地的自由民将已经耕种的土地退还给前种植园主。国会共和党人虽然在民权立法和重建官员任命的问题上可以与约翰逊针锋相对,但除个别激进共和党人之外,没有人支持在南部实施土地再分配,也没有人阻止约翰逊的退地政策。自由民所希望的土地再分配化为泡影。
因为经济上没有自立,绝大部分获得解放的前奴隶们最终成为分成制(sharecropping)下的无地劳工。他们拥有自由,但仅仅是一种一无所有、任人剥削的自由。经济上的极度贫困将许多人推到南部农业“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随着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和联邦政府从激进重建的后撤,南部各州政权相继回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手中。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南部黑人的政治和公民权利遭到进一步的剥夺,陷入到无权、无势、无经济自立、无社会尊重的二等公民的困境之中。用黑人学者杜波伊斯(W.E.B. Du Bois)的话来说,“奴隶们获得了自由,在阳光下短暂地待了一会儿,然后又被推回到奴隶制中”(方纳:《重建》, 1004页)。
重建为何没有产生或者无法产生中国“土改”那样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做一篇大文章,甚至一部专著。在这里,我想从重建和“土改”发生的历史背景、两者的目的、思想与体制条件、改革者的准备以及暴力的使用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供批判和讨论。
首先是“解放”进程的发生与新秩序的降生。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废奴是联邦政府因战争需要而作出的决定,奴隶解放是内战前事先没有预料的结果,所以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在战后重建开始时都没有将自由民(获得解放的前奴隶)的权利和经济自主作为重建的目标和内容。林肯和约翰逊的总统重建方案都是以南部的迅速回归为首要目标,而不是黑人的权利与经济自主。虽然有20万黑人士兵参加了内战,并有黑人军团在关键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们只占200万联邦军队人口的十分之一,其重要性未能得到足够的承认。内战时代的中共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解放受压迫的农民、推翻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政府、夺取政权为主要目标,并将广大农民对战争的参与与战争的胜利密切联系在一起;提出和推动“土改”既是对农民群体的政治承诺,也是为了保证解放军能够长期而稳定地获得农民人口的支持。所以,农民的解放与中共革命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分歧和意外。事实上,1947年之后,“土改”与解放战争是同步进行的。
第二,在主导重建的北部共和党人眼中,重建的目的不是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也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奴隶主阶级,而只是废除奴隶制,在南部建立一种以“自由劳动”(free labor)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而这个新的经济体制的核心仍然是财产权优先、财产权至上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唯一不受保护的是前奴隶主拥有奴隶的财产权。林肯的解放宣言和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以无偿的方式剥夺奴隶主的奴隶财产,但当前南部邦联成员放下武器、宣誓效忠联邦之后,约翰逊总统便命令将没收的土地予以归还。从土地拥有和经济资源的分配上来看,内战和重建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经济体制,也没有足够强大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力量来启动和支持这种改变。而中国的“土改”则是一场由上而下的、经过策划和思考的、通过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来实施的、并深受贫困群众拥护的制度革命。虽然“土改”的策略与实施会因时因地而异,但其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推翻旧的土地所有制,根除旧的乡村权力结构,让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新的土地和经济资源。
第三,重建的立法进程遵循的是已经成型的宪政原则和程序,虽然针对极端情况国会会做出超出常规的立法(如采用《1867年重建法》这样的强制性措施),但整个过程基本是一种遵循既定程序的有限“革命”。即便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公民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包括从前奴隶主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极少数激进共和党人提出的土地再分配改革建议,虽然在道德上具有崇高性,但在政治上为许多共和党人所反对。经济正义(economic justice)所强调的原则不是“平均地产”,而是自由劳动者的“自力更生”,实质上是坚持对私人产权的捍卫。中国“土改”则是针对土地所有制的一次真正的革命。“土改”之所以能够推进,因为它首先是在中共控制的解放区中进行的。正如韩丁所描述的,中共不仅在解放区拥有政治控制权,而且还能够通过其工作队,深入乡村社会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土改”是一种对新的经济秩序的设计,中共因为掌控了绝对的政治权力,也拥有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空间。但在美国重建时期,传统联邦制和联邦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对联邦政府企图追求的改革形成遏制力,国会通过任何一项具有改革性质的立法都需要艰巨的谈判和无数的妥协。推动即便是最温和的土地资源分配政策(如1866年针对南部的《宅地法》)也要面临重重困难。
第四,重建的来临显得突如其来,卷入的阶级和利益群体非常多,包括前种植园主、前南部邦联的成员、南部的白人自耕农、北部资本家,自由黑人、自由民、来自北部的理想主义的改革派和政治投机分子等。推进任何有效的南部重建计划,都需要在权力体制内建构相互呼应、步调一致的政治结盟力量,并需要获得基层选民的支持。但这种政治结盟——包括北部和南部共和党人之间的结盟,黑人与白人改革精英群体之间的结盟,普通黑人与黑人领袖之间的结盟——都没有能够长期而稳定地存在过。同样处于贫困经济地位的白人自耕农和黑人自由民此时因为种族主义的影响也无法在基层形成有效的阶级结盟。相反,种族主义反而成为在南部白人内部建构反激进重建势力的一种思想基础。方纳在《重建》中描述了一些具有理想主义的黑白政治领袖,他们具有改革意愿,也具备中国“土改”工作队队员的献身精神,但他们的人数不多,并无法构成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网络,并缺乏来自上层的组织和经济资源。
第五,南部的政治空间与政治暴力以及对奴隶解放的抵制。在整个重建时期,南部的白人反对势力,尤其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组成的KKK等武装组织,一直存在,顽强地抵制激进重建,凶狠地对打击黑人行使权力和争取经济自主的努力,并严酷地惩罚同情和支持黑人的白人盟友,政治恐怖的气氛笼罩在南部基层的许多地方。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推动即便是温和的重建改革显得异常困难,即便在黑人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也是如此。在中国“土改”运动时代,以土地法大纲为界,对农村阶级的划分比较单纯;农会在工作队的辅助下,发挥了主要的领导作用。而在美国南部的重建过程中,获得解放的前奴隶人群虽然通过教会、联邦同盟或群谊社团建构了黑人社区,开启了政治化的进程,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建设持之以恒、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许多住在乡村和偏僻地带的黑人更是处于政治上与外部隔绝的状态。
还有一个方面的因素值得考虑。从奴隶制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比来看,奴隶制是一种以种族为基础的强制性劳动体制,奴隶被视为财产,奴隶制所遗留的残酷影响(包括对奴隶人格的摧残和对黑人文化的破坏)非常巨大。而中国农民在人身上并不完全依赖于地主阶级,一旦得到外部力量的持续动员与组织,并从“土改”中获得经济利益,可以转化成为革命的力量。而种族主义思想与文化与奴隶制相伴而来,渗透在战前和战后美国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手中抗拒重建、打击黑人积极性的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之一。中国乡村的旧势力(包括“土改”时代的地主武装和恶霸势力)也对参加和拥护乡村改革的农民形成威胁,但相对于美国重建时代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而言,它们可以利用的组织、法律和经济资源都相对有限。
那么,我们如何评价重建呢?如何看待这场被方纳称为是“美利坚一场未完成的革命”?或者说,重建在美国历史上是不是一场革命?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历史学家争论了许多年。争论的分歧可以从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段所用的定义来表现,如:reunion, restoration, reconstruction, revolution。这些不同的用词说明不同历史学者对重建的不同解释。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革命”,以及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重建的结果。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重建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没有进行“土改”,没有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做根本的改变,前奴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没有获得“翻身”。重建也未能根除种族主义;相反,因为它的失败,白人种族主义者通过暴力建立起种族等级制,剥夺了南部黑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并将种族主义变成南部法律和生活方式,并一直将这种状态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重建是美国历史上一场革命。我不知道有没有middle revolution(中间革命)或transitional revolution(转型革命)的说法,我觉得,从宪政原则和政治运作来看,重建的确是一场美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革命。重建建立的三条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建立了出生地公民资格,赋予男性公民投票权的宪法保护。相对于第一次建国而言,这三个方面——普遍自由、公民权平等和跨种族民主——都是革命性的创举,也为20世纪的民权运动和延续至今为止的“权利革命”奠定了基础,等于重新界定了美国的建国原则。
方纳认为,重建创建了一个具有实权的、具有扩权潜力的联邦政府,改变了先前的联邦制下州与联邦政府的权力分割,关键性地遏制了州权至上的理论与实践,为美国的长存和安全提供了保障。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重建创建了一个新的拥有权利的公民实体,并且是一个可以持续增大的公民群体。这个群体拥有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一种注重权利平等的政治文化,形成一种新的遏制专制——无论是思想上、政治上或经济体制上的专制——的力量。
的确,重建的时间很短,而且最终未能持续下去。但它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让400万前奴隶行使自由人的权利,让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员,成为黑人学校的教师,成为黑人教会的牧师,成为黑人家庭的父亲与母亲,成为黑人艺术家、商人、自耕农和学者等。他们享受自由和平等很短,只有10年左右,但他们却创造了先例,为后代留下了珍贵的记忆,为20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二次重建保留了火种。
所有的革命和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行动,而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方纳的《重建》之后,又有大量新的关于重建的著作继续出版,有的作者甚至提出了“漫长的重建”(long Reconstruction)的概念,将民权运动视为第二次重建,与内战后的重建属于同一场“解放”运动。当今美国也有人在呼吁这个国家还需要进行第三次重建。从这个角度看,重建真的是一场还未完成的、还在继续进行的美国革命。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