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6岁的顾凡及,曾经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长期从事计算神经科学的科研与教学。退休以后,他开始写科普书,决定把科普创作和翻译作为自己余生的事业和追求,至今已出版16本科普著译,包括面向大众的科普读物《脑科学的故事》。12月8日,在“上图发布×世纪好书”月度好书精选榜发布会上,《脑科学的故事(第三版)》入选10月榜单精选作品。
“进入脑科学领域以后,我最大的感悟就是,‘Use it or lose it,’不用则废”,日前,澎湃新闻记者在上海的一家养老院里见到了顾凡及,如今,他基本保持着退休前的生活作息,每天工作大约五个小时,睡前,他会在手机上听听书,最近在读马伯庸的小说。作为脑科学研究者,顾凡及和国内外的脑科学领域专家保持联系,持续关注世界范围内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随着年纪的增长,大脑的衰退不可避免,但我相信,动脑能使这个衰退减慢,我现在的脑子还算可以,因为我一直在用脑,没有断过。”

顾凡及
【对话】
退休后开始写科普,关注人工智能动向
澎湃新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科普写作的?
顾凡及:我是在退休后才真正地开始科普写作。我不喜欢什么事都不做、每天只是看看电视的生活,我觉得科普是我能够做的事情。2008年的时候,我的第一本科普书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当时杨雄里院士来问我,愿不愿意写一本给小孩子看的科普书,我说我有时间,可以试试,就这样写出了《好玩的大脑》。之后我又继续写科普书,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脑科学的故事》第一版,这是我第一本写给广大公众的科普书,从那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一年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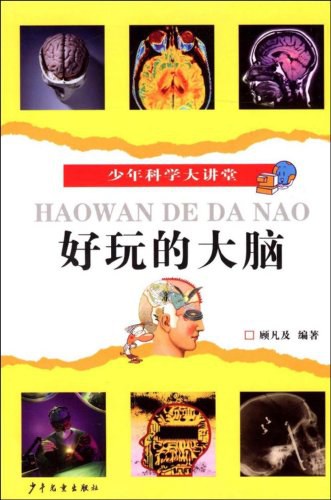
《好玩的大脑》书封
澎湃新闻:《脑科学的故事》第三版中增加了关于脑科学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比如脑机接口等,您对于这些最新成果的探索和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顾凡及:我原先从事的是计算神经科学的研究。退休以后,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进展,之后在进行科普工作的时候,也从各个地方积累材料、阅读和思考。我和同事合办过一本国际期刊《认知神经动力学》(Cognitive Neural Dynamics),和国内外的学术界朋友保持联系。在杂志的审编过程中,我收集了500个国内外科学网站,从上面获得了很多资料。我还从《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Mind)、《发现》(Discover)、《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等高级科普读物上获取信息。科普需要全面了解,我依据专业的教科书列出大纲,再以科学性、趣味性、前沿性作为标准,根据大纲来选择材料,把找到的材料收集到电脑或是纸质的文件夹里,之后在写文章的时候,方便查找。
澎湃新闻:您在书里写到和德国的退休信息技术工程师卡尔·施拉根霍夫邮件往来,交流人工智能的话题,关于未来的人工智能以及可能对人类带来的挑战,目前您是怎么看的?
顾凡及:人工智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对于人工智能,我只是一个有兴趣的外行,但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现在我不只是和卡尔保持联系,还有美国天普大学计算机系的王培教授等,我向这些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请教,和他们讨论,有时候也会争论。
以前我坚信,人工智能仅仅是一个工具,关键取决于人怎么使用它。现在我对这个观念有一点动摇。王培在书里讲到,智能系统有初始目标,对于生物来说,就是进化和遗传,对于机器来说,是工程师设定的目标。智能系统要实现初始目标,需要经历很长的过程,不断地和环境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许多派生目标,形成目标链,在这个目标链里,有些初始目标可能就消失了。我想,对我自己来说,研究脑科学、做科普可能就是我的派生目标,而不是初始目标,是随着我的经历和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我把派生目标和意志联系起来,在想机器的派生目标是否算是它的意志,当然这些还只是我自己的思考。
偶然进入脑科学领域,至今还在学习
澎湃新闻:您是把派生目标和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听说您本人是从数学专业转向了神经科学,这段经历是怎样的?
顾凡及:我在复旦大学数学系念到大四下学期的时候,偶然的机会被选出来做预备老师,负责给学弟学妹讲普通物理的课程,为此我去旁听了全部的物理系课程。之后又在机缘之下,被分配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当时他们恰好需要一个有数学背景和物理背景的老师。我进入生物物理系以后,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研究生物控制,包括给本科生编写生物控制论的教材,由此开始和脑科学打交道。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我去北京医学院听生理课,做生理学实验,又去北京大学旁听神经生理学的专业课程,慢慢地进入了计算神经科学的领域,后来,又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书。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计算神经科学没有正式的学科名称,处于神经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交叉领域,我总是先碰到任务,再去补相应的知识。直到开始做科普,我想要从头开始学习神经生物学的知识,我觉得博士也就是学习4年,我的前面绝对不止四年,我还用得起这个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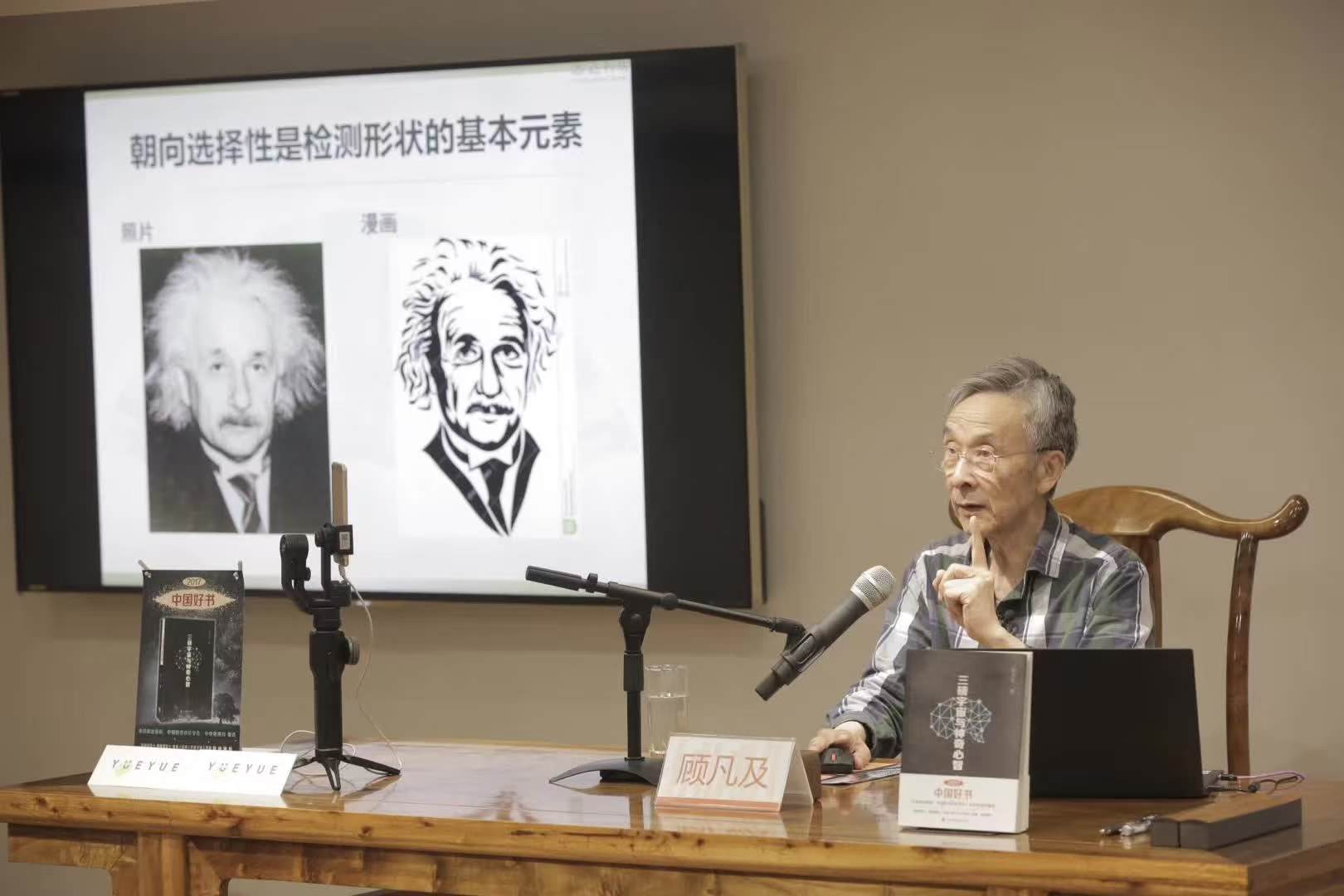
顾凡及做讲座
澎湃新闻:您如今每天的日常大致是怎样的?
顾凡及:我基本上是维持退休以前的生活方式。一般早上6点半到7点起床,8点参加养老院里的集体早操,之后从9点工作到11点,中间除了写作以外,也会处理电子邮件和手机信息。午饭过后,再工作一两个小时,然后午休,大概到下午3点的时候,继续工作两小时,晚饭以后,再继续工作。一天大概有五六个小时是在工作,中途也会去健身房做会儿操、跑会儿步,周末的时候也会看看电影。睡觉之前,我会在手机app上听听小说,放松一下大脑,然后晚上10点左右睡觉。一年365天,除了过节和聚会,基本上天天如此。
澎湃新闻:说到小说和电影,在《脑科学的故事》里,也能看到不少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引用。您对文学艺术也有很大的兴趣吗?
顾凡及:我从小就喜欢读历史和小说,尤其是传奇小说。可能说来惭愧,我读的往往不是被认为一流的作品,比如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我读了很多遍,其他三部我都没有看。武侠小说里我最喜欢的是金庸,最近我在听的是马伯庸的小说。国外的小说家里,我喜欢大仲马、梅里美、普希金、莱蒙托福这些,但有些比较深刻的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就看得很少。
保持好奇,保持活力
澎湃新闻:您从数学专业转向了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直到现在也一直关注人工智能、脑机结合等这一领域的发展,您对于脑科学持续探索的动力是来自哪里?
顾凡及:一个是好奇,一个是兴趣,想要搞好科研或者科普,都要有好奇心,要觉得这件事有意思。我自己要做这件事,我想这是我最大的动力。另外,年纪大了以后,我还是希望能够对社会有一点回报,觉得这样自己的生活比较踏实,也觉得这样好像自己仍然有活力。
澎湃新闻:如今您还在写新的科普书吗?
顾凡及:我现在手头有几本书要写。之前和卡尔合著了“脑与人工智能系列”,关于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热点和开发问题,这套书写到2019年中断了,之后又发生了很多新的热点和争议,比如欧盟人脑计划(EU Human Brain Project, HBP)终结,还有100多位科学家联署发文称综合信息理论是“伪科学”等等。怎么看待这些事,这是我现在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梁培基教授在合作写的一本书的内容。另外,我在准备《脑海探险》的更新版,也是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关于脑科学和交叉科学领域的新发展。在《脑科学的故事》里,有一章关于错觉,还有更多的材料没有延展,国外有作者写了一本《眼见非实》探讨错觉,我不太同意里面的观点,我正在写一本《错觉,魔幻世界背后的真相》,大约明年4月份交稿。除了书之外,我还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写稿,以及给一些杂志写短篇。大概每年维持在20万字左右。因为脑科学发展很快,不断地有新东西出来,要不断地学,学了之后,有些觉得好玩的、值得思考的东西就可以写出来。

《脑科学的故事》书封
澎湃新闻:对于现在正在从事脑科学的年轻人来说,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期望吗?
顾凡及:我羡慕他们生在一个好的时代。在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脑科学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脑科学的科普和研究也没有受到那么多的重视。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大量投资脑科学,我们国家也是,各个大学都有这方面的教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我想到一位已故的脑科学家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J. Freeman III)说过的话,他对年轻人的寄语是:你们背上没有成功的包袱。有些人成功以后,就沿着他原来的那条路线走下去,不愿意尝试新的事物,不愿意冒险,年轻人没有背负这些,完全可以去做你们想做的事。弗里曼还说过,脑科学要继续发展,一个要靠新的技术,一个要靠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需要国家投资,但是思想谁都可以拥有。
我看过很多科学家的传记,对照他们的成功,我觉得科学家要有三条品质:第一是好奇,这是他们的动力,有了好奇才愿意废寝忘食地去做这些事情;第二是质疑,不要觉得权威说的一定对,要自己用科学理性的思维去思考;第三是坚毅,坚毅不等于固执,你要常常质疑自己走的方向是不是对的。我念书的时候,没有老师的引导,也走了很多弯路,当然年轻人也不要完全相信我,通过你自己的实践来检验,如果发现我说的不对,就照你自己想的去做。各人头上一片天,后悔没用,我只想让我的余生过得开心、有意义。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