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7日,法国举行仪式庆祝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视觉中国 图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7日,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在巴黎举行,庆祝2019年失火的巴黎圣母院经过5年修复后重新开放。据巴黎圣母院介绍,8日还会举行庆祝仪式。从8日开始,巴黎圣母院正式向公众开放。
据报道,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总计耗资约7亿欧元(约53.5亿元人民币)。但另一条不太为人注意的信息是,这笔巨款之中,有大约一半资金是由少数法国富豪和私营公司捐助的,剩余大部分资金则依靠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地的私人小额捐助。
换言之,这项由法国政府发起的公共工程居然花的是私人的钱,政府仅提供了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事实上几乎成了“甩手掌柜”。巴黎圣母院修复重建的成功,再一次实践了私人资金生产某些公共品的优势和可能。
在博弈理论中,参与各方可能出于某些获益可能而采用相同的博弈策略,从而实现纯协调博弈(pure coordination game),各方协调获得最大收益。比如在狭窄的道路上两车相遇时,司机通常会默契地选择靠右(或靠左)行驶,安全无虞,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策略只会徒增风险。协调博弈下,参与各方有共同的兴趣和一致的利益,这类交易协议往往可以自我执行而无需第三方仲裁或强制。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的长老会、牧师、行会、法人城镇和商人辖区作为合同的执行者,实际上扮演的正是为协调博弈各方提供帮助的角色,奠定了自治传统的基础,直到后来,各种国王们才凭借其强大的统治权力设立起法院等第三方强力机构。
传统上,国家(state)背后的强力被认为扮演了保证契约履行、向社会提供诸如水利、交通、安全、法律等公共品的第三方角色。受此影响,主流经济学把“公共品”(public good/service)定义为消费上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物品(或服务)。而非竞争性,意味着所有人都是潜在的搭便车者,投资方无利可图,因而只能由政府提供。
多年前,诺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用英国17世纪领港公会建设灯塔的案例,从外部性的角度提出了公共品由私人供给的成功案例,有力地挑战了“公共品应该由政府提供”的传统观念。对此,有人反驳认为,受制于成本—收益约束,即使某些公共品能够由私人投资和生产,其供应量也将低于“最优”水平。但这一说法,显然无视了政府生产公共品也需要成本这一基本事实,而且所谓“最优”只是黑板上的抽象定义,在真实的市场中难以事先观察。
自掏腰包捐建巴黎圣母院无疑是一种典型的自发协调博弈,考虑到捐助者甚至获取不到任何实质利益,这种付出可以视为完全由个人需求或偏好驱动,而工程的成功则满足了捐资者的这种需求,其他人也获得了参观欣赏的搭便车机会。
将它与国家税收支持的公共品对比可以发现,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后者实际上是将基于个人需求的收益与付出进行了脱钩和分离,进一步地,按照詹姆斯·布坎南的说法,就连什么是公共品也由国家来决定(详见《同意的计算》)。一项并不满足自己需求却需要自己付钱(税收)的公共品,不仅意味着所有人都是潜在的搭便车者,而且拥挤的公地上,人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最优策略,是通过某种方式向政府要求更多符合自己偏好的公共品——收益高于自己的税负,而按照“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的揭示,公众偏好又是不可相加的。
此时,各自需求千差万别的搭便车者就异化成为剥削别人税款的人,而政府为了减缓或防止公地悲剧,要么在生产更多公共品的进程中成长为巨型利维坦,要么制定各种管制措施提高公共品的排他性,与宣称的“公共品”背道而驰。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奥马巴政府早年推出的医保制度、美国教育部主导的各类联邦科研基金等公共项目正是此类“公共品”的典型,而美国政府逐年上涨的赤字规模背后,或许也有公地竞逐的推动。
可见,公共品问题之所以成为普遍难题,并不是因为它的“公共性”,反而恰恰是因为出资人和收益人脱钩而导致的普遍“不公共性”。
巴黎圣母院这次由私人出资修建、私人和公众共同受益的协调博弈再次表明,公共品的生产并不一定需要排斥个人的自由选择,包括搭便车的自由。一旦私人资金与其需求偏好能直接相关,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往往能达成更优的资源配置和良好的正外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并非出于自愿而“被投资”的公共品,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公共”的。让真正喜欢它的人自愿掏钱,让爱搭便车的搭便车,或许是解决公共品难题可行的思路。
(作者何坤为农业投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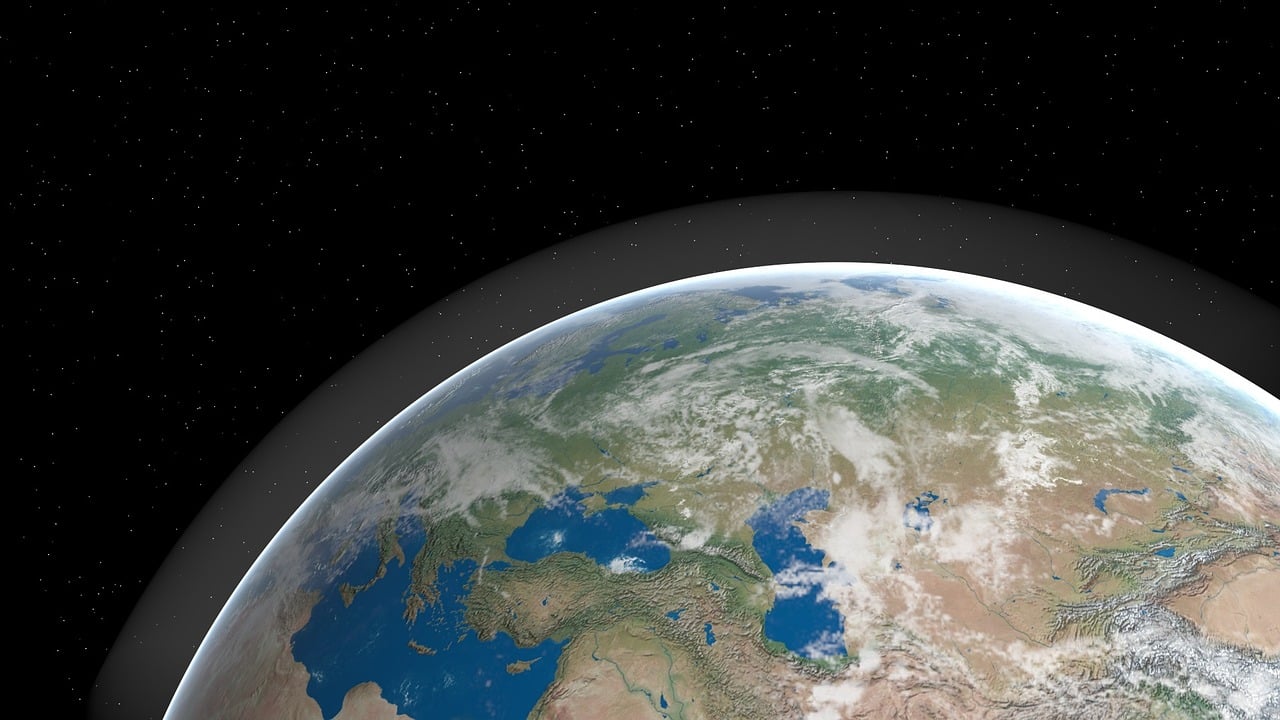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