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德森教授的夜晚》,[挪威]达格·索尔斯塔著,林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丨理想国,2024年11月版,352页,69.00元
挪威著名作家达格·索尔斯塔(Dag Solstad)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2022年由北京日报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第11部小说,第18本书》据说是达格·索尔斯塔的作品首次以简体中文版发行。达格·索尔斯塔曾获得多项文学奖荣誉,包括被称为“小诺贝尔奖”的瑞典学院北欧文学奖等,但是值得重视的理由更在于“他以清醒的头脑和存在主义者的眼光,关注着我们为生活做出的妥协、逃避和迁就……他诙谐而尖刻地讽刺了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就因为他对我们的妥协、逃避和迁就的关注与思考,以及回顾了我们曾经有过的燃烧的思想和叛逆的勇气,揭露了今天的个人与时代在当代生活中的巨大裂隙,真的值得我们阅读他的小说。
致力于翻译西欧文学作品的美国翻译家达迈·西尔斯(Damion Searls)在2015年发表于《巴黎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挪威文坛的四大元老”,说他们有点像披头士乐队:佩尔·佩特森(Per Petterson)是坚定的、永远可靠的林戈;达格·索尔斯塔(Dag Solstad)就是约翰,一位实验主义者、思想家;卡尔·奥维·诺斯加德 (Karl Ove Knausgaard)可以饰演可爱的保罗;约恩·福瑟(Jon Fosse)是乔治,一个安静、神秘、有灵性的人,也可能是他们中最好的工匠。我们知道,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给著名的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达迈·西尔斯把达格·索尔斯塔称作“实验主义者”和“思想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索尔斯塔多种头衔中,我认为像哲学思想小说家、政治小说家、现实主义者和文学煽动者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的作品的确时常会引发关于时代思想状况与文学探索的争议,他的文学创作早已成为了挪威思想界的一部分。
达格·索尔斯塔的《安德森教授的夜晚》(林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收录了他的两部代表作《羞涩与尊严》(Genanse og verdighet,1994)和《安德森教授的夜晚》(Professor Andersens natt,1996),他的思想性与实验性的锋芒在这部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羞涩与尊严》讲述的是生活情景中的一次偶然挫败所引发的精神危机的故事。这一天,五十多岁的高中语文与历史教师埃利亚斯·茹克拉在毕业班课堂上像往常那样,讲授伟大的挪威文学家亨利克·易卜生写于1884年的著名戏剧《野鸭》——“如果你剥夺了一个平常人的生活幻想,那你同时就剥夺了他的幸福。”这句挪威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台词就出自这里。他讲述这部戏剧已经有二十五年了,但在这一天遭遇了极为严重的挫败感。上课开始的时候,当他要学生把学校发的教材《野鸭》拿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他们的敌意,但他不理睬,只想着完成今天的教学任务。虽然学生都无精打采、昏昏欲睡——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手机可以帮助打发无聊的时光,学校管理层也还没有发展到要统计学生上课时的“抬头率”——他在讲述中突然发现了以前在研究和教学中从未注意过的问题和新思路、新见解,因此感到一种难以遏止的激动。但是这时下课的铃声响起,学生们已经马上“若无其事地经过老师身边走出教室,谁也没有朝他瞅一眼”(第9页)。第二节课他向学生提问,但没有任何反应,使他再次感到这样的授课真是一种折磨。达格·索尔斯塔详细描述了这位教师的内心纠结,在高中语文课中讲授经典作品时产生的种种无奈感:学生因提不起兴趣而感到无聊,他自己也对这种讲述的作用产生怀疑;虽然自己真诚地、仍然不乏热情地研究经典,但同时也悲哀地意识到那些感动了自己的经典文本对于眼前这些学生来说毫无作用和意义。但是在这些无奈背后的是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埃利亚斯·茹克拉想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的正式职业是坐在教室的讲桌后面,要求他的学生们阅读这些他们既不感兴趣也不太能理解的书。”(31页)他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种教学的无聊和乏味,而现在他在强迫学生接受这一套东西。
但是,这一天教学的挫败感还没有真正击败埃利亚斯·茹克拉。下课之后要回家的时候,下雨了,但是他的雨伞怎么也撑不开。更令他大为光火的是意识到周围有同事和学生在看着他——假如在这个时候他能够自嘲性地摇摇头、在细雨中走出学校,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他的情绪失控了,发了疯一样砸烂了那把雨伞,结果这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过程中看见了周围的学生目瞪口呆地,甚至是敬畏地围观他,使他怒火更旺。终于走出了学校,他开始号啕大哭。他想到自己的同事一定会挤在办公室的窗边看到了这一幕,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去面对目睹他失控的学生与同事,甚至想到无论同事们如何表现出淡化此事,说这是任何人都可能会出现的情绪崩溃,都无济于事。彻底崩溃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他只能离开这所学校,结束他的教师生涯。在街上的绵绵细雨里终于找到垃圾箱扔掉了那把倒霉的雨伞,他感到全身轻松了。但是此刻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现在站在这里胡思乱想合适吗,不是应该想想如何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吗?他不无嘲讽地暗自思忖着,或者想想要如何度过拿到第一笔养老金之前的这十五年”(49页)。“这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他想。这令人不寒而栗,但已无回头路可走。”(173页)
这只是一个开端。在教学中感到的挫败与失去理性的情绪失控导致他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折,他茫然地行走在街头,回忆起青年时代的往事、朋友、事业与婚姻生活的变化和曾经的理想和意气风发的生活,感觉自己与这个时代渐行渐远,对此无能为力——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化中被逐渐边缘化所带来的失落与无力感,这才是作者真正要讲述的故事。
《安德森教授的夜晚》的叙事结构和重心指向与《羞涩与尊严》类似,略有不同的是开头的事件仍然不断穿插在后面的故事之中。五十五岁的波尔·安德森教授独自一人在家里过平安夜,大约十一点钟,当他站在窗前观看对面公寓那些灯光明亮的窗户的时候,目睹了对面公寓里的一位年轻女子被一个年轻男子用手掐死。这是谋杀案,他告诉自己应该报警,但最终还是无法下定决心拿起电话——“‘我要说什么呢,’他想,‘我目睹了一场谋杀?对,这就是我必须要说的。然后他们便会嘲笑我,让我上床睡觉去……’”(189页)他继续盯着对面的窗户,头脑里出现了很多应该报警的理由,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报警。在接下来的白天,他去参加朋友的圣诞聚会,想要跟朋友聊一聊这件事,却始终没有开口;经过警局附近街道的时候,想到报了警就会放下这件事并且马上感到一阵轻松,但是同时他清楚知道自己不会走进警局。他为自己辩解的一种理由是凶杀已经发生了,这是无可挽回的既定事实,报警已经失去意义;至于凶手,他相信会被捉拿归案,但不应是由他介入其中并通知警方(199页)。这种心理纠结不断出现在整个故事之中,强化这种纠结的是与此同时他难以控制自己对于凶手的好奇心,因此他继续关注对面窗户的情况,迫切地想要知道有关他的一切。于是在整个圣诞以及新年假期里,他渐渐了解了凶手的名字、样貌乃至活动规律,也曾跟他擦肩而过。更为荒诞的一幕是,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他在家附近的一个日本餐馆里与凶手比邻而坐,有了交谈的契机,甚至一起散步回家,甚至还约了去看凶手的赛马首秀。安德森教授最后想到的是去洗一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这件谋杀案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小说也就写到这里。
在目睹谋杀案发生之后,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的悠闲日子里,安德森教授与朋友约会、聚餐、旅行。他时而感到自己与朋友们貌合神离,时而又比谁都更沉浸在对青年时代精神成长的回顾与对当下精神危机的热议之中。对新旧时代的精神状况、时代变动中的人生困境、文学的永恒意义以及作为文科教授的职业前景等等问题的讨论都不是空泛之议,而是来自安德森教授和他的朋友们的切身生存体验和挪威社会变化的具体语境。安德森教授在内心经受着“报警事件”煎熬的同时重返青春时代的思想家园,两者之间看似存在着紧张与冲突,这与埃利亚斯·茹克拉在情绪崩溃之后的青春回忆叙事一样,正是作者要营造的具有内心冲击力的对话语境和反思氛围。
语文与历史教师埃利亚斯·茹克拉因一把雨伞而爆发精神失控,安德森教授目睹谋杀案而迟迟不去报警,其实都只是令人焦虑的现实的一种隐喻。精神失控、关系荒诞、逃避选择、茫然失措,这样的体验并非只存在于黑色幽默的故事或存在主义的剧本之中。比较一下两位故事主角的结局,埃利亚斯·茹克拉无法忍受失控的自我被他者凝视和议论的痛苦,无法让自己重返那个熟人世界,因而不惜与过去的人生一刀两断;安德森教授则是在一再拖延与回避之中最后发现一切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在内心深处面对上帝也不再有什么愧色,只要打一个响指就能与自己和解、与上帝保持距离,一切就是这么简单。说起来有点残酷的是,如果说是那位中学教师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那么或许是安德森教授的更为深刻的思想和对人生意义的看穿使他能够从内心的折磨中逃脱了出来。
达格·索尔斯塔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生活中引发灾难的情绪失控和隐藏在几乎所有人内心的逃避心态设置为揭露人生真相的无情镜面,折射出人人被裹挟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冰冷与敌意。正如有评论所讲的,“他塑造的人物真实可信,在一个冰冷而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漂流,每个人在几乎任何层面上都令人难以忍受地无法与对方沟通。他的天才之处在于其中还有让人发笑甚至快乐的时刻。索尔斯塔成功地捕捉我们迷惘人生中难以描述的、流动的动作。”(《新人文主义者》,New Humanist)书中有很多细节描写充分表明了索尔斯塔最擅长的文学手法:精准地捕捉人生中的尴尬、迷惘时刻,以不动声色的戏谑和幽默揭示出人性在被规训、被凝视的现实世界中遭遇的落寞与无奈。
埃利亚斯·茹克拉只是一名从教二十五年的高中教师,一个关心社会的普普通通的挪威公民,每天按部就班去学校工作。平凡而低调,拿着微薄的薪水,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一生中唯一的高光时刻就是三十六岁那年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没想到十几年以后妻子的娇媚迷人已荡然无存,这很令他伤怀不已。同时更让他感到悲哀的是1980年代的社会变化导致教师职业自豪感的消失,他在每天接触的媒体中感到这个职业群体不再被社会关注,一种被贬低、被排斥的感觉令他感到被时代所抛弃。“还不够吗!他偶尔会自言自语。你们能不能放过我们,他恳求道。”(130页)听起来真让人替他难过。但是,埃利亚斯·茹克拉在精神上偶尔会闪耀出一道光芒。当他的一位同事漫不经心地说“我觉得今天我有点像汉斯·卡斯托普,我可能应该躺在被子里”的时候,猛然吃了一惊——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当中的主角汉斯·卡斯托普被一位教数学而不是教德语的老师随口提及,“埃利亚斯·茹克拉在那一瞬间心里陡然一亮”(146页)。他开始快乐得心里发颤,突如其来的快活颤栗传遍全身,这是学校里不可思议的一天。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密切关注那位并不熟悉的同事,他非常愿意接近他,甚至想象着如何邀请他到家里共进晚餐。但是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敢向他提出这样的计划。他曾经酷爱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弗朗茨·卡夫卡、赫尔曼·布洛赫、托马斯·曼和穆齐尔的作品,对1920年代的小说情有独钟。他甚至还想象过自己成为托马斯·曼笔下的人物,想象着托马斯·曼会如何与他对话,但是他马上被现实拉回到令人沮丧的1990年代(154-157页)。
从挪威文学的发展来说,索尔斯塔当然深受他的文学前辈易卜生的影响,在小说中处处流露出他对易卜生的研究与思考。易卜生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毋庸赘言,有意思的是,据说因为有了易卜生,挪威语成为许多英语作家和翻译家都愿意学习的一种语言,比如詹姆斯·乔伊斯就是这样。从索尔斯塔个人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历程来看,他在十六岁的时候阅读挪威著名作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起了关键作用。他说当时是一位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同学向他介绍汉姆生的书,如果没有他的介绍,他很怀疑自己日后会成为一名作家,因此他一直对那位同学心存感激。他一口气读完了所有能够从图书馆借回来的克努特·汉姆生的书,后来他在访谈中说当时汉姆生吸引他的是关于单相思的故事,那种绝望的浪漫主义是他真正能认同的。他甚至在读书的时候就在校报上发表了一些模仿汉姆生文笔的社论。后来他更喜欢的是他的现代主义小说《饥饿与神秘》(Hunger and Mysteries),成为作家之后的索尔斯塔慢慢认识到重要的是汉姆生的语言风格成为一种文学理想(见挪威文学评论家安·法塞萨斯[Ane Farsethås]对达格·索尔斯塔的访谈,《巴黎评论》第 217 期,2016 年夏季)。我们知道汉姆生曾经说过,好的语言具有色彩、光亮和味道,作家的使命就是驾驭语言,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让它显得无力。另外,在汉姆生笔下的那些人物的复杂性和怪癖心理无疑也对索尔斯塔有所影响。除了汉姆生之外, 他的早期写作还受到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的影响。
但是在索尔斯塔自己的作品中,他的探索和语言风格的形成还是很有个人独特性的。对于习惯了小说中的生活叙事文体的读者来讲,可能更有新的阅读感受。他的小说叙事的框架中随时插入思想随笔式的文体,长长的句子和插入其中的话语把读者步步引向曲折的意涵和微妙的转折,难怪译者说当一不留神便会“误入歧途”,或被弄得眼花缭乱(译后记)。理解的“歧途”与语言的“缭乱”正是“思”的标配,直至去到无可言说、不得不沉默的幽暗时刻。
索尔斯塔曾就读于奥斯陆大学,他当过教师和报社记者。在1970 年他加入了被认为是奉行“毛主义”的挪威工人共产党(Arbeidernes Kommunistparti,AKP),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敏锐思想性和社会批判性与其个人经历和体验有紧密联系。因此在小说的构思中索尔斯塔不会止步于故事中人物身份的边缘化、生活中的荒诞时刻带来的尴尬和人生的瞬间崩溃等情境,他需要的是借助书中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讨论更深刻的问题和思想议题。当他笔下的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在生命中的茫然时刻回顾青年时期精神上升的思想语境的时候,就更应该说他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他个人的精神自传,是他向时代的精神状况发出的强烈探测和质疑的思想札记。
埃利亚斯·茹克拉和他的朋友约翰·科内柳森讨论关于康德与马克思的关系的时候,对自己产生了疑惑:“难道他现在无法像以前那样,怀着理性的热情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像他曾经梦想加入康德学说的阐释者的行列一样?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马克思主义能否给他带来同样的满足感,同样持续不断的快乐,让他能够感受到突破思想界限的喜悦?”(99-100页)茹克拉的朋友科内柳森也是这样,他们曾彻夜长谈,都知道要回到他们早年学生时期那种思想氛围已经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推移,约翰·科内柳森很少再提起作为自由解放工具的马克思主义。他慢慢地避免使用如工人阶级这样的词汇,这让埃利亚斯·茹克拉松了一口气”(100页)。但是他们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解我们这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方面的优越性”能让他们着迷,不再只是思考阶级关系、权力结构等外部因素,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用来理解深受资本主义影响的人们内心的梦想、期待与失望,还有隐秘的渴念(101页)。于是约翰·科内柳森在商业广告艺术中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的闪亮、璀璨、耀眼的视觉文化背后的华而不实与黑暗;当他在1975年去墨西哥城参加一次国际哲学研讨会的时候,看到大批农村贫民住在城市郊区那些令人绝望的贫民窟却再也不愿离开的情景,令他对都市资本主义的迷人蛊惑力深感震撼。但是约翰·科内柳森得出的结论却是要为资本主义效力,不管是自嘲还是反讽,他立即行动起来,飞去纽约投入一家投资咨询公司。这一逆向性的构思也正是索尔斯塔所擅长的,同时也反映了他激进思想中的变化印痕。
当安德森教授在朋友中间开怀畅饮的时候,他会想到他们属于同一代人,有一条牢固的纽带将彼此联系在一起。那是在六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建立起来的精神纽带,是在具有左翼倾向的思想战壕中的战友。那时他们虽然不一定会加入AKP,但是他们共同反对加入北约,在七十年代对欧共体(欧盟前身)投反对票,在一场挪威和南非的网球锦标赛期间示威反对种族隔离,共同参加反对核武器的活动,在粗呢大衣上佩着“对核武器说不”的徽章。当然他们每个人也有自己独特的关注对象,本科生安德森的激进主要表现在对批判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的兴趣和支持,同时对文学艺术领域的前卫思潮尤为关注;他的朋友伯恩特·哈尔沃森则对军备竞赛和冷战感到忧虑,急切地想要投入行动。安德森阅读着那些晦涩难解的诗歌,这也是他的政治激进主义的一部分。他关注法国和波兰的前卫电影,关注现代文学和抽象画艺术,他以巨大的热忱投入了解先锋艺术,深感这种艺术确实掌控了我们自己的时代,但是又经常在理解的过程中感到挫败、令他非常沮丧。但当他对一首现代诗歌在瞬间有了领悟,整个身心便会充满欢悦。这时的他会感到自己不安的、错乱的灵魂仿佛已经与同时代最伟大的思想融合在一处(212页)。但那是三十年前的1960年代。现在他们已经五十多岁,是医生、心理学家、著名演员、教授和文化部门官员。他们又重新属于同一阶层、同一个圈子:事业的成功与生活相匹配,宽敞舒适的住宅、乡间木屋和庄园、汽车和游艇,无论他们是否还是激进派,都不影响他们享受优于他人的生活。在那一张张油光闪亮的脸上,谁还能看出他们曾经是一群激进的年轻人?那时他们拒绝与当局和平共处,坚持与社会主流唱对台戏,拒绝顺从权力,更让人敬佩的是那时他们拒绝成为社会地位受人羡慕的那一类人(225页)。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安德森教授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思想篝火的余焰还在燃烧,这当然是索尔斯塔的思想在燃烧。“在我们这个时代,商业化以无与伦比的能量激发着人们的热情和欲望,这就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他担心他们已经遭遇了最终的失败。他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哪怕只是为了自己的心灵安宁。……他再也不想掩饰自己认为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很可悲的事实。”安德森教授问他的同事:“你上一次因为希腊悲剧而感到震撼是在什么时候?我是说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震颤,让你内心深处颤栗的感觉,而不仅是点头认可,平静地享受……”(256页)作为文科教授,安德森想到自己不再拥有历史意识,他的神经就会恐惧地嘶喊,因为这将意味着我们的时代将会和我们一起消亡。虽然国家大剧院还在上演易卜生的戏剧,但是他感到人们演出的不是易卜生的作品,而是他的名望;对于作品本身,人们多少都是漠不关心的。他对于自己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群鬼》这部剧作也产生怀疑,因为连自己的心灵深处也没有了颤栗的感受。因此“我对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作用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真的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时代了。时间的牙齿在啃啮着我,摧毁一切。时间的牙齿在啃啮着那些最杰出的思想成就,将它们毁灭殆尽,让它们变得苍白失色”(258页)。安德森教授当然无法解答他遇到的问题:“他厌恶这个时代。但他又给不出其他选择。‘因为我们不是永恒的知识分子,我们只是商业化时代里的知识分子,深受大众心灵激荡的影响,而大众心灵激荡正是我们自身的无能所致。’”(256页)老实说,《安德森教授的夜晚》中大段的思想叙事真的值得在我们的思想史、艺术史的课堂上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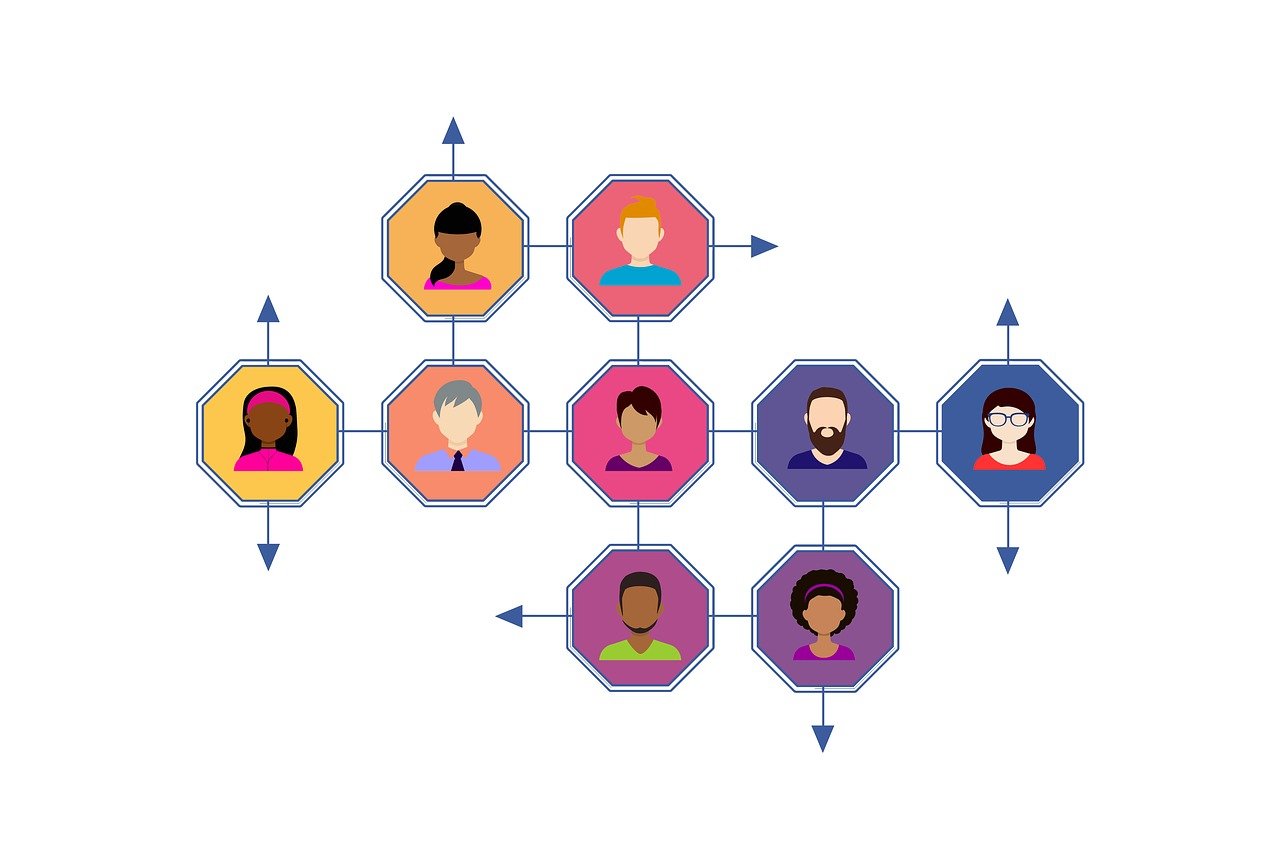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