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是其所牵涉到的两个学科——历史学与人类学——双向奔赴的结果,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之所以会如此,是与各自学科发展史相关联,或者说是各自学科中所存在的不足相关。运用新的“历史人类学”视角来研究拉丁美洲史,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对中国拉美史研究界的召唤,更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界的机遇。
历史学是首先进入到“历史人类学”领域的,或者说,真正开启“历史人类学”领域的是历史学,而非人类学;相较而言,人类学有意识地与历史学相结合,在美国人类学开创者博厄斯(Franz Boas)那一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随着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统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时,对历史的关照就变得微乎其微了。当人类学再重新“亲近”历史学,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所以,在英文表达上,历史人类学,即Historical anthropology,是历史学家们提出的;传统上,人类学界则长久以来都是以“history and anthropology”来表达二者的关系,并没有刻意将二者融合起来。
历史学之所以会先行一步,是因为历史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已经再次经历了大的理论转向。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对于历史的看法,说“历史即真实”,在理论派别上,即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学派,也即是历史学的科学派。在此之前的遂被称为“前实证主义”,或者叫做自然自发的历史观(naturalistic history)。这种历史观到法国的年鉴学派崛起时,就基本上被颠覆了。这种颠覆,其实就是哲学上、尤其是方法论上对实证主义颠覆的反射。如果说,以前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就是对以往过去的“客观”记录,是遵循着“科学”与“实证”的原则,那么,现在则明确地意识到,历史是很难“科学”和“客观”的,因为无论是历史材料之记载、历史书写中的材料选择还是历史书写者的个人喜好,都充满了主观的因素,更遑论在其中左右选择的权力因素。这些因素无疑都会影响历史的“客观性”。所以历史学就从“客观”论调走向了“主观”论调,在历史观上有了大的调整和转向。而且,随着方法论上结构主义、诠释学、尤其是现象学、以及最近四十来年被启发而生的后现代主义被介绍到历史学之后,对历史的解释就从“explanation”走向了“interpretation”,进而演变为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历史观,超越了早先简单的主客观二元论。

火车运输甘蔗的景象
于是,在历史的书写上,也遵循着这样的发展路径,从各种自发的、体例多样的,变成体例统一的,有一定规范的,接着是有很强规范的,进而到年鉴学派的宏大叙事和长时段历史,到如今的微观史、生活史。历史从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书写,走向了小人物、小事件、小群体,历史变成了“心态史”“意义史”和“观念史”。这就是为什么罗新和王笛的一系列书写如此令人耳目一新而大受欢迎,因为这类书写是生动的、有血有肉的,能够引起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共鸣。这种历史观的变迁也恰恰暗合了人类学自身发展的轨迹,二者在另一个层面上链接到了一起。
那么,为什么人类学会在新的时期跟历史学结合在一起呢?这是因为,人类学自西方发展起来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研究的主要就是exotic culture(异文化),特别是殖民地拓展到的地方,旧大陆与当地文化接触就成为必然,在对比中,文化上的差异就会极其明显,这种差异构成了早期人类学的主要内容。通过对这些显得“边缘化的”、“原始的”的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试图描摹人类自身的发展历程、帮助人们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在方法上,人类学家往往采取的是白描式的,且极尽细腻、生动之能事,与传统的宏大叙事的历史学有着不同的旨趣。当人类学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转入到对现代社会的研究时,这种关注于细节和底层人们的书写习惯和学科规范并没有改变,但恰好与此时兴起的历史学向微观史、生活史、物质史的转向发生了呼应,二者都有共同的研究旨趣和关注目标。因此,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可谓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双向奔赴。终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作为交叉学科的历史人类学开始崭露头角。
这个交叉学科的出现,除了历史学学理的大转折——年鉴学派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之外,还有当时国际环境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随后的冷战,让人类学难以进行其所擅长的“田野调查”(fieldwork),从而就有了要结合历史来对远处的文化(cultures at a distance,玛格丽特·米德语)进行描摹和测算,这就有了二战期间露丝·本尼迪格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虽然出版略迟,但研究是在二战期间做完的),以及之后大量的关于东南亚的研究作品的问世。当然,这种转向,其实又暗合了美国人类学之父Franz Boas的主张,即记忆民族志/文化志(memory ethnographies)。Boas因为反对进化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创建了“历史特殊论”学派,对历史的关注是其应有之义。但后来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学派,因为主要关注的是无文字的社会,以至于似乎“历史”就变得不可捉摸、不那么确定了,这才导致历史与人类学的分离。而当人类学又转回到现代有文字的社会后,历史书写就自然地与人类学结合了起来。
历史人类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进入中国,标志性事件就是1993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应邀至中山大学演讲。而稍早出生自香港、又在英美读书并在耶鲁大学担任教职的萧凤霞(Helen Siu)则早已经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她联合中山大学的青年学者如陈春生、刘志伟以及香港中文的科大卫,对华南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调研,用不同于传统历史书写的材料来构建华南社会的发展史。他们因此被称为“华南学派”。萧凤霞对历史人类学有很深入的研究,并且从七个方面对其进行界定。其中核心的要素,就是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结构过程(structuring),而非静态的,其中的个体则有很强的能动性,而非完全被动的存在,并且她因此把地域性扩展到更广的区域,对全球性、国家性和地方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当然,除了华南学派之外,其实以自觉不自觉的历史人类学方式研究中国的先驱已经很多,如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关于底层市集社会结构的研究,武雅士(Arthur Wolf)关于大众宗教的研究,弗里德曼(M. Freedman)关于宗教形态的研究,以及晚一辈的孔飞力(Philip A. Kuhn)关于“叫魂”和“晚清帝国”的研究,等等,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人类学界都形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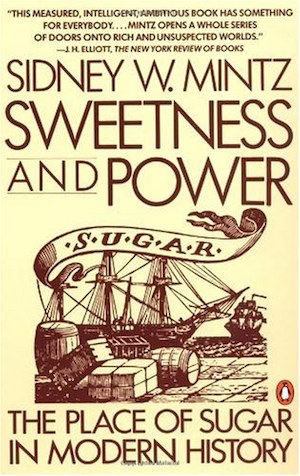
《甜与权力》(Sweetness and Power)
历史人类学在拉丁美洲研究上也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其中,饮食人类学的开创者西敏司(Sidney Mintz)的名作《甜与权力》(Sweetness and Power)通过对“甜”的追溯,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面——产糖的甘蔗是紧俏的商品,而加勒比热带区域恰好适合种植这样的作物,但早期的屠杀和病菌,导致印第安人被灭绝;劳动力的不足,催生了奴隶贸易,进而也就导致大庄园种植经济在加勒比的泛滥;而随着替代性的甜菜在欧洲的大量种植,则又导致了甘蔗种植业的衰落,加勒比的地位就因此受到影响,曾经的“甜”的天堂失去了竞争优势。一件物事而引发的历经数个世纪的人口奴役迁徙和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产业类型的转移,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剪影。这种书写方式是以前所没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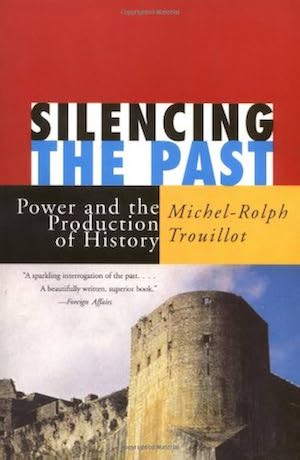
《让过去缄默:权力及历史的生产》(Silencing the Past: 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1997)
另一部引发广泛关注的历史人类学著作则是米歇尔-拉尔夫·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ot)的《让过去缄默:权力及历史的生产》(Silencing the Past: 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1997)。Trouilot是一名来自海地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在这部引起众多关注的著作中,他以生动的笔触讲述了许多历史被塑造的故事,其中记述的海地历史上被隐没的一位黑人英雄杜桑·卢维杜尔(François-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1743.3.20—1803.4.7)故事尤为动人,从而向我们展现了两种历史观的博弈:历史性1(historicity 1)和历史性2(historicity 2)。历史性1就是“what happened“,也就是实证主义的历史观;而历史性2则是”that which is said to have happened”,则是建构的历史,这往往是我们看到的历史面目,与真实无关,甚至恰恰相反,因为书写历史的权力并不掌握在知道真相的人手里。这本著作有人曾经评价为“福柯和霍华德·津恩”一起才能写出来,可见其影响力。因此其出版社曾经在20周年、25周年分别进行了学术纪念活动,组织学者讨论其中的启发性意义。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或精细或粗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如Cheryl Natzmer关于皮罗切特后人们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忆与自我修复的作品: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Creative Express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Post-Pinochet Chile)。总之,历史人类学的书写让今日的历史呈现出了很不一样的面貌。
对于中国拉美研究的学者而言,无疑也应该尽快地学习和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式来进行拉美史的研究。相比于那些做中国史研究的学者而言,做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已经有所滞后。其实,仅仅就中国与拉美的交往而言,历史人类学就大有用武之地。比如,关于华人华侨史,当今的华人华侨与历史上的华人华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更多的隐蔽的、深层的故事未能见诸于世,我们的研究还极其不足。薛淇心关于古巴老华侨的田野笔记(辑刊《中国与拉美》第二辑)看哭了多位编辑和读者,充分显示了历史人类学书写的力量。除此之外,还有中拉之间的文化遗产交流史的研究,当前中国与拉美之间大量的合作与交往中的人与事,等等。这些都是适合用新的历史人类学的框架或者视角来书写其中精彩过往、多姿今天、缤纷未来的研究,值得我国拉美史研究给予充分的关注。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