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2日,浙江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学术社团观通学社举办“沿波讨源:重构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与理论谱系”工作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机构的17名学者参加了本次活动。本次工作坊持续一天。与会学者从理论重释、史料考掘、跨文化视野等维度出发,围绕早期左翼文学的核心议题及张广海近著《“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展开深入而热烈的学术研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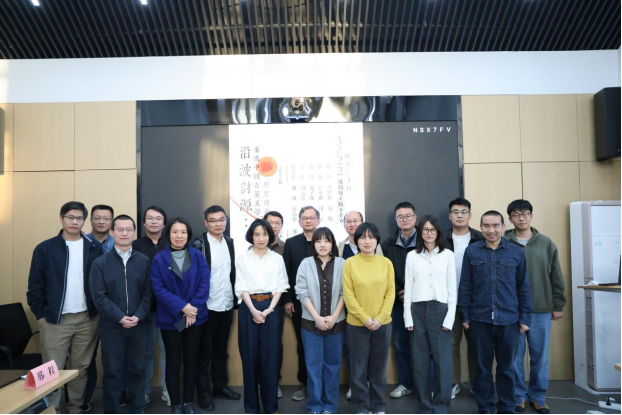
一、“革命文学”及相关论争的再认识
重识一般被称作“革命文学”的早期左翼文学及相关论争,是本次研讨会的核心议题。与会学者从各自的路径出发展开探索,发表了独特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凯从张广海近著《“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谈起,结合其《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一书写作经验及近年研究,指出“革命文学”论争存在一段漫长的“后史”,有必要将其置于更长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他指出,后期创造社在观念上存在某种模糊性与调和性,并未实现理论的彻底。他们对由创作、编辑、出版、印刷、发行、接受等各环节所形成的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形态尚未展开反思,其批判多停留于作品主题和内容层面,未能从颠覆现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或文学形式革命的角度展开根本性批判。然而,这种未完成的工作却在解放区的文艺实践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承接,表现为通过群众文艺实践颠覆现代文学生产模式,如取消作者独立性、淡化出版环节等。程凯指出,应当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联系性,将“革命文学”论争的漫长“后史”纳入考察视野,才能完整把握无产阶级文化历史进程的深层逻辑。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子凌深入阐析了“革命文学”论争所蕴含的多重张力结构,认为这些张力结构在根本上呼应了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处境问题。他认为,其中最核心的张力在于“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即历史发展究竟是自然进程还是主体意志推动的结果。这一命题不仅关乎对“革命文学”论争的阐释问题,更触及“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规划未来”这一深层哲学问题。刘子凌指出,或可以将“革命文学”及“革命文学”论争研究置于历史哲学的思考维度,在必然与可能、宿命与意志的辩证关系中,充分把握其思想内涵与时代意义。这一研究视角,也为思考现代知识分子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角度。
南京大学文学院葛飞细致梳理了李初梨、成仿吾、阿英、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关于早期左翼文学的历史叙事,探讨了早期左翼文学运动中“正统性”“划时代意义”等问题发生、演变并被建构的历史过程。他特别关注左翼阵营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消长、创作路线的调整,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叙事变化,着重分析了这些动态变化对“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形塑作用。葛飞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和阐释,揭示了左翼文学话语权争夺背后的政治逻辑与文学观念博弈,为理解中国“革命文学”历史叙事的变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复旦大学中文系刘天艺基于近年研究旨趣与经验,重点谈论了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史料发掘、整理与阐释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并尝试建构了研究方法论。他特别对“革命文学”概念的指称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该术语在学科研究中呈现出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进而导致了其与“左翼文学”等相邻概念的混用。他强调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必须审慎处理这一术语,既尊重历史文本的原生语境,又要建立清晰的概念边界,以此来避免因概念不清造成的研究偏差。
二、早期左翼文学个案研究
与会学者还深入到早期左翼文学的个案当中,展现出早期左翼文学的丰富性,在域外论争、作家心态、形式批评、感官叙事、美学渊源等方面,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吴宝林谈论了日本学界对中国左翼文艺研究史料的整理,以及自己的资料探索和发现,进而对早期“左联”在东京两个分支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日本分会”的形成状况及其展开的“理论战”进行了深入发掘,揭示出这场“理论战”在批判模式、政党介入等方面与“革命文学”论争存在历史相似性。他指出,某种意义上这是20年代末论争的域外延续,印证了程凯刚才提出的“‘革命文学’论争存在一段漫长后史”的观点。因此,若以更大的历史视野将其统摄起来,这一域外论争亦可被视作四十年代及“当代文学”诸多“理论战”的“先声”。吴宝林还讲述了他在研究过程中深切体会到的历史的“惊心动魄”,即论争表面上是意气用事,或只是理论分歧,但实际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剧烈波动,并造成了一定的历史后果。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胡风的革命文艺思想,还拓展了“左联”研究的国际视野,为理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提供了必要的视角。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吕彦霖通过1983年姚雪垠书信等史料,还原了1938年“《风雨》事件”的真相与细节,指出这一事件被姚雪垠在1986年、1987年修改《春暖花开的时候》时不加涂抹地加以呈现,造成小说“既左又右”的暧昧面貌。吕彦霖认为,在姚雪垠身上存在着鲜明的“革命文化人”秉性,即“革命”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动态的平衡,当其中一方受到压制,平衡被打破时,另一方则会强烈反弹。而“《风雨》事件”作为有价值的案例,展现了“革命文化人”在政治洪流中的摇摆姿态。
浙江大学文学院邢程认为瞿秋白的“拟鲁写作”体现出鲜明的“形式无意识”,即瞿秋白虽然在其鲁迅论中主要从内容主题的战斗性质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维度来建构鲁迅,但其1933年以“鲁迅风”写就的12篇杂文,首先摹仿的实际上是形式与风格。她还借用本雅明对贡多尔夫的批评——如同“猴子一样在树枝间跳来晃去,只是为了不必接触地面(即文本)”,对以《〈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为代表的论说模式的方法论作出反思,认为未能深入文本的内在形式结构,揭示其形式自律性。对于历史研究中的“同情的理解”立场,她在肯定其意义的基础之上,还认为当下学者不应惯性地沿袭前人的材料与方法,混淆“材料文献”与“经典文本”的本质区别,进而导致真正有效的批评方法被遮蔽。
复旦大学中文系康凌以殷夫的革命实践及《在死神未到之前》《孩儿塔》等诗作为讨论中心,指出殷夫大革命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感官化特征,即善于通过听觉、嗅觉、视觉等感觉经验来呈现革命者的身体体验,这种独特的感官书写,使革命受难者的身体在文本中超越了单纯的描写对象,转而成为连接诗歌艺术表达与社会革命实践的重要媒介。他还结合鲁迅阅读殷夫诗歌时的不安感受,揭示出殷夫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共享着理解“亡友”及“鬼的世界”的感官机制与心理方式。该研究不仅探讨了殷夫诗歌创作的形式特征,更深入揭示了感官叙事在左翼文学内部的某种普遍性。

南京大学文学院颜炼军同样关注殷夫诗歌,但侧重分析殷夫诗歌的精神与文学资源,他通过对《花瓶》《呵,我爱的》《孩儿塔》等一批文本和相关意象群的细致解读,指出殷夫在精神资源与写作主题上与闻一多、朱湘、何其芳等诗人有相通之处,像二十年代许多诗人一样,他也曾以拜伦、雪莱、济慈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为师。像“死神”“流浪人”等意象,皆能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中找到源头。他由此揭示了左翼诗歌与浪漫主义传统的复杂关联,为理解左翼诗歌的美学质地与复杂构成打开了空间。颜炼军还特别关注到殷夫晚期诗歌中出现的“海燕”这一高尔基式意象。他指出,这种新意象的引入可能反映了两种创作状态:或是诗人思想发生实质性转折,或是现代作家常见的“写作分身术”。虽然殷夫整体上呈现出激情与行动的高度一致,较少显露“分裂”,但透过这些文本细节,依然能看到殷夫诗歌中的曲折情感和内在裂隙。
浙江大学文学院周旻以巴金早年的“上海时期”为脉络,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勾勒出了1920年代早期上海无政府主义共同体的大致轮廓,分析了共同体内部思想观念的“和”与“不同”,并以自由书店及《自由月刊》等文化阵地为中心,探讨了巴金等青年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出版、翻译等文艺实践表现自我的无产阶级文学观念等问题。周旻还对无政府主义思潮与“革命文学”思潮的分歧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冲突集中体现在对革命本质的理解差异上,前者主张渐进式的社会进化论革命,强调个人自由;而后者则坚持激进的阶级革命论,推崇政治斗争,这种根本性的理念分歧使两派在1920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对抗”。该研究拓宽了中国左翼文学的起源路径,有助于我们在现代中国激进思潮的多元谱系中更好地认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三、左翼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由“革命文学”相关问题出发,诸位学者还围绕“如何认识左翼文学、左翼理论”等问题,反思了当前左翼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子凌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左翼文艺理论本质上不是一套认识论体系,而是一种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伦理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吸引力,主要不在于其解释世界的理论力量,而在于它承诺了一种个体救赎的可能性,为解决人生困惑提供了新的伦理指南。因此,他认为对左翼理论在成为共识性话语之前的传播过程的深入探索,能够揭示人们如何借助这一思想体系来理解个体、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关系。刘子凌对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存在及伦理抉择的关注,深化了我们对中国早期左翼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主体问题的思考,为研究左翼思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刘子凌同时提出,理想的左翼文学研究应能够很好地激活历史瞬间,既通过史料还原历史现场,又能避免陷入史料泥潭而不能自拔;研究者既需要运用“后见之明”的理性分析,又要保持对历史当事人所处语境的“同情之理解”,方能更为深入地接近历史对象。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吴宝林对当前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进行了反思,指出近年来诸多“各领风骚三五年”的“转向话语”虽然拓展了研究边界,如打破了革命叙事的单一性,但也带来了“扁平化”历史动力的研究困境。他特别强调了张广海著作中所提到的“人情物理”这一概念在左翼文学及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意义,认为理想的研究应当保持对中国现代文学内在脉络和“现代中国”生成机制的把握。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吴述桥关注的是左翼文艺理论中“组织”话语问题。他首先考察了“组织”话语的跨语境传播,从语义上梳理了“组织”的词源和演变过程,指出中国的“组织”话语传播经历了一个由日本传至俄国再传至中国的曲折过程。他以茅盾创作为例,指出左翼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组织”的思想观念。这种组织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创作指导层面,党组织通过意识形态引导直接影响作品的主题思想,文学批评家则扮演着具体指导创作的角色;在文学生产机制层面,“左联”及中共地下读书会等组织形式承担着意识形态生产的功能。他指出,左翼文学在组织文学生产方面形成了独特模式,因而有必要重视“组织”作为方法论概念的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深入探索组织化运作与左翼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范雪分享了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定位问题”的思考。她以郁达夫后期小说《出奔》为例,认为郁达夫在他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表述中使用的“荒谬”一词可能相当关键。荒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判断阶级的方式。这可能与当时中国并没有发生英、美所发生的机器荡平世界、物质大生产的事实有关。在这个事实世界的感觉里,那个要被警惕和反对的,不是“物”的掌控者,而是传统上长期与统治关联在一起的“文”。邢程对范雪的观点表示赞同。她以《鲁滨逊漂流记》为例,指出作品在时态运用上的矛盾折射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理性精神与冒险冲动之间的心灵张力。借此视角,我们或能更好地观察早期左翼文学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与内在矛盾。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曾小兰分享了她对张资平的研究心得,认为张资平的形象长期被扭曲与遮蔽,实际上张资平展现出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不同的理性思考特质,而对此一领域的探索,不仅能促进研究者自身的学术成长,更有助于还原一段历史真相。

四、《“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研讨
在浙江大学文学院陈奇佳主持下,与会者还围绕浙江大学文学院张广海的近著《“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展开了圆桌讨论。
张广海首先讲述了该书写作缘起与立场,表明该书力图“既站在左翼与右翼之间,也站在左翼与左翼之间”,在破除左翼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鲁迅中心主义”预设的前提下,探索“革命文学”论争的真相与意蕴。他从“事”与“理”两个角度谈论了该书旨趣,着重分享并探讨了“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是否蓄意发动鲁迅批判”“彭康的入党时间考辨”“茅盾的庐山行迹考辨”“后期创造社的理论批判潜能为何被抑制”“阶级性与人性之辨该如何认识”“后期创造社的再定位与太阳社文坛活动的再认识”等既具有一定趣味、也值得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的问题。其次,北京大学出版社高迪基于该书的编辑经验,发表了对学术“生产”与“写作”的见解。她认为,编辑作为学术生产链条中的特殊角色,能够目睹稿件最原始的状态,因而尤其能关注到作者写作的紧迫感与思考的张力,并强调在“生产”的功利性与系统性之外,学术著作应保持创造性、切身性和敞开性。
接着,与会学者围绕该著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讨论。陈奇佳指出,他从张广海著作中特别关注到了夏曦、何畏、沈泽民、张闻天等人物,这些个案折射出许多左翼文学史上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问题。程凯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呈现出以“理论论争”为核心的特征,体现为“文化政治斗争史”的叙述倾向。他以“漩涡”为喻,形象描述了这种高度压缩的理论话语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而正是这种复杂的理论互动构成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他进而指出了“实证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认为过度强调实证可能导致文学史研究中“革命内在动力”的消解,因此,如何深入探讨文学论争史仍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有待深入展开的核心问题。对于文学论争研究,程凯认为,需要注意到其“表层”与“深层”的双重结构,研究者需要穿透论争的外表,把握隐藏于其下的逻辑脉络和实质。程凯认为,“鲁迅中心主义”这一现象根植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选择,即瞿秋白等革命理论家试图寻找区别于后期创造社“观念突变”的模式。这一选择过程同样延伸至80年代的后续历史之中。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周敏以侦探小说为比喻,指出张广海该著通过侦探式的严谨史料考据,还原了被当事人有意或无意遮蔽的历史真相,同时又能在证据难以触及的领域,凭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从盘根错节的文字陈述中精准把握历史人物的心灵轨迹。他认为张广海的研究不仅体现出“笨功夫”与“真智慧”的较好统一,而且在理论批评与史料考证的结合方面,具有了“以厚重约束轻灵,以轻灵举重若轻”的学术品格,这使得该书一方面“雅俗共赏”,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又不失专业研究的深度,能扎实地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
吴述桥指出,张广海的近著对于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具有很好的方法论意义:在实证层面,通过扎实的史料爬梳提供了确切的历史细节;在理论层面,又对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种将微观考证与宏观思考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既避免了空泛的理论推断,又超越了琐碎的史料堆砌,在“史”与“理”之间保持了富有张力的平衡。
颜炼军先论及张广海此前出版的《左联筹建与组织系统考论》一书,认为其对史料的考辨和梳理特别精彩,写作上有卓异的个人风格;继而评价新著在史实考证与理论辨析的结合上,更上层楼,做了非常出色的推进。同时他也恳盼其后续研究或可在此基础上,在文学作品的维度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做到兼顾“史”“理”“文”的立体和呼应。
康凌指出学界长期存在着“一体化”的左翼知识的固化框架,左翼内在的动力与势能被封存于这一框架之中,而张广海的研究则将左翼被压抑的内在动力重新释放,通过对左翼理论野蛮生长时期的“非主流作品”的发掘,呈现了被主流叙述遮蔽的理论洞见与实践挫折,较好地复现了历史现场的多元样态。
对于张广海著作中对“阶级性与人性”议题的关注,葛飞建议可尝试突破文学研究框架,建立纵向的研究视野,将视域从创造社刊物扩展至五四以来的中共刊物,系统考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历程与接受机制,加强理论阐释。程凯则建议,进一步超越依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讨论阶级性与人性论争的视角。
吴宝林认为当前文学研究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困境:一方面研究者往往难以摆脱当代视角,容易将“当代性”投射到历史现场,造成对历史的扭曲解读。另一方面,“还原主义”式的研究视角又会局限于“历史风貌”的刻画,而难以深描出“跃动的历史”。他指出理想的研究状态应保持“游移”的特质——研究主体与历史对象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游移的关系,进而肯定了《“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一书游动于不同历史对象之间的立场与姿态。刘天艺则指出,张广海该著努力摆脱既定左翼文学史的叙述框架,将“革命文学”论争还原到1920年代中国革命尚未定型的生成阶段之中,辨析了“革命文学”与种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交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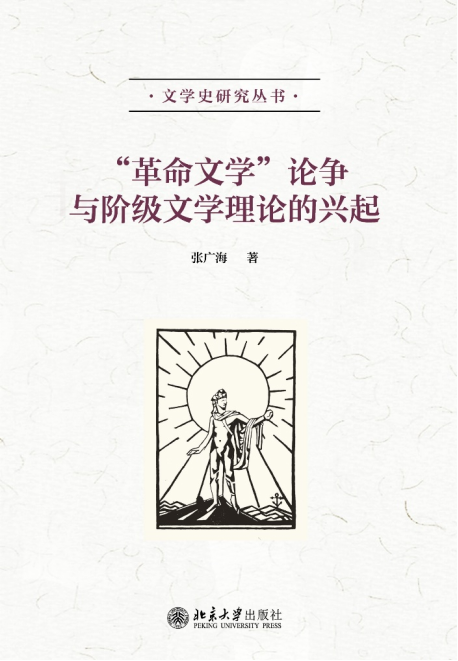
本次工作坊重新审视了左翼文学的发生机制与谱系演变,既聚焦文本细读与历史现场还原,亦关注“革命文学”的历史回响,呈现出方法论上的开放性与问题意识的前沿性。工作坊既深化了对早期左翼文学复杂性的理解,也为后续研究的开拓提供了可能的学术生长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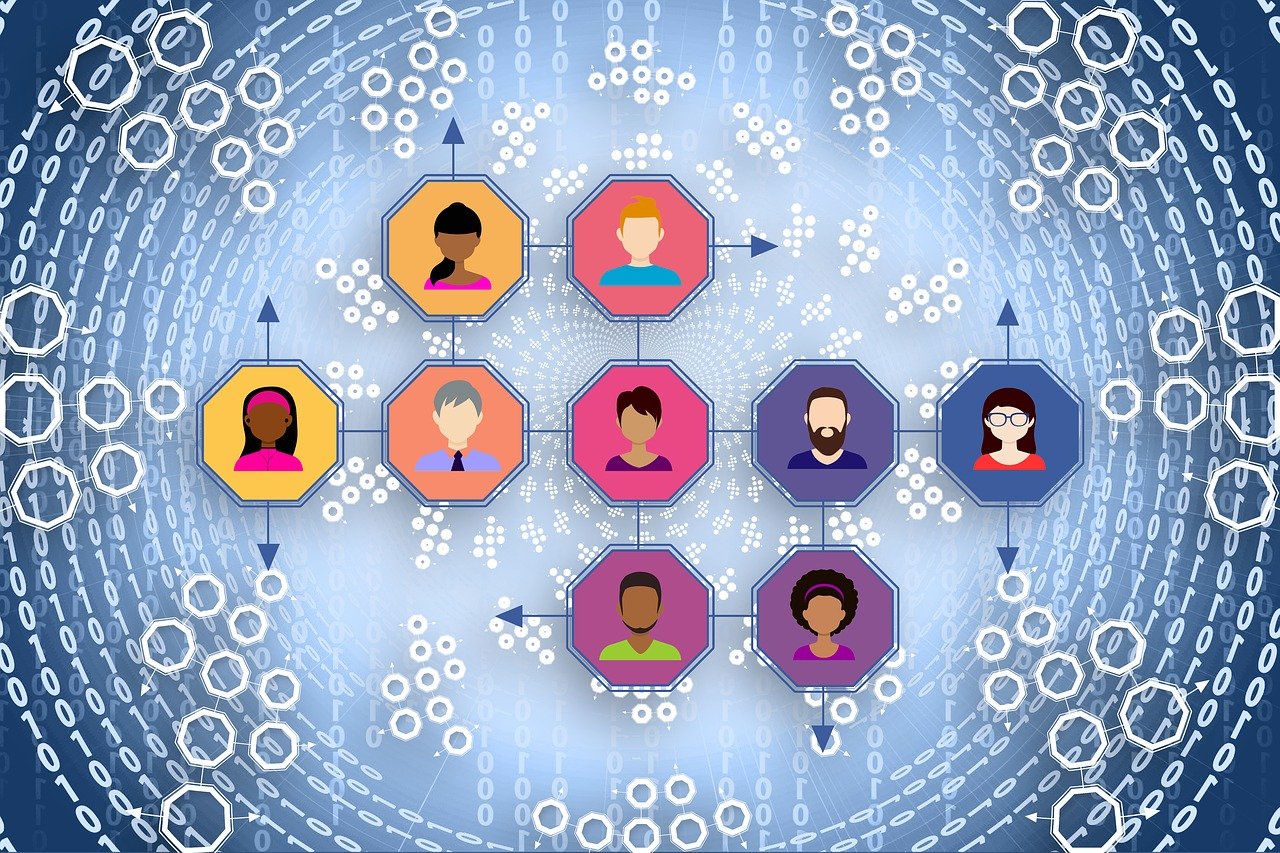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