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明起源”丛书总序
从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来看,古代近东、古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源地,对古希腊文明具有重要影响。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环地中海域的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就有较繁荣的文明形态和城邦生活。古代近东和埃及的宇宙论神话、灵魂学、政治观展示出对存在秩序的整体理解,其影响不止于早期希腊神话、哲学和政制,而且延续到后来的希腊化和罗马帝国统治时期。
古代近东文明包含的宇宙起源论、灵魂轮回和灵魂不朽说、宗教神话等,蕴含着对本原、灵魂与身体、善与恶、一与多等议题的思考,激发了古希腊哲学最初对宇宙、自然、灵魂等问题的热切探索。在荷马、赫西俄德、柏拉图及后世思想中,也可瞥见古代近东神话与“宇宙—政治”秩序观念的余晖。因此,欧洲或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否可略过古代近东而直溯古希腊文明,仍需仔细考辨。
古希腊哲学在融汇古代地中海各地区辉煌文明的基础上,实现了诸多创造性转化,对人世各种基本问题有了更丰富深邃的思索。柏拉图作为古希腊哲学和古典理性主义的突出代表,缔造了宙斯时代或荷马时代之后的文明形态,体现出一种文明综合与提升的典范性努力。柏拉图不仅将宇宙论与目的论关联起来,还特别注重城邦秩序与灵魂秩序的融合,以应对人世的无序化和心灵的畸变。柏拉图试图在适度保留传统宗法的基础上,通过哲学对智慧的求索重塑文明秩序,使政治、法律和文明具有更稳固的根基。
对于什么是自然、本原,自然与礼法的关系,自然与强力、正义的关联,柏拉图的理解迥异于自然哲人、智术师和历史学家,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构成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大张力。柏拉图重新定义自然、灵魂、正义、理性、强弱等核心概念,形成了新的宇宙论、自然观、神学观、自然法和政治理念。与之相反,智术师和历史学家将强者统治弱者当作自然正义和自然法则,而导向强力主义、帝国和僭政。此外,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成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在古希腊亦有一个相对立的非政治的哲学传统,即犬儒派的厌世主义、廊下派的世界主义、伊壁鸠鲁派的快乐主义。可见,古希腊哲学本身存在种种思想分歧,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相。各哲学流派与古代地中海诸文明的关系也盘根错节,皆有待深入细致地重新梳理。
两希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对西方文明的形成亦有重要作用。两希文明中的不同要素,如理性与信仰、古罗马法律制度、基督教文明、日耳曼帝国统治等,对西方文明的最终成型有许多层面的影响。同样需要进一步探察和辨析,近代西方文明主要是承接古代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抑或以希伯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从而厘清西方文明的整体面貌和不同文明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现代西方哲人提出新的自然和政治原则,构建了现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论,更为关注人的自然欲望的满足。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哲人对于自然状态、人性、德性和政制的新构想,塑造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新面目。古今哲学对自然、德性、法律、理性、快乐的看法存在诸多争执,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制度设计、道德意识、人性认知和文明理念。可以看到,西方文明体内部具有各种张力。重新探究西方哲学和文明的根源,可以更好地看清西方在近现代为何遭受了文明、价值、政治上的危机和困境。通过检审西方古今文明的得与失,亦可打破文明史的线性叙事,展现西方哲学史和文明史中的转折、断裂和变型。
从东西方古典文明来看,中华文明与古代近东、古希腊文明亦有相当的契合性,对于宇宙、城邦、德性、战争与和平等重要议题常有共通的见解。东西方古典文明都强调德政和灵魂完善,对强力主义、政治失衡、人伦失序、过度欲望化等均有深刻反思。故而,对东西方传世经典的深入阐发与互鉴,也有助于古典文明的返本开新和古今价值的转化融通。
林志猛读《恢复古典的创制观——西塞罗〈论法律〉义疏》

在《论法律》中,西塞罗对“自然”(natura)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一开始就指出,要探究法律的根源,首先得弄清“自然”赋予人什么恩惠,人的心智(mens)有何种创造完美事物的巨大能力,人生在世要履行什么义务,人与人之间有何自然联系(《论法律》I.16)。在西塞罗看来,要解释法的本质,需从人的自然本性去寻找,凭借哲学来探究。他更看重的是人追求心智完善的自然目的和自然义务,因为理性蕴含于人的自然本性。西塞罗提到廊下派的法律(lex)观:
法律是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ratio summa),它命令必须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事情。当同样的理性在人们心中得到确保和建立时,就是法律。因此,他们通常认为,法即智识(prudentiam),其含义是智识要求人们正确地行为,禁止人们违法。(《论法律》I.18—19)
西塞罗认为法律与自然紧密关联,但传统诗人却力图将两者拆开。卡斯珀表明,按照传统诗人,人的想象力或心智与自然无关,自然之物易朽,而不依赖于自然的诗作才永恒。诗的创作或技艺可以征服自然,由此对新政制的立法者或创制者构成威胁(卡斯珀,第27页)。诗人构筑的诸神形象和宗教若成为法律的唯一根基,在时代变迁和宗教衰落的过程中,法律将无法持续改良直至失去权威。因此,需要将法律与自然、真理融合起来,使自然成为法律和正义的正当基础,这种自然法将支配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西塞罗由此让我们看到,政治和法律无法超越自然,违背人的自然本性,两者均植根于自然而有其限度。
西塞罗还表示,廊下派秉承希腊法律(νόμος)中的公平概念,即法律是赋予每个人所应得。但他自己更倾向于认为,“法律”(lex)源自“选择”(lego)概念,法律是自然的力量,明智者的心智和理性,亦是正义与不义的准则(《论法律》I.19)。实际上,柏拉图也早就将法(νόμος)与理智、理性、哲学关联在一起:“法意图成为对实在的发现” (柏拉图:《米诺斯》,林志猛译,载《柏拉图全集·中短篇作品下》,华夏出版社,2023年,315a),法是“理智的分配”(νοῦ διανομὴν)(柏拉图:《法义》,林志猛译,华夏出版社,2023年,714a) ,“理性(λόγος)力图成为法”(柏拉图《法义》835e)。在柏拉图看来,好的立法基于诸德性的自然秩序(柏拉图《法义》631b—d)。西塞罗对法律的阐述与柏拉图息息相关。
卡斯珀明确指出,西塞罗兼取了希腊与罗马对法的理解。西塞罗式的政治智慧认识到,政治正义是自然正义与习俗正义的结合,西塞罗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区分了分配正义与交换正义。法律不仅要给每个人分配应得之物,还要在人遭受不义时进行矫正以恢复正义(卡斯珀,第42—43页)。法律要做出恰当的分配,就得充分认识每个人的自然本性,以分配适合其本性的有益之物或位置,使人各得其所。因此,法律需要包含理智或智慧的要素,才能做出这样的分配。换言之,法律和政治需要高于其自身的哲学。但对于各种不义和犯罪行为的矫正,又需以政治和现实为依据,采取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手段。自然法虽是最高的,但西塞罗并不限于谈论最高的法律,而是顾及民众通常会提到的那些有允许或禁止效力的条规(《论法律》I.19)。
在西塞罗那里,自然、神、人之间有着独特的关系。西塞罗提出,统治整个自然(naturam omnem)的到底是不朽神明的力量或本性,还是理性、权力、智慧、意愿等概念。在各种生灵中,唯有人有感觉、记忆、预见、理性、智力、思维等,人由神所创造。人和神共有理性这一最美好之物,彼此间存在“正确的共同理性”(recta ratio communis)。法律便是理性,人与神在法律上也共有。人们若服从于同一个政权,便是服从于“上天秩序、神的智慧和全能的神”。因此,整个宇宙应视为神人的共同体(《论法律》I.22—23)。西塞罗进一步表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看法:
天体经过不断的运行和循环,达到了某种可以播种人类的成熟状态;人类被撒播于地球各处,并被赋予神明的礼物——灵魂;当组成人的其他成分来自有死之物,脆弱、易朽时,灵魂却产生于神明。因此完全可以说,我们同神明之间有着亲缘的或世系的或同源的联系。(《论法律》I.24)
西塞罗对人的灵魂和人神关系的描述,同样有着柏拉图的思想印痕。按照柏拉图《蒂迈欧》中的创世论,宇宙灵魂具有理智,支配着整个宇宙体。人的灵魂是宇宙灵魂跟一些杂质混合的产物,在此世活得好的灵魂会回到天上对应的那颗星辰。造物者在恰当的时机将每个灵魂“播种”到地球、月亮等之后,灵魂自然生长为最敬神的部分(柏拉图:《蒂迈欧》,叶然译,载《柏拉图全集·中短篇作品下》,34a—b,41d—42e)。 在《法义》中,柏拉图将宇宙灵魂视为一种“自我运动”,能推动自身和宇宙万物运动。灵魂作为“初始之物”,优先于物质性的诸元素(水、火、土、气等),因此更应称为“自然”。柏拉图最后将诸神定义为具有完整德性和理智的诸灵魂(柏拉图《法义》892c,896c,899b)。显然,西塞罗认为人的灵魂源于神,并在天体运行中被“播种”,人回忆和认识自己便是在认识神,这与柏拉图的看法极为相近。
卡斯珀注意到,西塞罗笔下的至高神赋予人理性,人与神共享理性,可谓同一谱系和族群。“西塞罗的至高之神似乎受到理性和自然的约束:至高无上的神受内自身内在标准约束,同时以这一标准掌管人与次一级的神。相比之下,《创世记》中的创世神神秘而全能,人根本无法企及。”(卡斯珀,第58页)西塞罗描述的神明显不同于多数人崇敬和供奉的传统神,而是更多用理性、理智、智慧、德性、灵魂这类概念来展现,更接近柏拉图呈现的理智神。西塞罗甚至说,神人相似,具有同一种德性,那便是达到完善,进入“最高境界的自然”(《论法律》I.25)。自然原本有别于习俗塑造的诸神,西塞罗却将两者融为一体。自然不仅给人提供了丰富无比的东西,还教导人发明了各种技艺,凭智慧创造出种种生活所需之物。在柏拉图看来,人的自然目的在于追求灵魂的完善和心智的完满,使自身拥有健全的德性和智慧。爱智慧的哲人常被比作神样的人。西塞罗同样表示,人与神经由完善和发展理性,可达到自身存在的最高境界,人与神共享同样的德性。西塞罗得出:
按照自然生活是最高的善,亦即过适度的、符合德性要求的生活,或者说遵循自然,如同按照自然法律生活,亦即尽其可能,完成自然要求的一切……自然要求我们如同遵循法律般地遵循德性的要求生活。(《论法律》I.56)
依自然生活即过合德性的生活和根据自然法生活,因为法律源于自然。这种生活被视为最高的善,西塞罗进一步表明,智慧是所有善之母,而“哲学”的原意即是爱智慧。哲学既教导人认识诸事物,更重要的是教人认识自己,以感受到自身的某种神性,进而在智慧的指引下成为高贵和幸福之人(《论法律》I.58—59)。从这些论述看,西塞罗更为强调的是哲学而非宗教,即便他的哲学与政治、宗教有所调和。因此,西塞罗在根本上并非廊下派或犬儒派。廊下派的自然法基于神圣天意说和人类中心的目的论,西塞罗在《论神性》中都进行了批驳。尽管《论法律》看起来有廊下派的思想痕迹,但西塞罗终归更倾向柏拉图哲学(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 156—157页;卡斯珀,第49—50页)。
廊下派的自然法或神法相当于最高神或其理性,通过形塑恒在的质料,自然法等同于支配宇宙大全的有序原则。人作为理性存在者能认识并遵从这样的自然法,而走向有德的生活和完善。但有德性的生活并非普通人的道德生活,而是类似于哲人的沉思生活。问题在于,多数人能过哲人的生活吗?廊下派也被看作是平等主义者,否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然奴隶。但这并不能证明,所有人在成为智慧者或有德者方面自然平等(施特劳斯:《论自然法》,张缨译,载《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87—188页)。 比起柏拉图,西塞罗为传统宗教做了更多保留。西塞罗也表示,自然法要与人类生活真正相关,就不能将人类视为脱离身体的灵魂,而必须看成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卡斯珀,第38页)。但灵魂在认识并接受德性之后,便不再受制于身体,而会抑制对快乐的追求,摆脱对死亡和痛苦的恐惧,并保持宗教的纯洁性,分辨善恶(《论法律》I.60)。西塞罗在兼顾罗马宗教和政治现实的同时,更为强调灵魂的优异和理性生活。
在解释自然法和自然正义时,西塞罗追溯到法律和正义的起源或第一原则。卡斯珀表示,西塞罗遵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导:探究某物“是什么”依赖于其开端,开端内含此物的终极目的和自然本性(卡斯珀,第41页)。既然法律源于自然且内含最高理性或正确理性,法律就不只是由人民的法令、统治者的决定、法官们的判决确立,或是人民投票或决议的产物(《论法律》I.43—44)。因为,多数人的意见有好有坏,彼此之间相互冲突(柏拉图《米诺斯》314b—e),法律作为善物并非源自坏的意见。正义与不义的区分同样依据自然,而非意见或决议。无疑,西塞罗对自然正义和自然目的的看法也更接近柏拉图。

西塞罗
宗教法与官职法
《论法律》卷二主要探讨宗教法。西塞罗认为,真正的立法者必须具备最高的实践智慧,共和国应由懂得最好的自然法的政治家来统治,此即自然法共和国。自然法体现了正确的理性,自然法共和国创立者的目标在于正确的理性,并能够以通俗的理性言说教化公民。法植根于自然意味着基于人的灵魂,植根于明智者的灵魂和理性。西塞罗虽看重理性,却未忽略宗教和虔敬,他创立的政制基于对诸神的尊敬及诸神统治的自然。
西塞罗像柏拉图那样引入了“法律序曲”(legis proemium),即置于正式的法律条文前的劝谕性言辞。法律序曲旨在让人更认同并接受法律,并从中学到东西(柏拉图《法义》723a)。西塞罗的宗教法序曲表明,凡事皆由神明统治和管理,按神的决定和意志发生,神有恩于人类,关注每个人的为人、行为、想法和是否虔敬。此外,人具有理性和灵智,宇宙大全同样有,天体乃是靠理性运动。没有什么事物能超越自然,自然具有理性(《论法律》II.15—16)。西塞罗还提出,我们若承认诸神存在,其灵智统治宇宙,并关心人类,能向人显示要发生之事的征兆,预言就可能存在(《论法律》II.32)。柏拉图在《法义》卷十也论证过,诸神存在、关心人类且不会被献祭和祈祷收买。诸神作为有完整德性的诸灵魂,理智、智慧也是其突出特征。
在卡斯珀看来,西塞罗接受私人圣坛和家族诸神,其城邦有别于柏拉图的城邦。西塞罗的城邦会更虑及人的境况,这些人居住于自然世界而非理念的世界,同样注重公共仪式而不仅仅是纯粹的哲学。西塞罗对宗教的关切是其关注自然和自然法的一部分,因为,宗教及其典礼加强了政制的正当性。西塞罗的法律确立了宗教崇拜体系,但人应当借此形成对政制的伟大敬意和尊重,造就健康的共和国(卡斯珀,第148页)。宗教法的引入是为对灵魂保持永恒的关注,使灵魂尽可能朝向理性与自然正义。但卡斯珀在对照柏拉图的论述中,往往更凸显柏拉图的哲人王和善的理念,柏拉图的城邦看起来过于理想。(雷克辛指出,西塞罗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柏拉图,但更依赖于罗马理想、习俗及传统。西塞罗强调人与神的关系,并表示像祖先那样恰切地敬神将十分有益。他同样认为,柏拉图过于形而上和理想化,西塞罗则回溯到罗马祖先及罗马国家的辉煌历史。参 John Rexine, Religion in Plato and Cicero,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59, pp. 127-128。) 实际上,柏拉图《法义》构建的是次好的城邦,或现实可行的最佳政制,即包含贵族制、君主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政制(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一卷《立法的哲学基础:〈法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9—111页)。 哲学在《法义》中非常隐蔽,已经过淡化与调和,可与宗教和政治更好地融合。
《论法律》卷三涉及官职法,《法义》卷六也是处理官职问题。在提出具体的法律条文前,西塞罗像柏拉图那样放入了法律序曲,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官员及其职责与法律之间有内在联系,官员的职责是规定正确、有益且符合法律的事情,官员如同会说话的法律。第二,官员的权力有宗教基础,乃是神圣权力的一部分。第三,合理安排官员的职位,官员们要知道如何轮流统治与被统治(《论法律》III.1—5)。
西塞罗也提倡包含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要素的混合政制,认为最好的共和国是混合的或节制的共和国。保民官职位乃是混合政制的必要部分,既能平息民众的愤怒又能防止僭政,从而确立正当的政制。西塞罗对官职的安排体现了政治的节制,充分认识到政治的限度和人的限度,其创立政制的教诲是对政治节制的教导。所有的创制者应从自己原有的政制出发,而非推倒重来、连根拔除,直接另立新政体。西塞罗构建的最好法律并不是对任何现实政治的完全抽象,而是顾及人类生活和利益,以适用于现实政体或共和国。西塞罗从既定的罗马共和国出发,并在罗马之外寻求立法标准。在拥有稳固的根基后,方能走出罗马,在自身政制之外寻求超越性的哲学指引。因此,卡斯珀将这种政治正当看作自然正当与法律或传统正当的结合(卡斯珀,第202—203页)。
卡斯珀表明,西塞罗的哲学与政治任务息息相关。西塞罗试图在罗马重建共和政制,为未来的自然法共和国缔造者提供模型。因此,西塞罗首先要复兴健康的哲学,以引导共和制的回归与平稳运行。此外,西塞罗借助荣誉或高贵吸引各学派,尤其是向廊下派显示,人要变得高贵需参与政治,而非仅仅过哲人式的沉思生活。由此也可说服学园派和漫步学派,正直和高贵之人都能认可的政制,并不只是专注于明智者,而是着眼于共同利益的自然法政制(卡斯珀,第84页)。可以看到,西塞罗的政制和法律与现实有更深的调和,但并未由此摒弃哲学。
“哲学与文明起源”书目(即将出版)
恢复古典的创制观:西塞罗《论法律》义疏(蒂莫西·卡斯珀)
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与政治哲学:《斐多》义疏(保罗·斯特恩)
柏拉图的宇宙论及其伦理维度(加夫列拉·卡罗内)
言说自然:亚里士多德与理性的发现(罗素·温斯洛)
西方文明的神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范畴和政治神话的西方(安里柯·斐里)
柏拉图的克里特城邦:《法义》的历史解释(格伦·莫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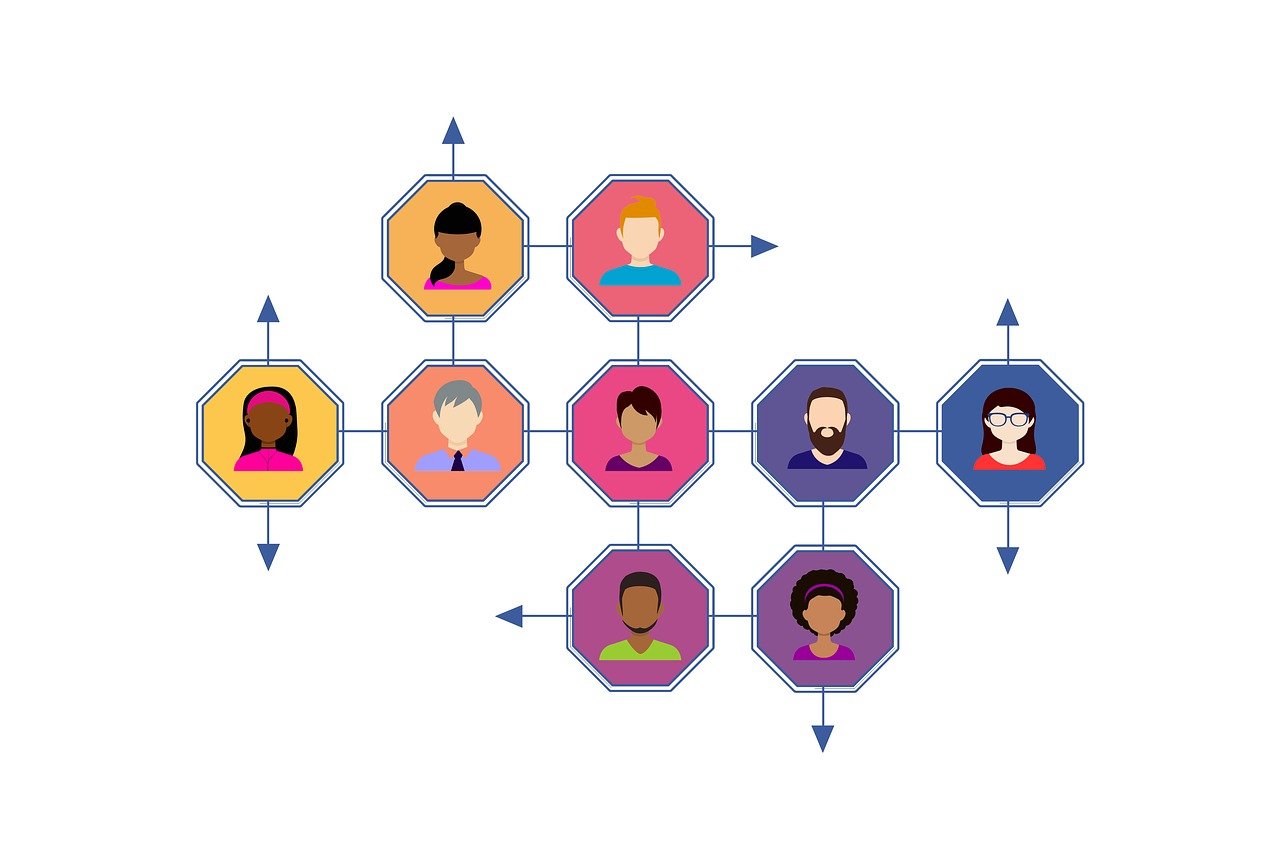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