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后十五日,为清明。正是春风骀荡,红蕊吐艳,绿芽萌新之时。

本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清明前的镇江、江阴等地惯以荠菜、韭菜配刀鱼作馅包制馄饨,蛋清皮子薄软相宜,随包随吃。江南多河鲜海错,刀鱼是春季里可以说道说道的滋味之一。陆游笔下,刀鱼也做寒食清明的节物——“江鲚堆盘粔籹香,山家节物亦穷忙”。濒江一带的食俗,春肴以刀鲚为胜,1885年4月13日《申报》记载:此鱼春初始有,清明前后较多,夏则无。然好奇者每以尝新为快,故清明前每斤值青蚨一百数十翼,而清明后一日则仅售四五十文而已。

刀鱼资料图
刀鱼自古别名就非常多:鱴刀、鱽鱼、刀鰶、聚刀鱼……大部分的名称源于其形状像刀。明人魏浣初叹:“江南忆,佳味忆江鲜。刀鲚霜鳞娄水断,河豚雪乳福山船,齐到试灯前。”刀鱼多产自沿江以及太湖一带。不同地方鱼群大小种类有细微差别,古时没有拉丁学名那么严谨,对于那些俗名人们笼统归为刀鲚。上海话中的“烤子鱼”(凤鲚),推测或为古籍中的“鯌子”。《山海经》中称鮆鱼,大者尺余,郭璞标注道:“太湖中今饶之,一名刀鱼。”春夏上市多,以“肉质细腻、腴而不腻”为人称道。宋·毛胜《水族加恩簿》:“惟尔白圭夫子,貌则清臞,材极俊美,宜授骨鲠卿。”但也因细骨太多,也叫做刺鱼,是不受怕刺的人欢迎的。
东坡先生诗曰:“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水鮆鱼肥。”刀鲚、凤鲚是洄游性鱼类,平时生活栖居在海里,每年春末由海入江,并溯江而上,在江河中下游淡水入口处进行生殖洄游,它们4月产卵,3~5月为鱼汛期。进入长江的刀鲚甚至可以到达洞庭湖,漫长的征途中它们很少涉食。鱼近海则仍染腥味,长途跋涉则清减,所以游至江苏恰恰好。北宋·赵抃《和美毗陵鲥鲚之美》中有记载,“江南鲥鲚客夸肥,公到常州鲙熟时”。南宋·楼钥《送袁和叔尉江阴》也曾谈到,“况有海错供庖烹,河肫鲥鲚鲜不腥”。肥美不腥,因此常州、镇江、江阴等地过去食刀鱼多,但湖南人并未形成类似的食癖。

清蒸刀鱼资料图
现在长江禁捕,从前诗人吃的江刀是不允许上餐桌了。清·沈朝初《忆江南 其十七 名馔》 有言,“苏州好,鱼味爱三春。刀鲚去鳞光错落,河豚焙乳腹膨脝”。清·厉鹗《扬州清明有感》则言“芹芽入市刀鲚上,非我无酒开心颜”。刀鱼并非只有长江里独有,江河湖海本都有刀鱼。由海入江洄游也不止一条河,我猜江鲚的美味中有一部分功劳是源自温柔乡里的文人太能写太会写,引得天南海北产生了无限遐想,也带动了现代刀鱼的养殖行当。
现代人常常把清明当作一个记忆的时间。据传“明前鱼骨软如绵,明后鱼骨硬似铁”,清明前的鱼比较鲜美。古人发现刀鲚来时,常有杨花飞舞,这样的景象北宋梅尧臣一人就写了不少。“杨花正飞鲚鱼多,良脍举酒谢河伯”、“鲚鱼何时来,杨花吹茫茫”、“日暖杨花四散开,江边鲚鱼无数来”、“春浦杨花撩乱飞,春江鲚鱼来正肥”、“过淮逢絮鲚,泊岸采芦蕨”……古人的诗句里虽也有提及寒食清明,不过他们默契把杨花柳絮,风吹浪白当作刀鲚的信号。北宋司马光写“鲚鲙思吹絮”之句时自注:“吴中食鲚鱼鲙以杨花为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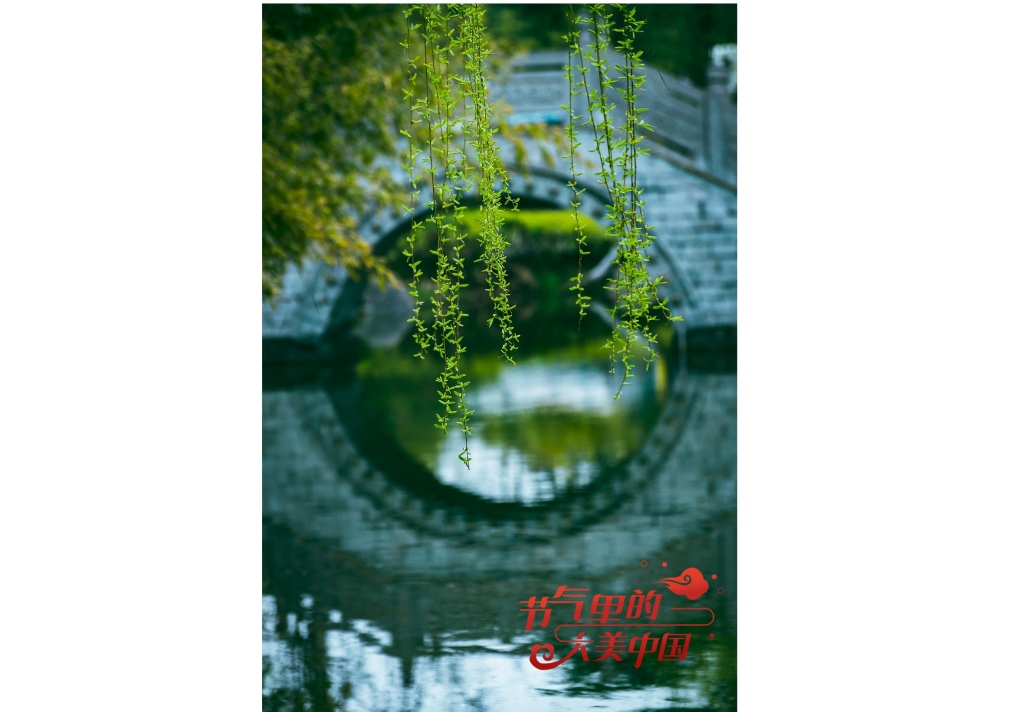
刀鱼在古代的食用方法很多,主要清蒸、煮汤、酥炸或做鱼鲙。《随园食单》中介绍蒸刀鱼的做法如做鲥鱼,用甜酒酿、清酱与鱼同蒸,不加水。如嫌鱼刺多则可刮取鱼片,钳抽出鱼刺。选用火腿汤、鸡汤、笋汤煨煮。晚清上海南汇人倪斗南曾赞道:“春三刀鲚炖鲜汤,不用煎熬异味尝。”
怕刺还可以选煎炸,不过袁枚吐槽金陵人怕有鱼刺,炙鱼到焦枯的地步,是不可理喻的。他分享了芜湖陶太太做法:用快刀将鱼背斜切,碎骨尽断,再下锅煎黄再添佐料,吃起来便不觉有骨刺。《调鼎集》记载炸过鲚鱼的油,古人也会去渣贮存起来,用此油浇各味菜肴或作汤羹,味亦鲜美。这真有点像调味料油的意思了。清代鲚鱼还会刮肉脱去细刺,油炸做鲚鱼饼,或与虾仁相混做成长圆丸子炸食。

除了鲜鱼肉,也有吃鱼子的。刀鱼的鱼子团在一处如螳螂产的卵,故称螳螂子。明代时候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宁,人皆喜食。如今倒不如刀鱼馄饨出名了。出于储存考虑,古代人民还把鲚鱼做成酱、鱼干。方便在其他季节或远行时携带食用。北魏《齐民要术》中就有取六七月取干鲚鱼做“干鲚鱼酱”之法,与生鲚鱼味无大差别。鱼与鱼酱都可作为礼物相赠,北宋梅尧臣有诗名为《邵考功遗鲚鱼及鲚酱》。
民国时期上海确实也有类似的产品,每年夏季吴淞口盛产凤尾鱼,食品厂便收来做五香凤尾鱼罐头,远销中外尤受南洋喜爱。1935年的《上海食用鱼类图志》中提到这类鱼每担最高三十元,最低八元。刀鱼与做罐头的凤尾鱼相似,但是要稍大一些。民国时刀鱼佳肴最经典当属刀鱼饭和面。(如今的昂刺鱼饭的做法也与之类似。)在上述图志这份资料中有记载当时的烹饪方法:
“刀鱼饭:把刀鱼破开,洗过之后,用竹钉将它的脊骨钉住在锅盖上,锅里照平常的煮饭一样,到熟的时候,把锅盖慢慢地揭开,所有的刀鱼肉自然落到饭面上。刺呢?因为鱼被竹钉钉住了,全副整个的悬挂在锅盖上,不会落到饭里,这一锅饭饱含着刀鱼肉的汁,盛起来加上作料,煮成汤饭,真可谓鲜美绝伦。”
这样的刀鱼吃法是从江苏传来上海的。起码在1934年,上海的镇江菜馆里能吃到。老半斋当时在汉口路浙江路口,新半斋在老半斋对门。所擅长的菜肴中便有一道“出骨刀鱼面”。与刀鱼饭类似,鱼钉于盖上,锅中盛好少许酒、酱油等佐料,细火烧之,等鱼肉落锅中后调芡便得到了最初的醇厚汤汁,1918年便已经有这样做法了。
至于馄饨,当时倒无提及。一斤的刀鱼馅可以包四十枚馄饨,如今的刀鱼馄饨用的是海刀鱼,腥味对于吃惯花鲢鱼圆的水乡孩子来说并不突兀与陌生。原本长江刀鱼的产量是相当可观的,但因江刀生存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过量的捕捞使得江刀数量骤减,而禁捕则是为了更长久的发展。不远的将来,杨花飞舞之时人们能再次与诗篇中的江鲚重逢。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