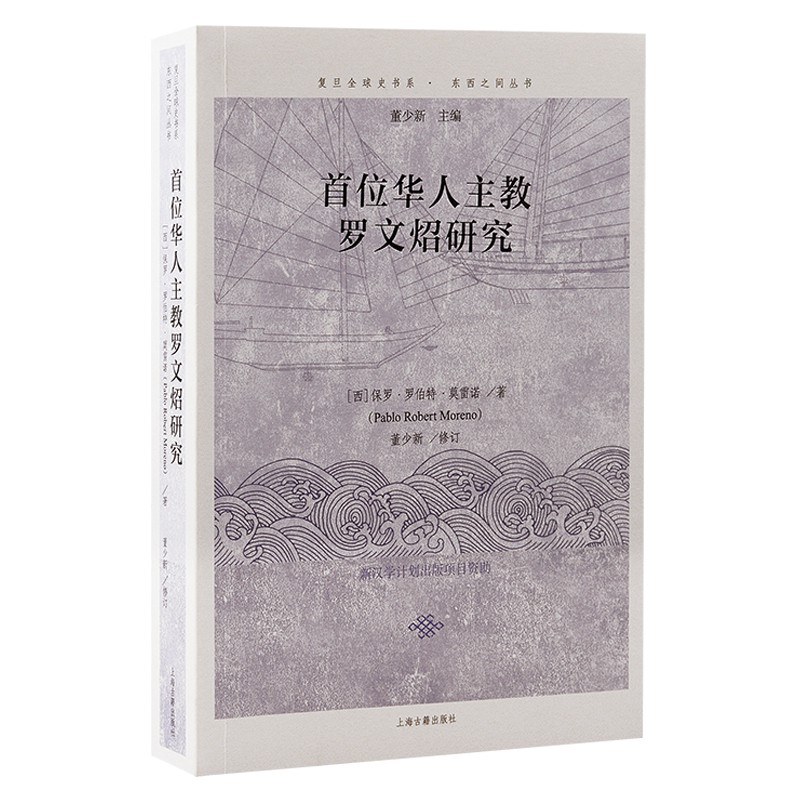
[西]保罗·罗伯特·莫雷诺著,董少新修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9月版
谈起中国人留学史,人们最熟悉的是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1828-1912),实际上中国人出国留学远早于此。但在鸦片战争以前,熟练掌握西文,并在归国后做出成绩的中国留学生却不多。例如近年来较受关注的华籍神父李安德(1695-1773)和李自标(1760-1828),前者曾在暹罗总修院学习了9年,归国后在四川等地传教,留下了一部长达700页的拉丁文日记;后者在意大利待了近20年,归国后曾在马戛尔尼使团担任翻译。《首位华人主教罗文炤研究》([西]保罗·罗伯特·莫雷诺著,董少新修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的主角罗文炤(罗文藻,1617-1691),不仅多次出国,而且归国后还成为首位华人主教,地位远在李安德、李自标之上。本书所讲述的正是罗文炤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孩子,成长为管理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江苏、安徽、朝鲜等广大地区的传教士和教徒的南京宗座代牧的故事,而故事背后则是中西相遇、明清鼎革、礼仪之争等大历史。
罗文炤1617年生于福建福安,成年前的他社会地位与教育程度并不高。1632-1633年,西班牙传教士来福安宣教,彻底改变了罗文炤的命运。他1634年领洗入教,1638年底前往澳门,1640年又转赴马尼拉。此后,他多次往返于福建与马尼拉之间,并在马尼拉学习了神学、西班牙文和拉丁文等。1654年,他在马尼拉晋铎为神父。1665-1671年,传教士因为康熙历狱而遭驱逐,罗文炤作为中国人,是唯一能在各省自由传教的神父。1674年,他被教宗任命为南京宗座代牧,并于1685年祝圣。罗文炤是明清时期唯一一位华人主教,再度出现华人主教已是1926年。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罗文炤像
人物研究著作的优劣,很大程度取决于对历史细节与人物心理的刻画水平。本书作为罗文炤的中文传记,成功兼顾了二者:本书通过对西文史料的细致爬梳,采铜于山,展示出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细节。由于罗文炤几乎未留下中文著作与书信,甚至提及他的中文文献也极少(张先清教授通过田野调查补足了一些遗憾),所以研究罗文炤需要依靠西文文献。在本书之前,袁若瑟(José María González)的《罗文炤传》(1966)虽以广博著称,也仅收集到罗文炤的书信47封,而本书却收集到罗文炤的书信120余封!作者所下的苦功不难想见。与袁若瑟将这些书信简单地归于罗文炤名下不同,作者注意到罗文炤署名的书信大部分系代笔,并将其分为罗文炤构思并亲笔书写者、别人构思并由罗文炤书写者、罗文炤口授而由别人代笔者、别人构思并书写者四类(第308页),从而辨析出它们各自代表着谁在发声。作者与修订者精通多门西语,两人对西文史料的掌握和运用可谓已臻化境。
更重要的是,本书还以档案为基础,对罗文炤与欧洲传教士的复杂心理进行了深描,私以为这是本书最突出的优点。当时在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有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奥斯定会等多个修会,而其背后又牵涉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罗马教廷等的权力斗争。罗文炤作为中国人,由方济各会士受洗,却加入了多明我会,其被任命为主教,则是由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所力推,但他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态度又更接近与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士相对立的耶稣会士、奥斯定会士。因此,他不得不长期在各种力量之间,维系一种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他并不友善。例如罗文炤虽由方济各会士受洗,但马尼拉的方济各会士却对他较为冷漠,所以他最后只能加入多明我会。而一些传教士在利用他的同时,又不信任他,例如有人怀疑罗文炤“访问各个教堂的动力在于他贪心银子”(第153-154页)。又如罗文炤被任命为主教后,需要经过祝圣才能正式就职。按照常理,多明我会士应非常欢迎本会会士升任主教,但当罗文炤前往马尼拉祝圣时,陪同他前去的多明我会士却百般阻挠,罗文炤委屈地写道:“他坚持我不能受祝圣是因为中国传教区所有神父都是这样跟他说的,而且他离开中国就是为了避免我受祝圣……为了试图骗我以及通过谎言出卖我,让我被关在这里……他告诉省会长中国传教区的所有神父恳求省会长要非常注意不要让我受祝圣,因为我反对多明我会并支持耶稣会的看法……”(第265页)他甚至气愤地写道:“如果我是多明我会的敌人,怎么没有把我在中国吊死?”(第269页)他被同事的背叛深深地刺痛了。罗文炤升任主教后,一些传教士也只是把他视为工具人,他们不希望罗文炤拥有自己的意志,屡屡试图对他进行操控。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有时不惜假冒罗文炤的名义,篡改或伪造书信。
另一方面,中国人对罗文炤也态度暧昧。虽然有很多中国教徒因为他升任主教而自豪,但也有不少人轻视他,他们更尊重欧洲传教士而非华籍神父。例如有传教士记载:“中国人不尊敬自己的人,即使是神父。这种情况在罗文炤身上就发生过很多次。”(第289页)“有一次我跟一个中国人谈话,告诉他已经有一位做到主教职位的中国人,他回答说:神父,这位主教和我没有什么不同,我也和他一样。他是个种大米的农民。”(第223页)罗文炤甚至还因为在马尼拉未获祝圣,最后只能从被关押的多明我会修道院屈辱逃走,而觉得自己“像逃犯一样”,不敢回家乡。(第302页)诸如此类的心理记述,全书俯拾即是。作为首位华人主教,罗文炤的成长之路遍布着荆棘与心酸。因此,本书可谓关于明清之际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心灵史。
除个体与微观层面外,本书在宏观层面的意义同样值得关注:首先,罗文炤是全球信息网络的一环,在中国与东南亚、欧洲之间“起到了一个联络与沟通的角色”。(第456页)他长期在中国和马尼拉之间,帮助运送传教士、资金、信件等,甚至在清政府实施海禁和迁海后,也未中止。罗文炤不仅服务于教会,其传递的消息还影响到西班牙人的军事决策。例如1665年,罗文炤从福建前往马尼拉传递信件等,同时向马尼拉政府报告了荷兰人在召集海军,很可能要将郑经赶出台湾,于是马尼拉政府决定派兵至Cagayan等岛,以防御郑经。(第145页)正如书中所言:“传教、贸易与政治三者之间联系紧密,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而罗文炤是该网络中的重要连接点。”(第144页)同时,罗文炤作为主教,又通西语,故有资格和能力直接向罗马报告,这是其他中国人难以具备者,他成为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向欧洲表达诉求的重要管道。
其次,罗文炤所经历的各种纷争,很多是世界性矛盾的中国投射。欧洲人在将欧洲及殖民地的各种争端(例如保教权之争、修会之争)迁移至中国的同时,又由于中国情景的加入,使事态变得更加复杂,而罗文炤本人经常并不知情。例如罗文炤在马尼拉祝圣失败,其根源是当时罗马教廷设计的亚洲教会结构方案本身充满争议,“罗马教廷任命罗文炤为主教和南京宗座代牧,并希望他在受祝圣之后去协助法国宗座代牧陆方济,不料马尼拉政府、西班牙传教士以及罗文炤本人都反对这一教会结构方案。”(第263页)正如作者所言:“罗文炤不够了解多明我会在整个教会结构上的角色,可能也不完全理解耶稣会与多明我会的竞争关系以及修会里上下结构的一些情况。”(第270页)本书是探究“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葛兆光语)的极好范本。
由于本书主要依靠西文史料,故受其限制,本书对欧洲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各方对罗文炤的利用着墨较多,并辨析了罗文炤所谓“中国声音”背后的欧洲声音(此为本书一大亮点),而对罗文炤的主体性不得不弱化处理。在传教士眼中,罗文炤经常是一位学问不深、态度摇摆不定、易受他人摆布者,但很多时候他其实颇有主见和决心。例如法国宗座代牧、多明我会士掌控了罗文炤的任命文件和主教津贴,试图以此要挟罗文炤,但他并未屈服,而是冒着无法祝圣、资金匮乏等风险,坚守自己对中国礼仪等的立场。因此,他并非无原则地“配合”谁,而是包含了一定的主动选择,他希望找到最适合中国人“本性”的、更“温和”的方式,正如罗文炤所言“难道你们以为我这么笨?”(第321、428页)又如在葬礼问题上,他充分意识到方济各会士、耶稣会士都在“用我的名字来支持各自的观点”,而且还表示“会等待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不仅以个人看法而且以宗座代牧的身份来表达我的观点。”(第334页)作为一位纵横于中西各派之间,并荣任主教之人,其自身的主体性,有待于日后更多中文史料的发现。
在本书的基础上,读者或可进一步参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著作(史景迁著,陈信宏译:《胡若望的疑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沈艾娣著,赵妍杰译:《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年),其笔下的胡若望、李自标与罗文炤一样,均出身底层,三书合观,当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先驱们游走于中西之间的心路纠葛,其开创性与艰辛性远在近代留学生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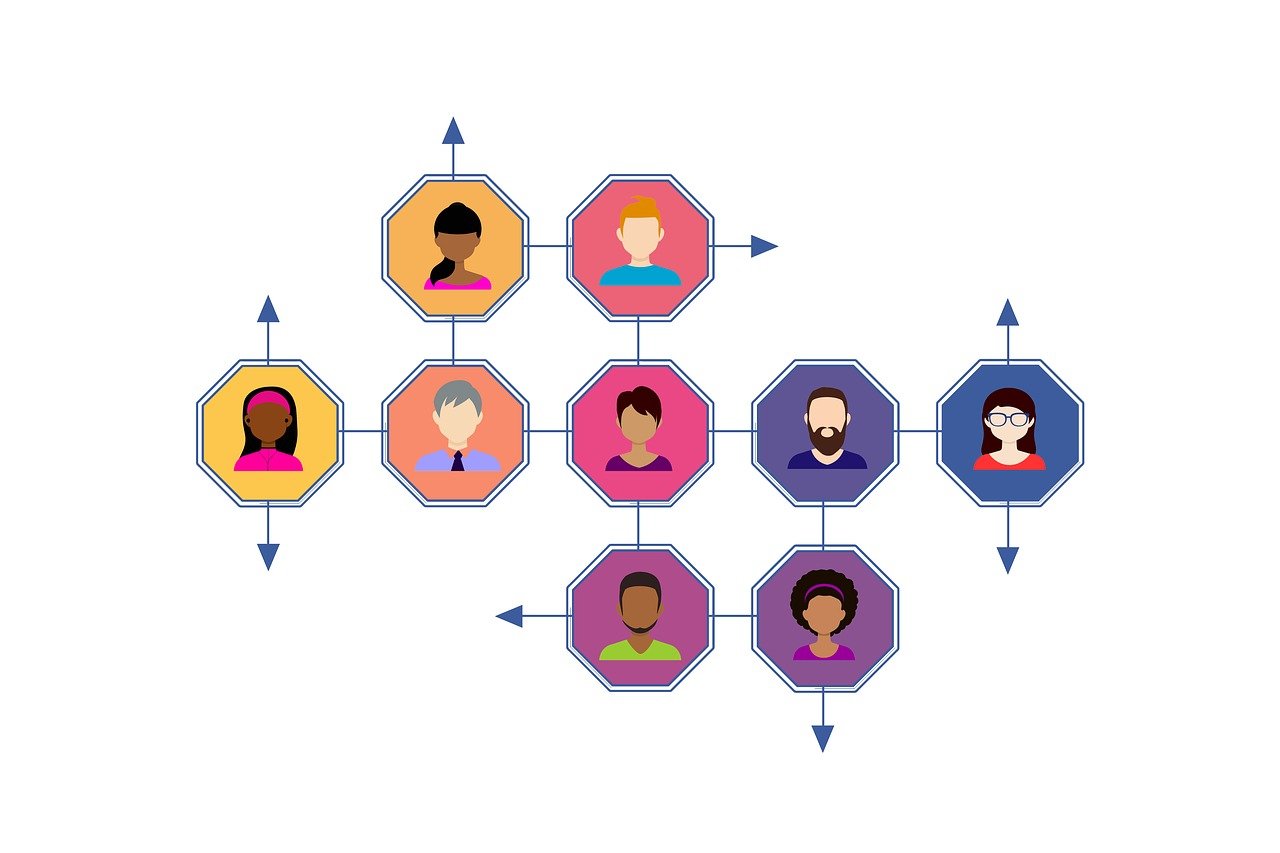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