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社会,我们似乎默认了一种约定:哀思只在清明节等特定的日子和场合公开表达,而在日常生活中,丧亲者的情感需求往往被忽视和压抑。这种对哀伤的时空限制源于传统文化观念,但忽略了哀伤的真实本质——它是一种持续存在、无法按日历开关的情感体验。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李昀鋆研究年轻丧亲者的哀伤体验,著有《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她自己也经历了母亲离世的哀伤。她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小群体。虽然很难检索到全国范围内由官方公布的总体数据,或查询到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抽样数据,但参考西方社会的数据大概能够推算出父母丧失在年轻子女群体中的流行率(prevalence)在 3.4%至 11%之间(作者博士论文,39页)。也就是说,100名年轻子女中约有3.4名至11人经历了父母的丧失。

澎湃新闻:华人社会提倡的“节哀顺变”来自《礼记》,古代丧礼是为了让人的自然情感能够在仪式中得到抒发和宣泄,制定了特定的仪式表达哀情。同时,为了保护生者不被哀伤之情过度伤身,很多丧礼的具体规定都贯穿着节制服丧者哀情的精神,譬如,要求子女在父母去世三日后必须饮食,为父母服丧期不得超过三年等等。在你看来,在华人社会的语境下,我们现代人的哀伤出了什么问题?
李昀鋆:我做的不是一个历史脉络的研究,所以整个文化究竟是哪一个部分突然间不一样了?我没有办法给到一个答案。但如果我们去看《礼记》,它在讲节哀顺变之前,是有大量的篇幅规定悼念逝者的具体做法。整个社会是有大量的文化和社会的仪式让丧亲者慢慢地过渡。当然我们也可以讨论说那些仪式可能对于一些人而言负担太重了,但相对来说,它规定的哀伤时间是限定的,也比我们现在长很多。
其实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和机构是有丧假的,丧假可能也就最多三天,如果超过了三天,你就必须自己再用其他假来处理。你处理完丧礼之后,你就被期待恢复正常。“节哀顺变”就更强调了“节哀”的一面。
当然我们中国人都很相信中庸之道,把握哀伤的平衡是最好的。但现实中,在葬礼之后,许多人的哀伤连“表达”的机会都很少,更别说走到“过度”的阶段了。
我的研究对象的经验跟我很不一样。因为我曾经接受社工教育,所以我会有意识地在丧礼上宣泄我的哀伤。但是我的年轻的研究对象会假装坚强,他们看到了自己另外一位父母在崩溃,丧礼上又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他们就会在丧礼期间去承担家庭里面那个支柱的角色。
另外,大家对于哀伤有一个误解,以为像电视剧里那样,知道那个人去世了之后会一下子哭得很夸张,或者是会有很多反应。我不否认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在当下其实脑子还在消化死亡,根本就哭不出来,正好又有一堆事做,就去做那一堆事了。事后他们会反思,我为什么在丧礼上哭不出来?我是不是不爱他?所以就会留下来一些自责和遗憾。慢慢地,哀伤明明在他们的心里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越来越大,甚至是越来越大的痛苦,丧礼结束后,就更难找到一个宣泄情绪或者说出哀伤的合适时机了。

澎湃新闻:不论是职场还是家庭这样的小环境里面,大家似乎也是希望相处的人最好是一个各项功能“正常”的人,有那么一种不容许零件坏掉的感觉。
李昀鋆:因为西方关于哀伤的研究稍微多一点,讨论也多一点,就有学者就总结了在工业化社会中我们对于哀伤的不同的论述或是想象,其中大家对于grief的一个想象就是:哀伤应该是有时间限制的。意思是过了这段时间你就应该结束,你应该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你应该继续做一个功能正常、很有效率的打工人。因为他也看到了其实工业化社会中我们对于人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于哀伤的想象也在开始被重塑:就连哀伤也必须守时、有度、迅速归位,成为一种“可管理的情绪”。
回到华人社会就更加明显了,比如我的研究对象里面也有人觉得,哀伤就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东西,他花了很多时间处理自己的哀伤,还很影响他学习。但是他其实没有办法跟他当时的导师去讲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去合理化说父母去世这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本来他可以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最后他接纳了这份影响,直接放弃了那个学位,然后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澎湃新闻:你认为丧亲对年轻子女来说是一次认知结构的失序。在应对这一困境时,有重构秩序成功的案例,但极易失败。你的访谈中有多大比例的年轻子女真正“缓过来了”?重构秩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李昀鋆:所谓“成功”缓过来的话,其实就只有一位,她是很明白地告诉我,她经历了一个顿悟的时刻,对整个事情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但是从大部分访谈对象给我的经验分享中,我不觉得他们是真正缓过来,我觉得他们是选择接受了一份被改变了的认知。
这些年轻人在经历丧亲之前,他们对于世界会有一些常见的预期。比如说会觉得好人有好报,我们的父母都很善良,应该能够像大部分人的父母一样在进入七八十岁的老年阶段后才正常去世。结果,砰,他们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可能突然间去世了。这对他有很多冲击,冲击他整个对世界的看法,他一直很想知道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的同龄人的父母依然健在,我们家为什么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努力去理解这件事情,也找到了很多“替罪羊”,但是这只是短暂让他们停一停。比如,可能他用抽烟喝酒这个理由来解释父亲为何早逝,但有亲戚抽烟喝酒得更厉害,然后活到了90岁,他就依然会痛苦:怎么这个解释不通啊?所以他们又开始有一些解释整个世界、解释失去、解释死亡的其他的想法。
这些新的想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很“丧”的一些认知。他会觉得好人不一定有好报,或者命运就是不公平的,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也不可能保长命等等。他会有很多很负面的人生想法。
我觉得他们很难说有一个点是真的缓过来了,至少在他们当时的那个年龄阶段里面,他们只是走到了那一步,就选择停在了这里,接受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他们自救的一些选择。因为那份真实的失去会很真实地不断在他的生活里面出现。别人有父母陪伴举行婚礼,或者别人生小朋友时有父母照顾……在这些不断出现的人生重要节点里,他都会再反刍一下那份痛苦,然后再想,他的生命、他的平行时空里面的世界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状态真的让他们很痛苦。
澎湃新闻:你提到,对于重构秩序失败的人来说,他们的自救经验包括有意识地命令自己停止、要求为自己而活、分割丧失和现在的人生。本来想问这些自救经验是否实际上内化了社会对他们压制哀伤的要求?但是现在听了你这个解释之后,可能也不一定是一种内化,也许真的就没办法。
李昀鋆:因为这个失去太重大了。其实我做这个研究,我也在反思的是,我跟他们的经验很不一样。我其实是很有意识地反抗社会对我压制哀伤的要求。那个时候我妈去世刚刚半年,当我和家人倾诉我对母亲的想念时,我的家人亲戚都跟我说,你不要再哭啦,你要继续啊。这种话我听太多了,但我不管,我会直接哭。而且我在日常跟我父亲打电话时,也会很直接告诉他,我最近什么时候又想到妈妈了。
但是我发现我的研究对象,大部分人其实很内化这个社会对压制哀伤的无形要求。一方面可以说是他们很害怕自己的哀伤触发家人,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他们相对来说可能更加遵从社会的规则,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哀伤收起来,应该自己去消化或者是假装正常。
我们会觉得90后或者00后好像应该更有反叛精神,或者是更有自己性格的部分吧,我又觉得挺有意思,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呢?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也在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呢?会觉得本来他们应该像我一样啊。
澎湃新闻:吴飞的研究认为中国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过日子,“过日子”将人的一生分解为“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老、送终、年老、寿终”等环节(279页)。这些生命环节通常是家庭来教授传习的,对年轻丧亲者而言,“过日子”的主角转换成了自己,他们需要直面这些生命历程。社会如何填补这一家庭功能的空白?
李昀鋆:如果去世的是父亲,年轻的丧亲者就开始操心自己母亲的照顾责任。我看到的就是他们自己一步一步去摸索,努力把母亲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来照顾,操心母亲的养老和看病。
说实话,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原子化了,很多事情,包括我母亲的丧礼如何操持,其实也不是我的小家庭告诉我的,是大家族的人帮忙,告诉我是这样子做的。现在这些东西就变成了自学,然后你就会发现,学校从来没有教过这种东西,真正重要的课题从来不是学校教你的,你只在学一些没用的东西。你遇到了一个问题,你就只能自己摸索到网上去查,然后发现照顾母亲或者老年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相对来说,男性可能会比女性更能接受整个“过日子”的叙事。年轻男性经历了丧亲后,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正常的生命选项。但是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这段路可能会因为丧亲中断。因为除了经历丧亲的各种冲击之外,她会发现,父亲会很快再婚或是很快去相亲。很多年轻女性在经历了父母尤其是母亲去世之后,她会对“过日子”的人生路径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她会停在那里,可能会有其他的探索。但对于男士好像这个部分的冲击会小一点,他会扛起更多的家庭责任。
澎湃新闻:你提到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在“搁置死亡”这一点上尤为成功。乔治·瑞泽尔的《社会的麦当劳化》曾描绘“现代的死亡方法”:现代的死亡发生在医院里,可能十分隐蔽,在清洁了萎缩的身体之后,尸体最终被送往现代墓地(211页)。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城市中,死亡过程的“套餐化”是否加剧了哀伤处理的困难?
李昀鋆:我最近在香港参加一个义工培训,医院的社工说,如果是亲人在医院去世了,那个医院可以做到让家属有4个小时跟遗体相处的时间,如果家属有特别需要,比如有佛教的信仰,需要围绕遗体念很长时间的经送别逝者,可以延长到8个小时。我觉得其实还是蛮人性化的了,因为香港医疗资源非常紧张,他们恨不得你赶紧出院的这种情况下,也能够给你提供一定的时间。
我自己的经验就觉得,现在整个死亡处理的过程是特别快的。我其实还在消化整件事情,下一步就已经开始了。大家该做的事情都做一下,都是很程序化的。你以为丧礼很慎重,很重要,会有很多你个人的、家庭的,或者逝者的一些部分,但是实际上反倒是那个公司决定了很多东西。然后你也会害怕,因为大家现在都会说他们是“宰”你们的,你其实更多的注意力就放在了别的部分上,你很难去考虑你在丧礼上还能宣泄一下你的情感,这个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在访谈中,不少年轻子女也表达了和我类似的困惑与痛苦:亲人的去世在他们心中是一件天塌下来的事,但整个社会却像在催促他们“赶紧处理完”,“别耽误正事”。
这个现象的确和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逻辑下的“效率至上”密切相关。在这种逻辑里,死亡被视为“生产流程中的中断”,丧礼被压缩为形式,哀伤被看作情绪负担,甚至“无用”的时间。它主张“快速清理”、避免情绪干扰,从而使生者尽快“回归轨道”。
这当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与城市化、去宗教化、制度理性化等多重现代进程有关。但确实,在资本主义强调效率与生产的社会里,死亡越来越被“搁置”,哀伤越来越被“私人化”,这对正在经历丧亲的人来说,是一种深刻的孤立感。
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回到传统,而是从传统中重新理解:一个人死去,不只是肉体的终结,也是一段关系的断裂,一个世界的崩塌。如果社会不再为这种崩塌留出空间,那它就会积压在无数人的身体和心里。
我觉得其实可以在家庭里面慢慢开始谈论哀伤,这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定会有眼泪,但也可能会带出很多疗愈的时刻,因为是这一个家庭共同经历了这一位成员的失去。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互相彼此找到力量,允许接纳这些哀伤,可能会比一个专业人士来给你提供辅导好很多。
虽然我的研究过程其实更多的是收集信息,做出一篇学术论文,但很多访谈对象说,跟我聊完一次访谈之后他们自己觉得舒服多了,让他们自己能够正视自己的哀伤,好像有一些事情他们也想通了。所以,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一个很多时长的哀伤辅导,可能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承托了一次他的哀伤,让他哀伤有一个出口,他就已经缓过来很多了。
澎湃新闻:除了丧亲的哀伤难以排解之外,现在年轻人的失去感可能是更难排遣的。
李昀鋆:其实bereavement这个词语,从狭义的理解来说它指的是丧亲,如果广义的理解,它其实讲的就是失去。这份失去可以是因为亲人去世而产生的,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失去。
我的确会明显感到好像最近大家对于年轻人的精神健康越来越关注。年轻人在一个超级内卷的时代里要怎么看到自己人生的希望?原来可以通过读书或者就业实现一些人生的向上流动,获得所谓的更幸福的人生,现在的竞争越来越大,对于人的压榨的那种感觉好像越来越明显,他们的情绪真的是承载了好多好多。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后面认识我的人其实也不会知道,我心里面很苦,但看起来是一个天天很开心的样子,然后正常地读书,“正常运行”。我们都内化了很多社会对我们的期待,感觉都是天生的牛马的那种,尽量维持外面的体面,回到家里面都是一颗破碎的心。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什么感受,就我自己当时的经验,我以为人生往后面一定是好的,但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发现人生的真相是很沉重的。后来通过研究和认识了更多人,我也会慢慢地感受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很沉重的话题,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丧亲,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其他的经历,心里面都有一块很沉重的石头在那里。
澎湃新闻:你接受了这么多媒体采访之后,自己会不会有点消耗的感觉?
李昀鋆:因为我本来有一份全职的工作,所以我都是夜晚来跟大家聊天,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其实我已经从这个研究里面获得很多了,我希望大家把关注点放到丧亲群体上面,希望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关注。
接受采访后我发现,的确每个人对于哀伤的理解和消化还是挺不一样的。其实我也会好奇,为什么会对我有兴趣,为什么会对这个题目有兴趣。我发现,的确大部分人之所以有兴趣,要么是因为自己的丧亲经验,要么是因为自己身边的人经历了丧亲。
我国没有丧亲人群的官方统计数据,丧亲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热门的指标,不会把它放到人口普查里面。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是通过文献回顾去推算西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中国可能可以参照它,但是也不确定那个数字是不是真的吻合。这本书出来之后,很多人写邮件给我或是在公众号里面给我私信,很多朋友会不断告诉我消息。我发现确实有很多年轻人是在经历一份失去,而且是很重大的失去,也一直对自己的情绪很困惑。这本书让他们感觉到了被理解,有很多安慰,所以就还是很开心的。
我想强调的是,所有的丧亲群体都需要被看见,不要去比较哪种更苦。其实我自己一开始也会有这种假设——要经历多严重的失去,才会有这种哀伤。但到最后我觉得要强调的是所有的哀伤,不管失去的方式是什么,失去的亲人是谁,他的哀伤都需要被关注,不要去比较他的哀伤究竟值不值得或者应不应该。在你有限的范围里对他多一些理解,给一点点安慰,就已经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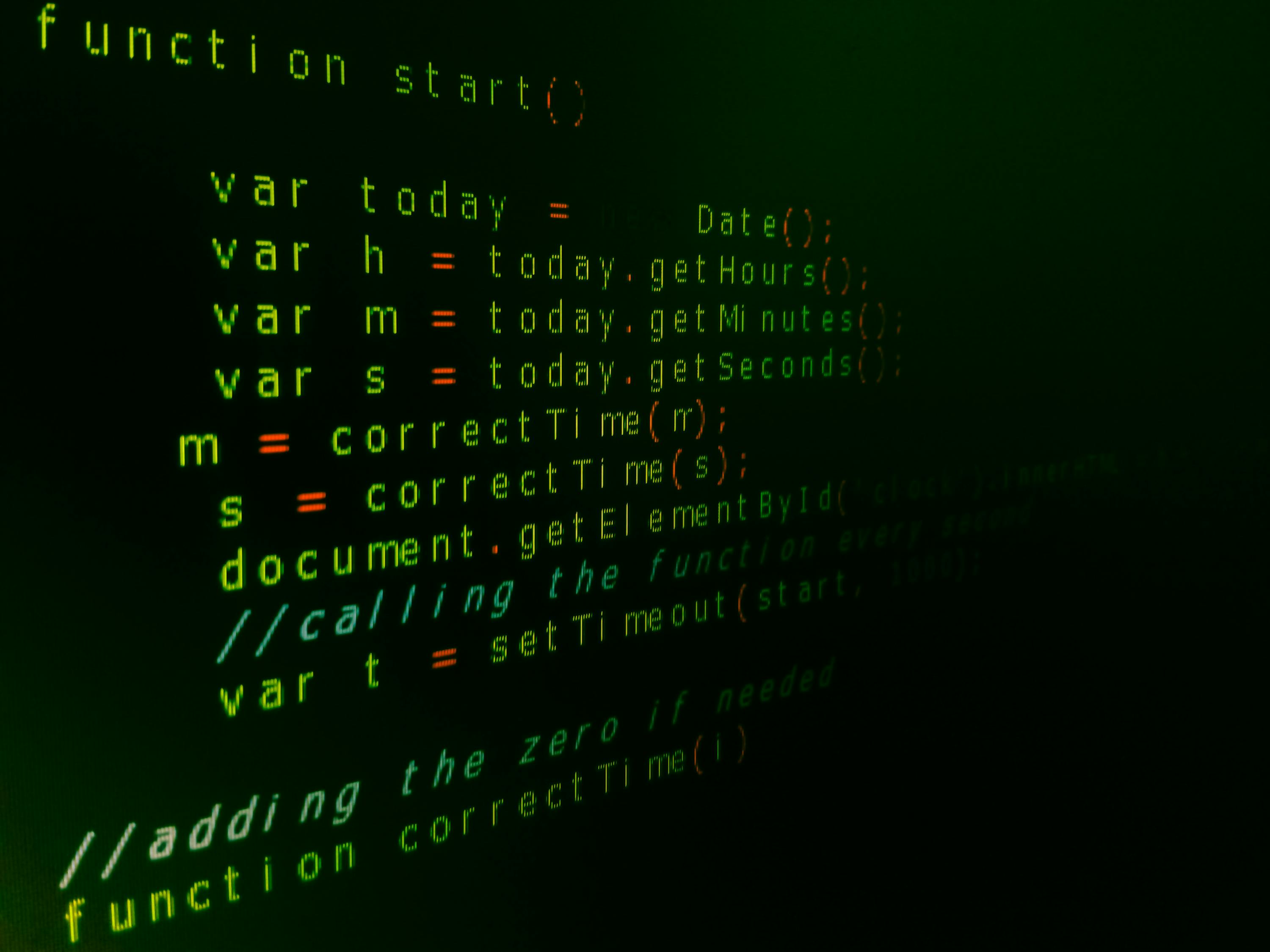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