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实施一系列针对移民的措施,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开始陷入紧张情绪。据《纽约时报》今年3月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43个国家的公民实施旅行限制。越来越多的移民开始担心自己将受到不断变化的签证政策和反移民言论的影响。

然而,梅吉亚斯也指出:将即将发生的灾难归咎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是最简单的做法。事实上,民主党长期以来也支持放松监管和私有化的自由主义政策,正是这些政策促成了如今“科技寡头阶级”(broligarch class)的崛起。在一个由全球最富有的人操控的“科技-独裁”国家(klepto-fascist state)面前,反抗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些科技巨头正是通过数据掠夺建立了他们的帝国,而人工智能只会加剧这种掠夺。人们必须拒绝殖民主义的核心谎言——即“强权即公理”。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两位作者分别作出了呼吁。梅吉亚斯认为:移民的福祉,也包括我们所有人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共同夺回对数据的掌控权,决定哪些数据被收集,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罗德里格斯则提醒人们:任何针对最脆弱群体的迫害,最终都会蔓延到那些看似不受影响的人身上。在阻止他们之前,所有人的隐私和自由都处于危险之中。
法国农业生态运动的历史与挑战
政治领域中使用的术语常常依赖于笼统的概括:“生态主义者”“农民”“城市人口”“决策”“消费者”等等。这些简化通常为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服务。例如,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工会FNSEA一直在捍卫农业世界的统一性——但是在其自身权威下。然而,过度简化现实、挤压掉所有细微差别、隐藏少数派运动和那些产生社会创新和试验新模式的边缘领域,这总是危险的。在平稳航行时,这些新事物可能会造成干扰,但当船开始倾斜时,它们可能会成为救命稻草。因此,在全球食品系统已经开始出现“漏水”、工业文明在其自身破坏力量的重压下“溺水”的时候,重新审视那些代表性不足且常常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生态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很有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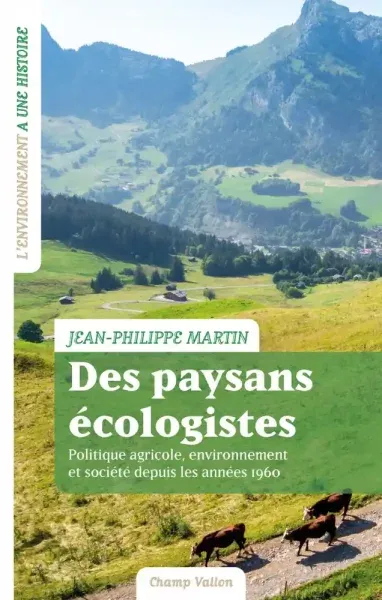
《生态农民:1960年代以来的农业政策、环境与社会》
让-菲利普·马丁的《生态农民:1960年代以来的农业政策、环境与社会》(Des paysans écologistes. Politique agricole, environnement et société depuis les années 1960,Paris, Champ Vallon, 2023)是一部追溯法国生态农业运动发展历程的著作。作为历史学家和农民联盟(Confédération paysanne)研究专家,马丁在书中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法国农业运动的全景,既包括主流农业组织,也涵盖了各种少数派生态农业倡议。
这部著作详细梳理了两种早期对工业化农业的批判性运动:一是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并在1960年代通过“自然与进步”(Nature et Progrès)组织在法国发展的有机农业运动;二是源于工会主义传统、特别在法国西部地区发展的工人-农民运动,后者强调农业的经济性与自主性。
第一种有机农业及其先驱——生物动力农业(biodynamic agriculture),接受了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的人智学(anthroposophy),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德国、瑞士、英国(1945年成立社会协会)和法国发展起来,尤其是1964年创建了“自然与进步”组织,该组织汇集了医生、农民和消费者。
这一运动强调健康和生态问题,但并不忽视社会问题。它由保守甚至反动的成员组成,同时又有倾向社会主义的成员。后者在法国催生了全国有机农业联合会(Fédération nationale d’agriculture biologique,成立于1978年,归功于几个运动的统一以及1981年法国政府——特别是农业部长皮埃尔·梅尼埃[Pierre Méhaignerie]——的认可,这导致了法国和欧洲“生物”或“有机”标签的创建)。
在工业化农业占据霸权的时期,有机农业提供了一个社会经济框架,用于保存和发展后来被“重新发现”的替代性农艺和兽医实践以及各种社会和商业实践,特别是与“消费者-行动者”的直接联系。事实上,有机农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消费者愿意为其产品多付一点钱,预兆着所有工会提出的一项要求:需要真正有利可图的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农业一方面大声要求提高价格并谴责消费者的矛盾行为,另一方面又毫不犹豫地因为高价格而贬低有机农业。诚然,在前一种情况下,重点是支付“生产成本”(农药、化肥、设备和银行债务),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重要的是保护环境和健康。差异立即显而易见。套用帕斯卡的话:农业企业这一边是真理,另一边则是谬误。
第二种生态农业运动兴起于工会主义内部,特别是在法国西部,这个地区在畜牧业中有着相互技术援助的强烈传统,并且以小型、劳动密集型农业为特征,与以谷物为主的东北部地区形成对比。
在饲料革命之后,当草地栽培取代永久性草原时,畜牧业经历了玉米饲料革命及其衍生物:杂交种子、化肥、植物保护产品、收割机、青贮饲料收割机、食品补充剂和大豆——简而言之,一系列进口的“生产要素”剥夺了生产者的自主权,使他们依赖于农工业综合体(agro-industrial complex),同时将他们的地位降低为分包商和临时工人。与农民之名相反,他们越来越像无产阶级。
正是为了反对这些趋势,在技术领域,像CEDAPA这样的组织成立了。CEDAPA受到农业科学家、活动家安德烈·波雄(André Pochon)的影响。同时,出现了一种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批评,强调工人而非农民的权利。这一运动由伯纳德·兰伯特(Bernard Lambert)领导,他在政治上靠近自我管理运动(self-management movement),后于1981年作为社会党人当选为议会议员。
这些运动要求农业“更加经济和自主”,这引自雅克·波利(Jacques Poly)1978年报告的标题,当时他是国家农业研究所(INRA)的主任。这些不同的运动于1987年联合起来,形成了“农民联盟”,赋予“农民”一种政治意义,并将其带入公共话语,作为全国农业经营者联合会(FNSEA)推广的农场主模式的替代方案。在这一趋势中更为低调的参与者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MODEF(法国家庭农场保卫运动组织)。
马丁着重描述了20世纪80至90年代生态理念如何在农民群体中逐渐扎根,以及疯牛病危机、转基因生物争议、水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如何促使农业界重新思考其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且自主的方法”对环境的危害要小得多。然而,该运动的社会议程与其生态关切(这些常被视为“城市”议题)之间的接近则需要时间。到了70年代末期,在放弃工业主义的农学家勒内·杜蒙(René Dumont)1974年总统竞选活动之后,兰伯特认识到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但该运动提出的社会批评被许多小生产者所接受,这些小生产者由于缺乏土地,加强了工业化生产,特别是通过养猪和家禽养殖。因此,生态问题在农民联盟内部引起了分歧。它通过推广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一种生态和社会关切的结合)逐渐加入了生态运动。生态关切也蔓延到了主导工会,其成员转向有机农业。随着1991年新工会“农村协调组织”(Coordination rurale)的出现,全国农业经营者联合会(FNSEA)失去了一些代表性权重。即使FNSEA试图接受有机农业,特别是在它控制的专业组织中,它优先考虑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合理”(reasoned)农业。
这些努力很快受到两个新担忧的威胁:大型食肉动物特别是狼和熊的回归(要么是由于土地荒废,要么是因为它们被有意重新引入),以及动物产品消费的减少(弹性素食主义/素食主义/纯素主义三件套)。大型掠食者的回归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和畜牧业,而动物产品消费的减少则可能影响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
这两种趋势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相当数量的“农民”是靠在不适合工业化的牧场上进行广泛畜牧业而生存的。纯素主义和大型食肉动物因此成为广泛畜牧业的威胁,而广泛畜牧业依赖于高山草地和从事这种畜牧业的农民。
这场争论揭示了追求生态社会的内在张力,这使得有必要解决多重且常常相互矛盾的优先事项:生物多样性、自然性、能源、土壤保护、水资源和景观。这些矛盾只能通过妥协来解决。这些紧张关系重新激发了一种对立的“城市老鼠”(被认为是“无根的生态学家”)和“乡村老鼠”(被认为是“有根的当地人”)的叙事。虽然这种冲突常常可能是残酷的,但它并不本质上排除妥协的可能性。
女性在专业中的角色日益增长也是一个反映整个社会的趋势。这对于应对农业的代际更新这一巨大挑战至关重要——这是一个真正的头痛问题,因为在农场如此资本化的时代,个人继承已经变得不可能。对此有三种解决方案:按照农民联盟的建议拆分这些农场;按照“土地联系”(Terre de Liens)所倡导的,让它们的资本还有劳动力共有化(mutualization);以及如全国农业经营者联合会(FNSEA)自1960年以来在实践中所做的那样,接受有限责任公司模式和基于公司的农业。最终的选择将取决于实施哪些公共政策。
农业工程师马修·卡拉姆(Matthieu Calame)在3月20日刊发的书评中,对马丁关于“生态农民自己成就自己”的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马丁的核心论点存在矛盾:一方面说生态农民“自己成就自己”(made themselves),另一方面又承认他们“享受支持”(enjoyed support,指享受生态组织和城市消费者的支持,这些消费者购买有机和本地产品,并接受社区支持农业)。他不认同马丁试图将生态农业“农业化”(agriculturalize)的防御策略,认为这种策略没有必要。他反驳了农业产业化是内源性过程的观点,指出农业产业化同样是受外部刺激的结果,而非农村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
卡拉姆认为生态农民的优势不太在于他们的本土性——即“自己成就了自己”——而在于他们为农业与社会之间的新契约铺平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享受”支持:他们与城市运动谈判,与之分享价值观和目标,商定了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流条款,他们希望这种交流有朝一日能成为常态。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