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蒙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文化传承与文化成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更是中国文化早期西传的重要基础。早在16世纪,蒙学经典《明心宝鉴》便成为最早被译为西方语言的中国典籍,并产生了多个译本。这些译本的差异,不仅源于译者的身份和翻译策略的不同,更反映了早期西方人中国知识观的演变。
《明清蒙学经典与早期西人的中国知识观变迁》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2025春季学期读书会“本文内外:世界文学的跨界叙事与知识生产”的第一期,由胡文婷主讲,魏京翔与谈。胡文婷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魏京翔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比较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西班牙Ibero-América Studies (国际刊号:ISSN:2696-2527)期刊学术顾问,编委会成员。长期致力于西班牙早期汉学史研究,中西文化关系史研究。
本次读书会围绕《明心宝鉴》这一蒙学经典与早期来华西人中国知识观的变迁展开,胡文婷聚焦于耶稣会士罗明坚的拉丁语译本,魏京翔则关注多明我会高母羡和闵明我的西班牙语译本。通过这一文本个案,把握早期来华西人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方法,以及如何将其纳入西方文化语境内的具体路径。这次对谈希望突破传统的译介学维度,通过横向的和纵向的对比分析,揭示出文本流动过程中的认知路径差异和知识生产机制的不同。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读书会内容。文本经发言者审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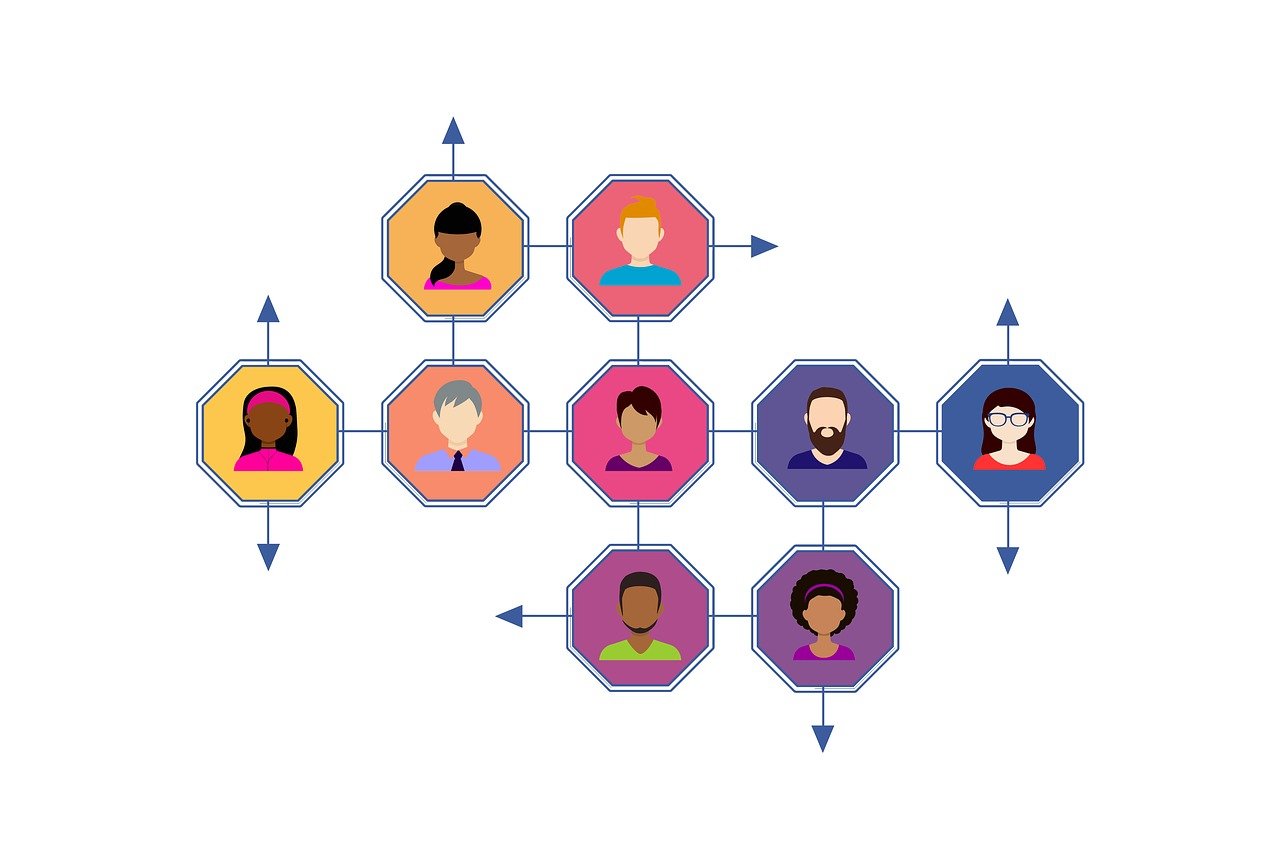
胡文婷:罗明坚的《明心宝鉴》拉丁语译本是近几年新发现的一部手稿,实际名为《诸家名言汇编》(Diversorum autorum sententiae ex diversis codicibus collectae),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拉丁语手稿合编在一起,藏于意大利罗马·伊曼努尔二世国家图书馆。该拉丁语译本共计31页,间有破损,均是拉丁文,没有中文对照,手稿标题左上方列有时间“1593年11月20日”(Die 20 Mensis Novembri 1593),后面写有“献给耶稣玛利亚的第一本书”(Liber primus,Iesus Maria),在手稿末尾(finis)有罗明坚的译者声明:“本人罗明坚于1592年11月20日晚完成该册书的翻译并将其献给万福圣母(Die 20 mensis Novembris 1592 in Vesperis Presentationis Beatisse.ae Virginis traductio huius libelli fuit absoluta per me Michaelem de Ruggeris)”,末尾处的1592年那里有对数字2进行涂改的明显痕迹,且罗明坚也首次彰显了其译者身份。译本分为3部分,以liber primus(第一卷),liber secundus(第二卷),liber tertius(第三卷)表示,标在了手稿页上端。另,该拉丁语译本共分为十六章(caput),翻译条目总计240条,是对《明心宝鉴》的节译。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最早发现了这组手稿,并就《诸家名言汇编》的日期进行了说明,认为该书是“1593年11月开始翻译并于当月20日完成”。另外,他对这本书的定位是中国多位作者关于不同主题的汇编(Miscellanea di diversi autori cinesi su soggetti diversi),且是作为“四书”附录存在的。另外,《明心宝鉴》还有其他几个译本,涉及西班牙语、英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等。
魏京翔:我来简要概述一下《明心宝鉴》这部典籍的西班牙语译本情况。《明心宝鉴》(Beng Sim Po Cam)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高母羡(Juan Cobo)最重要的中文译著,也是第一本被完全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中文典籍。关于该书的形成时间,学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1591年、1593年和1595年。这部伟大的译作并没有在16世纪的马尼拉或马德里出版,而是以手稿的形式存留数百年之久,其原件始终存放在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文献编号为Ms.6040。1929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发现这一译本,认为该书的中文和西班牙文译得都十分恰当,这才开始在学界引起反响。迄今,《明心宝鉴》正式刊布的西班牙文版本有:1924年路易斯·冈萨雷斯·阿隆索·赫蒂诺(Luís González Alonso Getino)在马德里版;1959年卡洛斯·桑斯(Carlos Sanz)在仔细研读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编辑,马德里维克托里亚诺·苏亚雷斯(Victoriano Suárez)大书店不仅出版了《明心宝鉴》的纪念版,还出版了桑斯为其撰写的导读;1998年,西班牙汉学家欧阳安(Manél Ollé)在巴塞罗那发布了《明心宝鉴》的现代版本;2021年,学者李毓中出版了中国台湾版本。当然,迄今为止,对高母羡这部作品研究最深入的当属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博士生刘莉美女士的毕业论文,2005年,她以专著的形式将其出版。据我所知,高母羡所译《明心宝鉴》的最新版本由线装书局于2022年11月在北京刊布,不仅包括了西班牙国家图书馆藏1590年中西文双语手稿的影印件,还附有西班牙多明我会士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呈递给当时西班牙王储费利佩的信。应该说,这一为了纪念中国-西班牙建交五十周年而发行的版本最为全面。
高母羡的手稿共计150余页,撰写于彼时菲律宾通行的米纸(papel de arroz)上。该译本首页写有:“一本中国书籍,名为《明心宝鉴》,指的是清澈心灵的宝镜,或是用以启迪精神的宝镜,以此可以看到清澈的心灵”。另外,在贝纳维德斯神父写给费利佩王储的信中,提到“该书是中国哲学家关于道德和美德判断的合辑,可以引领人们回归自然之理并最终抵达自然给予人们的完美合一的状态”。为了翻译这部中文劝善书,高母羡以《新刊图相校讹音释明心宝鉴》为底本,采用中西对译的方式,即西文在前,中文在后,但中文手抄笔迹不尽相同,推测应由不同的旅菲华人完成誊抄工作。在新文献,尤其是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的《明心宝鉴》拉丁语译稿发现之前,高母羡的译本在西方汉学界具有源头性的地位。它不仅涉及早期中国文化的外传,还关涉到不同西人群体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打破了学界一直以来华耶稣会中学西传活动为研究主体的惯性,将欧洲托钵修会的文化实践纳入到研究框架之中。
上述再版的西班牙语译本基本都是围绕高母羡的原始译本展开,但切入的角度是多样的,从最早的传教史视角,到后来的汉学和跨文化视域。当代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是从翻译史、教会史、比较文化形象学等方面切入,但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当作是一个知识产品的话,也可以从这本书管窥到在进入大航海时代后,中国知识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是欧美和东南亚地区)的再生产和流布。至于17世纪西班牙来华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翻译的《明心宝鉴》西语译本却未受到很多关注——该译本被收录进闵氏撰写的《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Tratados históricos, políticos, ét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quía de China)第四卷,下文简称《论集》。闵明我虽然与来华耶稣会士在神学观念、传教策略上颇有分歧,其所主张的“西化”立场也与利玛窦倡导的“文化适应”政策截然不同,但毋庸置疑,他依然是“17世纪西班牙汉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和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其撰写的《论集》因对中华帝国翔实的描摹,被伏尔泰称为“在有关中国的事上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好”。
《明心宝鉴》的早期西传背景
胡文婷:关于它的译介背景,我集中在耶稣会士罗明坚的翻译实践上,当然其中肯定与高母羡的译介背景会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首先,寻求自然理性,提供传教依据。罗明坚汲取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理论中的自然神学部分,认为信仰可以通过理性获得,而理性是普遍存在的,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人,而在异教徒中同样可以觅得理性的踪迹,鉴于《明心宝鉴》中的很多伦理道德都与古希腊哲学甚至是圣经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感,这为传教士在华传教以及争取传教支持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

罗明坚(Michael Rogerius,1543-1607)和利玛窦(Matthaeus Riccius,1552-1610)抵达中国海岸。这是来自P. Cornelius Hazart所著的《教会历史》中的插图,1668年在安特卫普出版。
其次,“文化适应”政策中的伦理学转向。罗明坚、利玛窦入华最初是沿袭着耶稣会士在美洲及在日本的传教经验,进行“文化适应”,主要体现在学习并使用当地语言撰写教理教义书籍等,比如耶稣会士Alonso de Bárcena(1528-1598)在秘鲁时曾用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编写了教理问答及词典,还用这两种语言撰写了忏悔手册,而沙勿略在日本期间,也编译和修订了公教要理书。所以罗明坚在入驻内地后,也用中文写了《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但教内教外的反响都一般,范礼安认为这本书不太完美,令利玛窦重做,而在他们邀请王泮为《天主实录》作序时也遭到了拒绝,“他看了书后非常高兴,称该书非常好,而且尽是很出色的理论,但他却不想亲自作序,也不想让任何人去写,并说没必要请人作序,只要印发给世人即可”。而消除士大夫的这种犹疑和审慎的态度就要先从道德伦理方面寻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径,由此推断不仅罗明坚注意到《明心宝鉴》这部小书,利玛窦也开始对西方伦理学进行翻译,撰写了《交友论》一书,就此融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圈。从这部典籍中还可以找到爱比克泰德《道德手册》的影子,它虽然充满泛神论的论述,但却对朴素的理性和教育的作用十分推崇。后来天主教也是积极挖掘了《道德手册》中的“天命”和“命定论”概念,以寻求其与天主教教义的相通之处,而这本书在1497年被译为拉丁语后,亦被用作中世纪教会和修道院的训导指南,在教会内部影响很大。很巧的是,这本著作也是利玛窦《二十五言》的底本,《二十五言》为进一步弥合中西文化差异搭建了文本路径,而罗明坚的《明心宝鉴》翻译则是为欧洲读者更好理解天主教和中国文化之同提供参考,可以说,早期来华西人从中从西都在积极寻求文化间的沟通与融合。
最后,格言作为一种普遍的语言符号,记录了先贤哲人的所言所思,并因其句式凝练、易诵易记,成为不同文化的核心载体代代相传。西方格言作为一种书写形式,亦承载了基于普遍经验所获得的真知洞见,古希腊古罗马作家如柏拉图、西塞罗、塞内卡等作品中常有格言出现。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一种修辞手段,是“修辞式推论的去掉三段论形式以后剩下的结论或前提”,是一种普遍性的阐述。而天主教的格言传统还包括圣经中的格言警句,因具有从上到下的言谕性,使得民众可以迅速理解并服从其背后的神意,而且也用于隐修实践和学校教材,比如耿稗思的《尊主圣范》和伊拉斯谟的《箴言集》,基于这样的文化前视域,《明心宝鉴》的格言语录性质也更容易引起在华西人的注意。
魏京翔:高母羡在翻译《明心宝鉴》时,与西班牙驻菲多明我会“文化适应”性的传教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多明我会作为天主教最早建立的修会之一,对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像我们所熟知的托马斯·阿奎纳就是多明我会士。同样地,多明我会在西班牙也占据着重要的宗教地位,多明我会会祖圣道明就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和费利佩二世的告解神父都是由多明我会士充任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也极力资助这一修会前往美洲和亚洲传教。这种与王室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解释了为什么高母羡西译的《明心宝鉴》手稿能递交到国王手里。此外,具体到天主教传播的“文化适应”策略,也并非耶稣会所特有,学界对此也有很多相关研究。姑且不论各修会之间的差别,“文化适应”性的传教策略体现的是当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尤其是初期阶段,是有着跨文化传播底层逻辑的。秉持着“扎根”优先的原则,传教士们通过学习本土语言、研究经典文本、融入主流文化,从而获得立足空间,比如利玛窦“合儒”、“补儒”和“超儒”的三段论就是很好的例证。“文化适应”策略是完成其宗教合法性本土建构的基础。
我们以西班牙驻菲多明我会为例,尽管他们并非最早抵达马尼拉的修会(早于其的还有奥古斯丁会和方济各会),但马尼拉大主教萨拉萨尔神父所确立的语言学习与社区融入政策使得这一修会快速发展。高母羡之所以能够获得《明心宝鉴》的中文文本,并集合多位中国文人帮其润色,都源于他深入华人聚居地并积极掌握其语言和文化。除《明心宝鉴》外,高母羡还用中文撰写了一部《辩正教真传实录》,亦由华人刻工进行刊印出版。从书目学的角度来看,它属于菲律宾最早印刷的图书。从汉学研究的层面出发,这是欧洲人用中文撰写的第二本书,仅次于罗明坚的《天教实录》,而在利玛窦《天主实义》之前。此外,这本书还是早期欧亚科学交流最重要的书籍之一,高母羡利用这部著作介绍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这是欧洲人以中文写就的第一部关涉天文学、地理学及生物学的书籍,这一点与来华耶稣会士奉行的“科学传教”很相似。事实上,两者都是在寻求异文化间可以沟通甚至融合的地方。
闵明我曾经也寓居菲律宾并且掌握了本地方言他加禄语,入华后也快速掌握了汉语并撰写中文教理著作,但他并没有延续高母羡这一多明我会前辈的传教路线继续前进。这与他在“礼仪之争”中所持的立场有紧密关系。“礼仪之争”作为早期来华耶稣会的内部矛盾后来扩展到整个来华修会,并在彼时的欧洲宗教界、知识界产生了巨大讨论。闵明我曾就如何定义中国礼仪的性质与其他来华传教士展开辩论。在他看来,这些仪式具有明显的宗教及迷信属性。《论集》也是在他返回欧洲后为了申明其宗教立场而作的,他希望可以重新阐释并完善有关中华帝国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叙述并澄清那些“在欧洲,已成为神谕的论述”。
《明心宝鉴》早期西传过程中的“文化融合”与“文化疏离”
胡文婷:罗明坚的《明心宝鉴》译本中更多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化融合”倾向,文本中也常常出现用基督教的历史和文化来比附中文内容。首先,罗明坚则参考了欧洲的格言集对《明心宝鉴》中的叙事结构进行了改造,把源文格言开端处所引的书目、人名都删去,虽有几处的章节标题和内容之间他以quidam autor loquitur(某位作者言)代之,但也未直接进入具体的文本语境中,模糊了格言警句的具体来源。而且罗明坚这种隐去格言来源信息的处理似乎向西方读者传递出普遍真理的存在,另外,为了让读者区分不同条目,罗明坚在每条之间加以alius(另)作为标识。这种方式又给他留下了改造空间,在译本中他或是把源本中同出一处的条目放在一起,或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将相似意义的条目合在一起,或是缺乏背景知识而错误地对条目进行了合并,他有时还会将源本中的条目进行分割,甚至颠倒了条目的前后顺序。总的来说,罗明坚将《明心宝鉴》改造得更符合欧洲读者的阅读习惯,却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源本的叙事特征。
其次,在译本手稿中,当遇到中西概念存在相通处时,罗明坚则会尝试将神学概念嫁接到汉语词汇上,如对“天”的人格化,强调“善恶”中的自由意志,以及《继善篇》中徐神翁所言的“正道”本指道家中的大道,有清静无为、归复心性之意,常被道教用以修身养性之法,但罗明坚则将其译为“via recta”体现的是圣经中的正确之道,即信仰之道。当遇到与西方文化迥异的观念或词汇时,罗明坚则会对文本原意及原词汇进行重构,在“改头换面”后将其拉入西方文化语境中,如他在翻译“得一日过一日,得一时过一时”中罗明坚增译的“人们最终走向死亡,平静且喜乐(cum viri mors venerit, non turbatur)”,更多想要向西方读者传递的是他们所熟知的基督宗教的死亡观,还在“待客不可不丰”中,直接添加deus这一神学概念,将儒家的日常待客礼仪赋予了西方宗教式的神圣性。另外,有一些中国特有的文化关键词,如将“玉”译成“石头(lapis)”,将“果报”译成“惩罚(poena)”,通过淡化甚至消弭原词的文化或宗教色彩来打破文化间的壁垒,使得源文本信息得以顺畅传递,但同时彰显了其求同过程中的西方基督宗教中心立场。
魏京翔:同样地,高母羡的译本与罗明坚相似,也体现了为“文化融合”所做的努力和探索。高母羡常常跟着旅居马尼拉讲闽南语的福建人学习汉语,他对《明心宝鉴》中出现的书名、人名及书中部分难以意译的地方皆采取了音译方式,所注字音为闽南语音。对方言的掌握和运用是“文化适应”性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母羡的译本中,闽南语的介入增加了不少异域色彩。但不同于罗明坚,高母羡对《明心宝鉴》中所涉及的百余部中文书名、各种人名、术语和隐喻几乎未做任何注释,因为对他而言,能够及时向欧洲传递出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已足够。
学者刘莉美在研究高母羡的西文译本时,曾提到很多体现“文化适应”策略和高氏以自身“基督教化”的思想来诠释他者的强烈意图:他不仅把中文的“罪”、“过”、“恶”、“非”都翻译成基督教中的“原罪”(pecado)一词,并且常常将中国佛、道的概念也转换为天主教的概念。这当然是一种文化比附,但也可以看出高母羡的目的不在于区分两者的不同,而是想要求得其间的“共同”。
反观闵明我的西译本就大不一样,作为天主教神学“纯洁性”的捍卫者,他对《明心宝鉴》中出现的“异教”(例如佛教、道教等)性叙述十分警惕,就那些暗含着“异教”色彩的术语和概念,他一律省略不予翻译。闵明我把《明心宝鉴》定位为“劝善书”或者说世俗性的道德教化文本,通过剥离“异教”元素,来确保文本的“纯洁性”。他将中国儒家的道德箴言转化为超越文化背景的“普世伦理”,从而弱化其与中国宗教传统的关联。闵明我希望通过“文化疏离”来强调文化的异质性,贯穿其中的是他非常强烈的“异教敏感”,这种“敏感”源于他对利玛窦“文化适应”政策的反对,当然,这种透过宗教滤镜的刻意剥离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明心宝鉴》与中国知识观的变迁
胡文婷:“礼仪之争”作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不仅是宗教立场的冲突,也是中西文化核心概念早期的一次碰撞,同时也常被认为是中西知识体系互动模式的分水岭。以《明心宝鉴》这一个案为例,可以看到在它的早期西传过程中,是由从最早期的“求同”转变到后期的“求异”,而且这种“求异”的倾向到了19世纪之后开始演化为寻求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基本路径。
比如19世纪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贤文书》,共计收录了200条格言谚语,不乏《明心宝鉴》的条目。德庇时在序言中称“正如一个人的言谈是此人思想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的格谚可以用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国家人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格谚与民族的行为处事方式联系紧密”。这本册子的编纂是为了辅助汉语学习,从其行文排列中也可以看出,中文居页中,左侧为罗马字母拼音,右侧为逐字英译,顶部附整体译文,体现了语言学研究范式的介入,而且也如德庇时所称“这本书中包含的大多数格谚都很古老,它们的抽象真实性或虚假性对欧洲读者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只是将它们作为民族文学的样本”,这说明以《明心宝鉴》为代表的这类格谚集已经从早期的文化沟通媒介转向为研究文化比较和民族文学的范例。
另外,还有意大利汉学家罗声电(Lodovico Nocentini)的意大利语译本,这部译本连载于1907-1908年的《东方研究杂志》(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上,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与西方截然不同,其中最能展现出中国独特性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在他看来,《明心宝鉴》是为了指导人们保持或恢复上天赋予人类的纯洁情感,美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唯一的信念。基于伦理道德的普遍性和民族性,他对其进行了翻译和注释,在其实践过程中也呈现出西方专业汉学对传统经典文本的关注和阐释。
可以看到,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时空进行流动时,由于文明间交流的阶段不同,以及交流者和阐释者的文化立场和认知范式不同,从而呈现出文本的差异化理解,包括误解、借鉴、挪用和融通,这种多元化的诠释路径最后层累为系统的知识观体系。
另外,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无论是典籍外译,还是西学汉籍,译者早已突破了语言符号转换者的单纯角色,这与我们现在常说的“好的译者应该像一面镜子一样如实地反映原作品”的观点是很不同的,早期译者的主观性渗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通过删节、改写甚至是将源本进行了重构,之于他们,“镜子”的翻译隐喻更像是“棱镜”,可以折射出不同文化交织过程中的各种光芒,这种现象对于文化研究而言,是十分有价值的。
魏京翔:晚明来华的西人所面对的社会思潮主流基本还是宋明理学。利玛窦聪明地发现,无论是朱熹的“性即理”还是王阳明的“心即理”,“理”都是实际存在的“实体”(“理”是无形而存在的),作为万物的本质与来源,“理”先于万物又寄于万物之中。这一点与托马斯·阿奎那所倡导的温和的实在论颇为相似。于是,利玛窦将西方神学中的“共相”和“殊相”概念联结到理学中的“理”、“气”观念,认为中国人的“理”可以暗合西方神学中的“共相”。就此,利玛窦相信中国人的创世观与天主教的神创论具有同样的逻辑理路,都是从“同一本质”到“不同个体”的过程。他巧妙地模糊了“Deus”与“理”之间的界限,并以此作为适应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
通过对《明心宝鉴》的西译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母羡应该也会认同上述判断。但这种模糊性的处理是反对“文化适应”策略的人所不能接受的,即坚称“Deus”与“理”二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闵明我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其观点是如果二者的思想体系如此相同的话,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学习西方的宗教呢?这种理解的差异和立场的不同,决定了上述两派到底采取哪一种方式来对待文化间的交互,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中国知识观:即将中国文化作为可以融合的对象还是作为有距离感的异质存在。对西方人而言,这样的争论始终存在并延续到今天。但无论是哪种方式,似乎都带有“跨文化传播的悖论诅咒”:选择妥协,可能会引起身份合法性危机;选择坚守,可能会限制影响力的扩大。比如,西方在构建中国形象的过程中,经历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理想化的推崇,也出现过19世纪批判性的转向。欧洲中国知识观的变迁,其背后是“中国镜像”导致的认知偏差,因为“中国镜像”的主体是西方的知识生产者,他们将自身需求投诸其中。所以,我们在回顾西方的中国知识观时,不仅要把握知识观的系统性和变动性,还要深入挖掘背后的文化动因,以求超越以往的二元叙事,从而破除偏见,更为客观、平等地去关注处于文化间的文本及思想。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