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人文极盛,“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说广为流传。其中潘岳与陆机总被文学史放在一起,故有“潘陆”并称。二人文风异趣,评家称“潘江陆海”,不为无由。恰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言:“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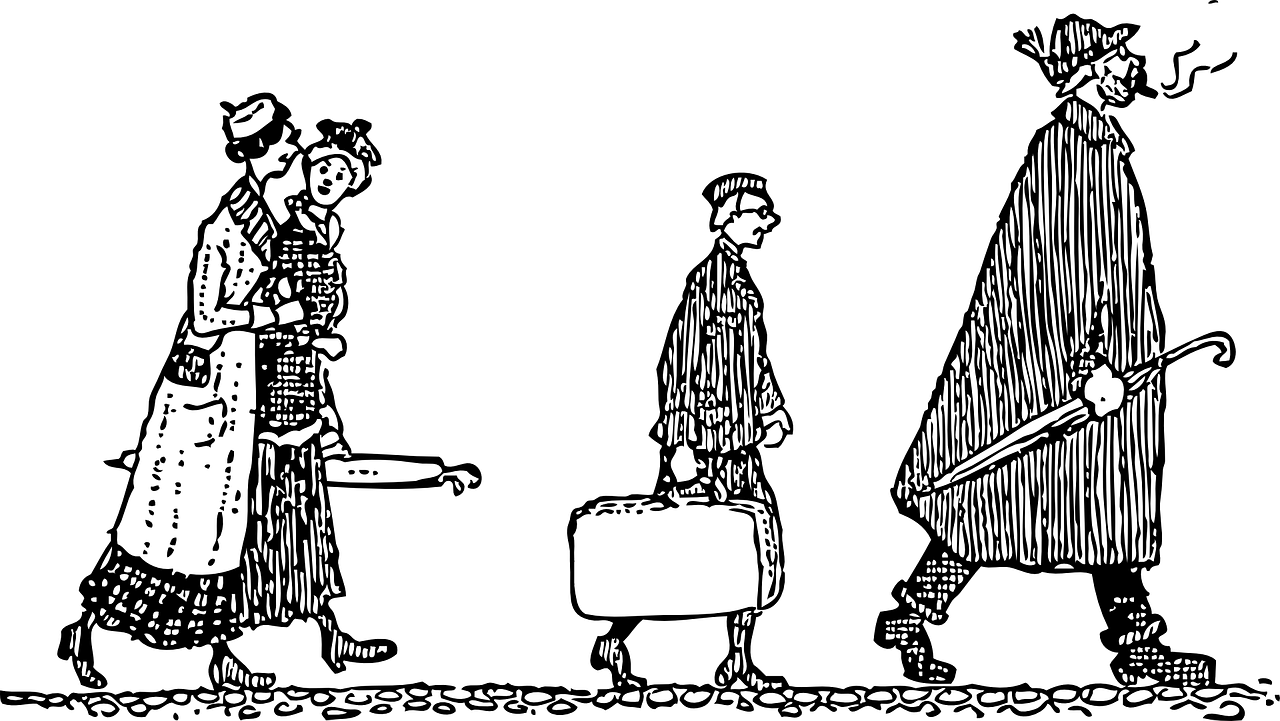
陆机曾为太子洗马,贾谧亦在“东宫积年”。正因此,潘岳代贾谧追忆过往“缱绻东朝”,与陆机“情同友僚”,赠诗的目的显然是为巩固关系。站在中朝的立场,孙吴政权不具合法性,故而潘岳直斥“南吴”乃“僭号称王”,平吴克胜,则“伪孙衔璧”。如此触目的字眼,作为陆逊之孙、陆抗之子的陆机,定然无法忽视,但又不得不承认眼前的既成事实。是以答诗刻意绕开“僭”“伪”之说,先将魏、晋嬗替归结为“天厌霸德”,“天命”既已转移到晋,所以“陈留(曹奂)归蕃,我皇(司马炎)登禅”,蜀汉与孙吴也随之来归,即“庸、岷稽颡,三江改献”是也。世人尽知,司马昭灭蜀在前、司马炎即位在后,也就是说,应是“庸岷稽颡”在前、“我皇登禅”在后。陆机有意错乱时间顺序,一定程度淡化了“三江改献”的屈辱。
潘岳代贾谧所作赠诗,将陆机比为来自“海隅”“南冈”的“长离”(灵鸟)“朱鸾”,分明还是在身份上作文章。此后,潘岳虽用大段笔墨称美陆机“播名上京”后的仕宦经历,但值得玩味的是,此番认可其实带有微妙的限定,即诗中“在南称甘,度北则橙”一语。这句古谚世所共知,原意是说南方的“橘”移植到北方会变成“枳”。站在陆机的角度,即使潘岳最终以“崇子锋颖,不颓不崩”这等赞语,释放了友善信号,但古老的谚语仿佛提醒他:北人对南人始终无法放下轻蔑之心。鉴于此,陆机答诗才会说:“惟汉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从地域、物产角度正面回击。他自视应为“万邦作咏”的“南金”,而非如对方所称“甘”“橙”之类“曾不踰境”的物什。陆机并未因由“南”入“北”而自掉身价,反倒在“度北”之后,“南金”的份量甚至会引发北方文坛的“三张减价”。(这组赠答诗,朱晓海先生已有相当精湛的论述,见氏撰《潘岳论》,载《燕京学报》新十五期,第156-157页。)
元康六年,潘岳出任著作郎,至八年(298年),因妻丧离职。也就在此年,陆机出补著作郎,宿命般地接替了潘岳的职位。这恰好与“安仁来,陆便起去”的逸闻相呼应,不同的是潘岳走、陆机便来。潘岳为亡妻作的《哀永逝文》应撰于此时;接任著作郎的陆机,得以进入秘阁,读到曹操《遗令》,于是写下《吊魏武帝文》。这一年的潘、陆,只是擦身而过,未曾正面对垒,却近乎同时写出关于“死亡”的动人篇章,可以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交锋”。
“死亡”是潘岳最擅长的文学主题。《文选》“赋”“诗”二类均有“哀伤”之目,潘岳的手笔赫然在列;此外,与“死亡”相关的《选》“文”之中,潘文居“哀”“诔”之最。就在充斥着“吊祭悲哀”(萧统《文选序》)的应用文类中,安仁的《哀永逝文》与士衡的《吊魏武帝文》一并获得昭明太子青眼。
潘、陆二文异趣,从哀、吊对象即可察知:《哀永逝文》写新丧之妻,《吊魏武帝文》则因早作尘土的曹操而作。伤至亲十分平常,吊古人稍显难得,是以陆机在序中特意假设有客发问:
临丧殡而后悲,睹陈根而绝哭。今乃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意者无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识情之可无乎?
通常而言,“丧殡”之时才会教人“悲”“哭”。感知死亡需要在场,书写死亡亦当如之。在《哀永逝文》中,作者几乎再现了从出殡到下葬的全过程,正因在场,情感才足够真切。曹操早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就已薨逝,处于“百年之际”“无情之地”的后人,本不应哀伤。陆机之所以“伤怀”,原因在于:即使像魏武帝这样有“回天倒日之力”“济世夷难之智”,“格乎上下”“光于四表”的大人物,最终也不过“藏于区区之木”“翳乎蕞尔之土”,难逃一死。
大人物不但会死,且死前的情状也不免难堪。陆机读到的魏武《遗令》,除却“经国之略”“隆家之训”,还有“爱子托人”“分香卖履”之类琐屑家务,而曹操希望将自己的衣裘“别为一藏”,死后竟遭瓜分。世人眼中的大人物,到头来竟这般“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眷恋尘世,无法忘情。
较之魏武帝,潘岳的妻子只是一个小人物,小到唯有通过潘氏留下的诗文,才能窥见其身影与芳名(《离合诗》)。在她身后,“悲”“号”“哀”“哭”不仅贯穿于丧葬过程中,也在潘岳的文学世界永恒回响。如果说陆机要探讨的是死亡之“理”,即人终有一死,大人物亦莫能外;那么潘岳要抒写的无疑是死亡之“情”,哪怕是小人物的死,也会令至亲长怀哀思。小人物有其“大”,大人物有其“小”,这或可成为“机、岳之文永异”,二者却又齐名的绝佳佐证。
文学之外,陆机、潘岳在史学上也有交手。当时朝廷欲修国史,就《晋书》该如何限断,即本朝的“历史起点”问题两次展开讨论。起初,荀勖、王瓉分别提出“正始”和“嘉平”两种起年方式;晋惠帝时,此一话题再引热议,贾谧又提出“泰始为断”之说(《晋书·贾谧传》)。唐修《晋书·潘岳传》直言不讳地说:“(贾)谧《晋书》断限,亦岳之辞也”,意即所谓“泰始”起年说为潘岳出谋划策。
其时,陆机也参与了《晋书》限断的讨论。王隐《晋书》即见此事,《初学记》也留存片言,其文曰:
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
另据干宝《晋纪》载:“贾谧请束皙为著作佐郎,难陆机《晋书》限断。”陆机对《晋书》限断的全部意见,现今已无法获知,不过既然贾谧派出当时的著名学者束皙与之辩难,便可知他与台前的束皙、幕后的潘岳看法相左。按照陆机所说,身为西晋“三祖”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尚未篡位,“实终为臣”,史家理应为其作“传”;而以后世追尊的角度论之,他们已然等同帝王,其传又可称“纪”。“纪”“传”名、实的两难,既凸显了“三祖”身份的暧昧,也折射出《晋书》限断的尴尬。正始元年(240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成为唯一的辅政大臣,随后改元“嘉平”,标志着司马氏已独揽大权。所以无论起年自“正始”还是“嘉平”,都好似预先将仍是臣子的帝王野心昭告天下;“泰始”起年,则从司马炎正式登基算起,才不至于扯下历史的遮羞布。潘岳与陆机,一个依附典午,一个出身“胜国”,天然的立场使二人根本殊途。
潘岳身为贾氏党羽,唐修《晋书》本传罗列其人数条“罪状”,最严重的一条指控当属:“构愍怀(司马遹)之文,岳之辞也。”元康九年(299年),贾后设计废除太子司马遹,先诈称惠帝身体抱恙,呼太子入朝,而后将其灌醉,诱使他抄写咒骂帝后的祷神文。这份构陷文书即由潘岳草拟,其辞云:“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晋书·愍怀太子传》)措辞不但与潘岳个人文风大相径庭,也殊非正常状态下司马遹可能的表达,荒唐错乱,倒是颇合醉酒的情态,足见代笔之妥帖。
永康元年(300年),贾氏一党被诛,潘岳、石崇等人也“白首同所归”(潘岳《金谷集作诗》)。此前惨遭贾后毒害的司马遹,得以恢复“太子”身份,获得“愍怀”的谥号。当时有两位作手,代表官方为太子撰写“诔颂”,其中一位便是陆机。在愍怀太子遭诬被害与死后复位的政治风云中,潘岳与陆机又一次宿命般地相衔:前者的手笔导致太子之“死”,太子之“死”竟又成为后者执笔的动因。陆机以诔文为愍怀洗冤,直斥贾后“如何晨牝,秽我朝听”,此时已随贾氏同入鬼录的潘岳,倘若地下有知,会否再次执笔与之争胜?毕竟举世皆知,安仁“巧于叙悲”(《文心雕龙·诔碑》),最擅哀、诔。
史称陆机有“豫诛贾谧”之功,不过几年光景,却在成都王司马颖麾下不幸枉死。《南史》记载谢灵运问谢晦“潘、陆与贾充优劣”,此番设问乍看古怪。如果说贾充代表着权力,潘与陆只是权力操控的两支笔,笔与笔之间才分辨孰优孰劣。不过“趋利”的安仁也好,“邀竞”的士衡也罢,二人屡次“交锋”的背后,总有一只权力的大手。
此前,吴国西陵守将步阐投降晋朝,陆机之父陆抗出兵讨伐,晋朝与陆氏对阵的将领为杨肇,亦即潘岳岳父。这场战役的胜败,对陆、杨、潘三族的未来影响深重。牵动陆机、潘岳命运的齿轮,或许在西陵交战之际就已开始转动。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