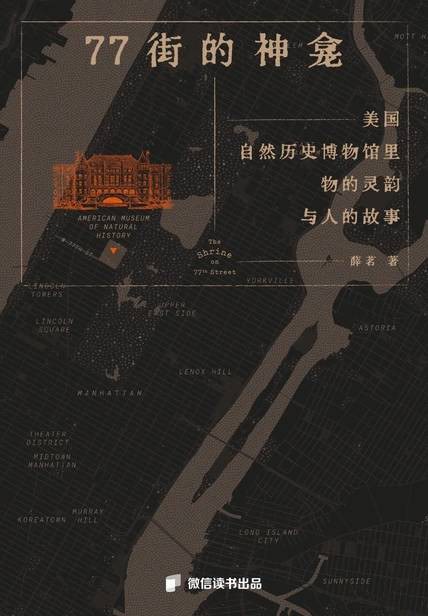
《77街的神龛: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物的灵韵与人的故事》,薛茗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出版,284页,88.00元
“77街的神龛”
三个月前,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研究员薛茗老师和我在上海建投书局分享了她的新书,《77街的神龛: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物的灵韵与人的故事》。活动主题取名:今天我们还需要人类学博物馆吗?
虽然书名笼罩在层层氤氲之中,但副标题已经道尽了其中的玄机。坐落于纽约上西区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缩写为AMNH),是由多座博物馆构成的博物馆群,它们不仅以世界首屈一指的天文、矿物、(古/现代)生物标本收藏和陈列著称,而且还庋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展品。其中的人类学博物馆,就是这座“77街的神龛”。
由于这些收藏不仅与博厄斯、米德等人类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呈现了一般意义的人类文化多样性,而且还在不同层面上联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使得这座博物馆,宛如祭祀自然之神的殿堂一样,成为人们不定期朝圣的神龛。
如何讲述这样一座博物馆的故事,绝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其中无数的收藏的确让人很难下笔,或开口。好在,薛茗仅用五件文物就完成了挑战。这五件文物其实也是全书五章的主题,分别是北亚通古斯语族尤卡吉尔人萨满的神衣、来自北京的《西游记》皮影、来自青海热贡的“冥想观音”唐卡、馆内工作人员临时搭建的墨西哥亡灵节祭坛和一条加拿大西北海岸海达族印第安人的独木舟。
回到当时的分享,为何要取这样一个名称,其实我是心存困惑的。人类学博物馆不是我和薛老师这样博物馆人类学从业者安身立命的基础吗?要是皮之不存,那毛又将焉附?不过,作为这本书的首批读者,翻看了这五件文物的故事,不说理清了“77街神龛”的历史,至少是解开了我自己的困惑。
五件藏品
那么,这五件文物究竟串联起怎样的历史,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们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下面是我按博物馆文物小说明写作方式,缩写的五件文物的简单信息。
一、尤卡吉尔萨满神衣。这件服装由俄国人类学家弗拉基米尔·约赫森于1900年为AMNH征集。当时AMNH聘用(未成名之前的)“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完成了北美西北海岸(即太平洋一侧)的远征考察,带回数千件文物,轰动一时。出于一个非常具有预见性的认识:“北美的原住民很有可能来自亚洲——西伯利亚的亚洲人通过某种方式穿越白令海峡,在新大陆定居、迁移、繁衍后代”,AMNH人类学部主任和博厄斯共同牵头,展开了一次对北亚地区的考察。他们聘用多位人类学家负责亚洲一侧的远征和文物征集。这件神衣是此次远征的成果之一。
二、北京《西游记》皮影。这件皮影由德国探险家伯特霍尔德·劳弗于1902年为AMNH征集。劳弗曾作为西伯利亚远征的一员,为AMNH北亚藏品的征集立下汗马功劳。他也因此打动了博厄斯,聘请他担任“收藏中国”计划的执行人。1901年,二十七岁的劳弗带着三千美元,从上海开始了他收藏未受西方影响的“前现代”中国计划。在之后的三年里,劳弗几乎单枪匹马征集了书画、碑拓、石雕,及草鞋、蛐蛐儿罐、麻将等民俗藏品共计“7500多个物件,近500卷书籍,以及500多只蜡桶录音(包括戏曲、皮影、民歌和小调)”,其中也包括了从一家北京皮影剧团打包来的“乐器、戏折子、剧本,以及500多件驴皮制成的皮影”。
三、青海热贡“冥想观音”唐卡。由作者本人2019年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征集而来。几年前薛茗以热贡唐卡女画师伦措的人生故事为核心拍摄的纪录片入选玛格丽特·米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影片的主要线索围绕伦措所画红唐《冥想观音》徐徐展开,作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女性画师,伦措一方面面临来自家庭和世俗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应对职业领域和市场挑剔的目光。正是薛茗的影片,让AMNH对这幅作品产生了兴趣,促使这幅唐卡成为了博物馆的新入藏品。
四、墨西哥亡灵节祭坛。这是每年11月初时,AMNH公共教育部门临时搭建的墨西哥亡灵节风格的“祭坛”。在墨西哥文化中,这件摆满亡者照片、十字架、蜡烛并装饰得五颜六色的装置原用于指引逝去的亲人重返人间,与在世亲友团聚。只不过,作为公众教育项目,博物馆“祭坛上摆放的不是人的肖像,而是过去一年里从世界上灭绝的动植物的照片”。
五、西北海岸海达族印第安人独木舟。该船由AMNH于1881年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负责原住民事务的总长手中购入,两年后运抵纽约入藏博物馆。由于它身长十九米,身重超过一吨,堪称“镇馆之宝”,使它在自然史博物馆中经常因为展厅内部装修而改变位置。它在博厄斯时代曾被高悬于西北海岸馆的天花板下,船头向北(之前则朝南)。随着博厄斯在二十世纪初的离去,独木舟在之后的整个世纪中都被置于地面,并加上数个人偶。到2007年,随着原住民的声音被博物馆采纳,船上人偶终于被清除,并再次凌空面南,成为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草莽年代的雄心壮志
看完这五件文物的小说明,线索已经非常清晰了。而且,抛开文物本身的年代,它们入藏的时间节点也很说明问题。可见,作者选择这样五件文物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通过比对这些入选文物的排序,它们正好代表了人类学博物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首先,人类学博物馆起源于博厄斯的时代,那时的人类学家有着收藏全世界的雄心壮志。1893年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周年的芝加哥博览会上,博厄斯就开始了布置人类学展厅的试验。早在他入主纽约自然史博物馆前,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是他的上一位雇主。这份工作简历,不但为他积攒了日后成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资历,也让他建立了更科学地呈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愿景。
在那个科学大发现的年代,博物馆的行事风格充满了草莽的豪迈气息。馆方掏钱,给策展人提供经费和宽泛的指南,策展人拿钱去目的地,按着自己的脾性随缘购入文物,相当于博物馆的买手。博厄斯自己兼了北美地区的策展人和买手,约赫森、劳弗则负责亚洲文物的征集。在他的计划中,还有整个亚洲、南美有待收藏。
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距离。尤卡吉尔是个百多人的小部落,是人类学家眼中的典型研究对象,一个车皮或许真的可能就把他们全部的物质文化都打包带走了。但“收藏中国”计划则是个与之相反的个案。上世纪之初的一次征集,七千五百多个物件,初看是一次丰收的凯旋,而对应到泱泱大国,却只能算个切片。随着博厄斯本人因人事争纷离开博物馆界,进入学界,收藏世界的计划就此中止。如此规模的远征,空前而无后,远方的国度从此封藏入了静止的时间胶囊。
话说回来,时过境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换个人去替代博厄斯、替代劳弗,也没人可以保证就能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靠着这种看似草率的方式,支撑起了相当一批现代博物馆的草创阶段。可草莽的时代自有草莽的好处,凭着劳弗的一双脚、一双手、一双眼,饶是博厄斯有诸多不满,沟通不畅快,也把藏品跨海越洋给带回了纽约。从草莽到草创,一种把世界收入囊中的雄心壮志,支撑起了博厄斯们的收藏野心,成就了AMNH人类学博物馆不可或缺的亚洲收藏。

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观看展览的参观者
独此一件
博厄斯时代的基业草创代表了人类学博物馆的过去。一百年过去了,今日的博物馆遭遇了怎样的挑战?薛茗以一种自我民族志的方式给出了解答。所以这次出现的,不再是七千五百多件藏品的其中之一,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独一无二。
薛茗在热贡的田野考察历时十年,最初也不是出于征集藏品的目的。她在当地走访、投师过许多唐卡画师,最后选择了女画家伦措的作品,并非出于偶然。之所以说她走遍热贡,有一件小事可以佐证。七八年前,我也曾到黄南拍摄唐卡绘画工艺,合作方是当地的一位男画师。虽然与他加了微信,但几年后近乎失联,我对他的个人信息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因为此次现场分享,我特意翻出了画师的微信——幸好他一直选择用自己穿着民族服装的照片作为头像——向薛茗证明我也到过热贡。她一看对方微信头像,就立即反应过来,说这位画师并非当地人,而是土族地区入赘过来的师傅,帮我唤起了头脑中的一点记忆。通过这件小事,她完美通过了我的“测试”,无愧一位称职的田野调查者。
话说回来,这位女画师正因为遇到了田野中的薛茗,让自己的人生故事成为博物馆藏品的一部分,有机会被博物馆里的观众、被读者看到。她早些年学画,打工,又抵住压力成立画室,并招收弟子,让女性学画者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种种经历也因此融入了唐卡。现在这幅画作,不同于北京皮影(不知制作者、表演者的名字,只是单纯的一件文化遗存,一件物件),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作为博物馆的参观者,肯定有人会问,这是不是哪位大师的作品?有没有经过哪些著名藏家的赏鉴?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令其在无数作品中被自然史博物馆收为藏品?也许回答都是否定的。然而答案又是肯定的。的确是博物馆人类学家或策展人利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特权,决定了这件作品的命运。但不能否定的是,每一件藏品又何尝不是源于某种特殊的因缘而成为选中之作的呢?那些钤满赏鉴印记的“名作”如此,名不见经传的人类学藏品亦然。
当然,从另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讲。这种状况其实还源于一个更实际的现状。当今的博物馆里,像几十年以前,一口气购入一整批文物,成百上千件同时入藏的情况早已非常罕见——之所以谓之罕见而非绝迹,是因为在某些急欲扩充藏品库的新建博物馆,还是有可能这般操作的。大多数博物馆的“历史”收藏都已成型,留给开源的空间已然不多。
所以,如此这般按个位数增补藏品的微调小改的方式,俨然就是(人类学)博物馆步履蹒跚的当下。
未来我们还需要人类学博物馆吗?
最后,看过了人类学博物馆过去和现在,不说走入黄昏,也难再现激情澎湃。难怪会让人引出“今天我们还需要人类学博物馆吗?”的话题,当然人类学本身也是以热衷反思出名,质疑自身的存续也算不上什么。
话虽如此,薛茗也没想让我们失去希望,所以这五件藏品中的最后两件,墨西哥祭坛和印第安人长舟,也就承载了人类学博物馆的未来,或者说一种可能的未来的形态。建在博物馆里的祭坛,用来纪念“过去一年里从世界上灭绝的动植物”,算是对纽约自然史博物馆创办宗旨的致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洲文化与北美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将被进一步加强。相信得风气之先、引领潮流的人类学博物馆,应该会在这一趋势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诚如詹姆斯·克利夫德在《路径: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翻译》一书中,对加拿大卑诗省海达族博物馆所作的观察那样,“被非法夺取的原住民物品,没有直接还给原来拥有它们的各个家族,反而是还给博物馆,而且最终是两个强制设立的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藏品的归属权始终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另一些同样与博尔斯有着密切关联的西北海岸藏品,则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比如,纽约自然史博物馆倾听到了原住民的声音,允许“原住民代表再次对着独木舟吟诵、歌唱”,并按照原住民的意愿调整了独木舟的摆放朝向。对我们来说,这会不会是一种对待人类学藏品更开放的态度呢。
在过去的许多世代中,人类学家或许是少数有机会深入异文化的探险先驱。而今,每当有一个人类学家抵达海地,早有上万海地移民来到美国俄亥俄的斯普林菲尔德市,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对当地人/移民皆然)都有机会获得人类学家一般的体验。比起人类学家的体验(那些在展柜外面观察“前现代”展品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更值得分享的是人类学家遭遇异文化时,乐见其与时俱进的宽容心和处理多元文化的丰富经验。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打开博物馆展柜里的时间胶囊,那个属于过去的人类学博物馆终将随风飘散。在历史的尘埃中,一个面向未来的无墙的人类学博物馆正在重建。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