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广乐钧天世莫知,伶伦吹竹自成痴。
郢中白雪无人和,域外蓝鲸有梦思。
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
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
这首《鹧鸪天》的作者是一代古典文学大家叶嘉莹,当年她偶然阅读了《鲸背月色》一书,书里讲的是在很早以前大海还没有被污染的年代,此岸的鲸鱼说话彼岸的鲸鱼也能够听懂,万物皆有灵,她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词。今日下午二时,叶嘉莹辞世,享年100岁,南开大学公布了这一消息。
生平:只有诗歌是主动做出的选择
叶嘉莹于1924年7月2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号迦陵。儿时的叶嘉莹是在北京察院胡同里的一座四合院长大的,四合院是其曾祖父叶联魁所购置,叶嘉莹在这里跟着伯父叶廷乂完成了自己的诗词启蒙。1941年,叶嘉莹入读北京辅仁大学,在这里她遇见了对她至关重要的恩师顾随,在顾随开设的唐宋诗课上,她认真记下了十几本笔记,后来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这段时间也是叶嘉莹创作力很旺盛的一段时期。
1948年3月,叶嘉莹来到南京,和赵钟荪结婚。同年11月,二人去往中国台湾地区。叶嘉莹曾说过,去台湾地区不是她的主动选择,她的先生也不是她的主动选择,去加拿大还不是她的主动选择。只有诗歌,是她一生中主动做出的选择,于她,诗歌是信仰,是乱世中的别有洞天。在台湾地区生活的日子,除了沉重的教书负担以外,叶嘉莹还要面对丈夫出狱后的性情大变。艰难时局下,她也想过自尽,是诗歌救了她。多年后,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叶嘉莹曾说,如果没有诗歌,人就会在苦难中被磨碎了。1969年,叶嘉莹携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又遭遇了长女和女婿车祸去世的事故。1978年她申请回中国教书,次年来到南开大学开始了回到中国以后的第一节课。在南开大学期间,她创办了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于2015年定居南开园。其作品包括有《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等数十种。
她是一个特别“真”的人,纯真、认真也较真
“还是很难过的,”《掬水月在手》的制片人李玉华这样和界面文化说道。她今日下午知道叶嘉莹离世的消息,是从纪录片出品人廖美立那里获悉。她说,目前她和纪录片导演陈传兴以及廖美立正计划去天津送叶嘉莹最后一程。
在83岁为《迦陵讲演集》一书所作序言中,叶嘉莹说自己生平很喜欢引用的两句话是——“以无生之觉悟做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境过乐观之生活。”她说朋友们或许觉得这只是老生常谈,但这就是她生命的真实叙述。“我是在极端痛苦中曾经亲自把自己的感情杀死过的人,我现在的余生之精神情感之所系,就只剩下了诗词讲授之传承的一个支撑点。”
正如叶嘉莹所说,这个支撑点成为了2020年10月上映的《掬水月在手》能说服她接受拍摄的原因。据李玉华回忆,起初叶嘉莹觉得自己不需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后来拍摄团队跟她说,这部电影不仅仅是记录其个人的一生,也是记录了古典诗词的传承,而这恰恰是叶嘉莹最珍视的东西。片子拍摄的时间拉得很久,从2017年4月10日开拍,到2018年7月基本完成,再到后期制作又花了两年时间,拍摄素材超过250小时,采访逐字稿有98万字。
在这期间,李玉华和叶嘉莹有着密切的往来,“她是个非常坚韧的人,我现在很庆幸有拍下她,当时她身体也比较好,拍完没多久她的身体状况就开始下滑。”李玉华说,叶嘉莹是个特别“真”的人,纯真、认真也较真。拍摄过程中,有一次叶嘉莹来到北京在酒店里和陈传兴促膝长谈,坐在床边她讲开心了还会荡起双脚,像小朋友踢水,很有少女感。
“她生活简朴,不挑食也不忌口,但日子过得简朴且简单。同时对时间有种紧迫感,她有一次跟我说‘玉华,我忙得不得了,稿子写不完’。”李玉华说,叶嘉莹九十多岁还在不断别的知识,她回电子邮件也很即时。而在更早之前,她还会大量回复读者来信,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她说这些读者能对古典诗词有兴趣就难能可贵。”
纪录片拍摄完第一次放给叶嘉莹看的时候,叶嘉莹有一些不同意见,而且比较坚持。李玉华就“斗胆”跟她说,“您也是创作者,如果有人抓着您的手教您怎么写诗,您会愿意吗?”叶嘉莹闻言道,“也是,那就这样吧。”李玉华说,叶嘉莹生活里是完全没有架子的,她有她专业和霸气的一面,但也有待人平等的一面。

应该感激她留给我们的遗产
诗人廖伟棠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说叶嘉莹百岁嵩寿辞世,自己不至于很伤心,“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并感激她留给我们的遗产”。而谈及叶嘉莹对他这位新诗诗人的意义,廖伟棠提及三点:“首先,叶先生从现代文学的概念出发肯定了词人吴文英的词的先锋意识,这可以视为叶先生的观念开放且前卫;第二,用近乎新批评的方式细读《秋兴八首》,对我们新诗人学习杜甫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台阶;第三,通过她的传承和推介,我们重新认识了顾随先生,我得以‘旁听’这位民国最伟大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师。”
尽管并没有在现实生活里和叶嘉莹有过直接接触,只是远远眺望,但廖伟棠认为叶嘉莹对自己来说依然有着独特性,“是在于她的治学方法是介乎我推崇的两者:西方现代汉学家的想象力与民国早年名士风范的斩截之间的。在年轻时代的我眼中,这毕竟是民国风范的遗存者,所以不免景仰。”他还提及,叶嘉莹和另一位不久前过世的诗人痖弦分别代表了古诗和五四新诗的两个最后堡垒的消逝,“对于我们后辈,如失恃失怙一样。”
《掬水月在手》上映时,陈传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现代人可能已经静不下心来读一首诗。但不管怎么样,就像叶嘉莹词中所言的“遗音沧海”,“总有一天,说不定又有另外新的一代人,他们有新一代的可能性,新一代的诗词从他们当中长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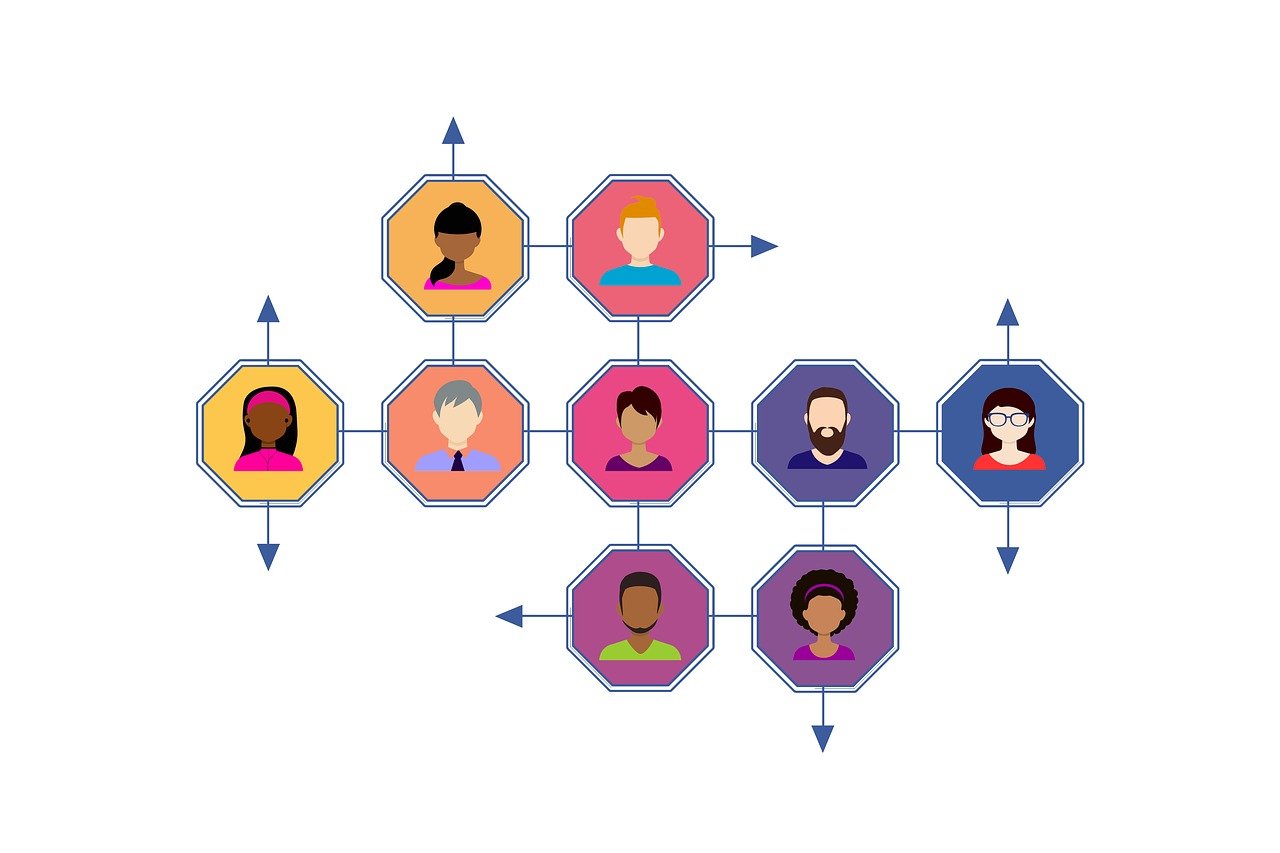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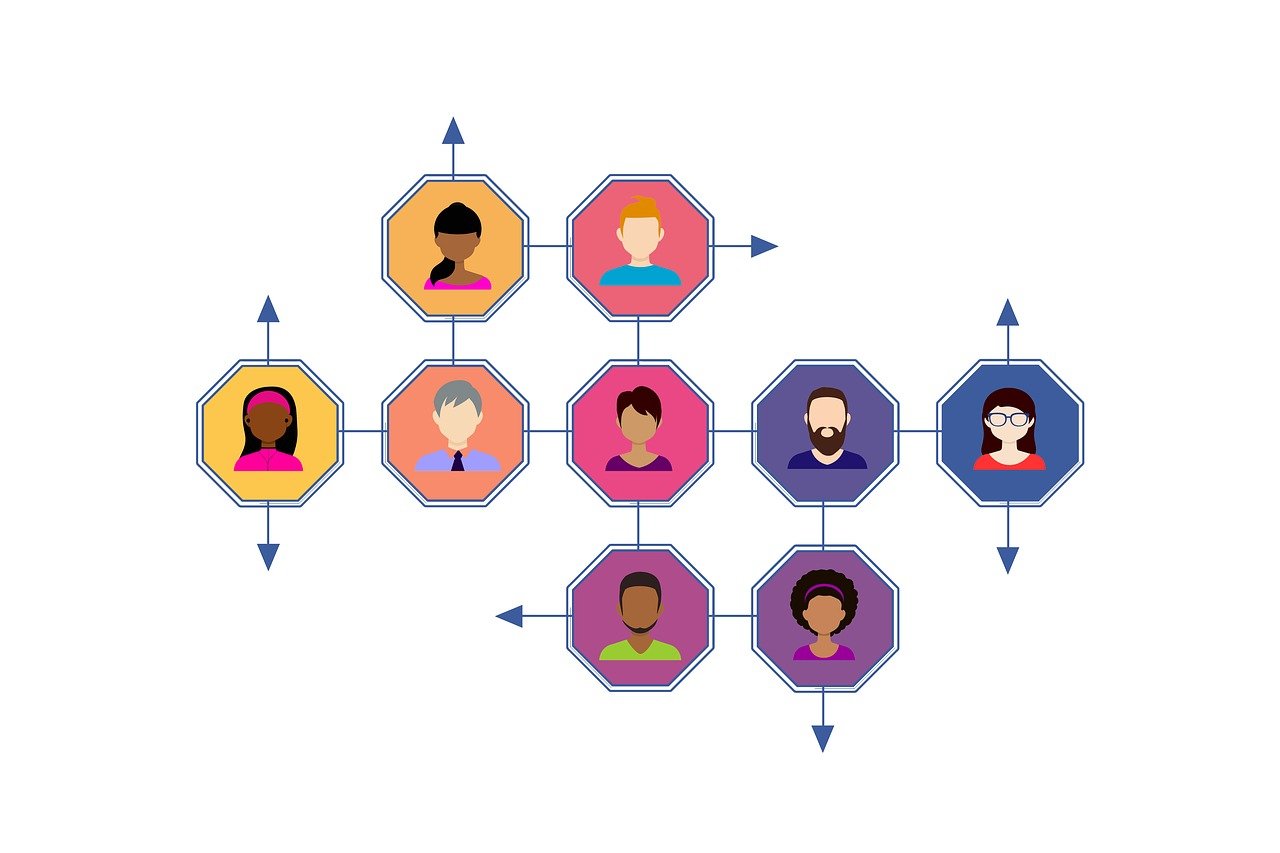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