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可以传世的大学史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必要条件:第一要有大的历史观,第二要有自己独有的述史脉络,第三要有丰富的细节,第四要有鲜明的写作风格。在这个意义上,鲁道夫的《美国学院和大学史》在该领域可谓当之无愧的名著。本书成书于1962年,于1986年绝版后,修订于1990年再版。在此之前六年,他刚刚出版一本院校史名著《马克·霍普金斯和小木屋》,探讨威廉姆斯学院的理念。写成本书之后,鲁道夫还曾于1977年出版了《课程:1636年以来美国本科课程研究的历史》,系统考察了美国本科教育内容300余年的历史变化。显然,在著者心目中,一部学院和大学史既有别于专门的院校史,也有别于其他细分领域的史著,是有其特定叙述内容的。鲁道夫首先定位于一部从学院和大学的角度写作的美国史,而不仅仅是一部美国高等教育史(王晨《译者序》)。全书重点放在美国二十世纪中期前的学院和大学生活和时代肖像,取材多自院校原始记录,叙述多于议论,对于大学核心的业务部分,如专业、课程和教学等,不做过多铺陈,只作扼要的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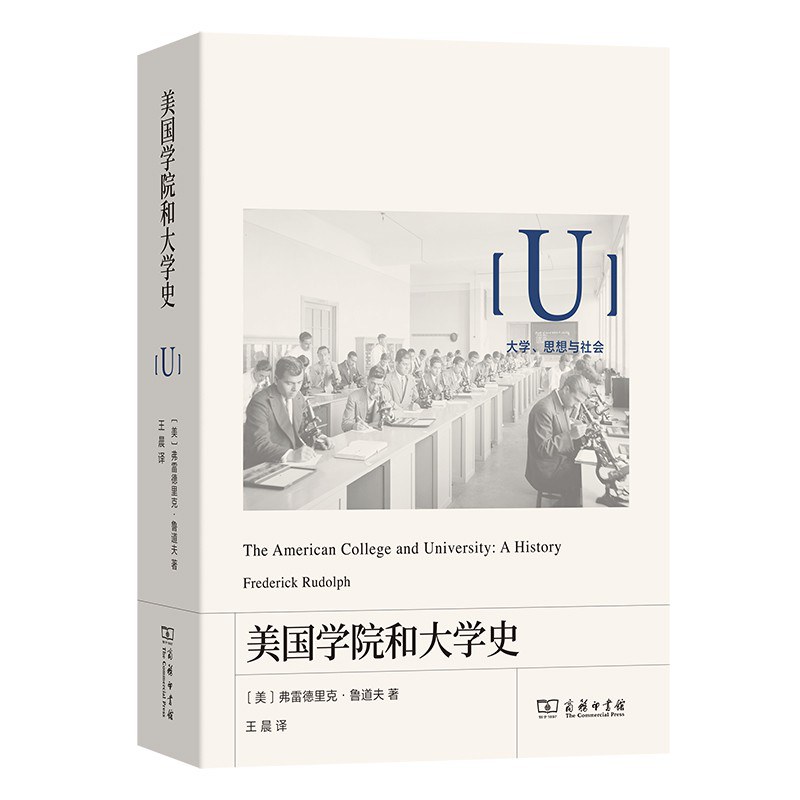
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美国学院和大学史》是高等教育术语的词源仓库,大学组织的家族图谱,美国精神生活的流域地图。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书里夹杂的历史和掌故之多,足以从政治制度、社会思潮、工业化进程、组织文化等多个角度提供不同的文本阅读体验。从美国社会的角度看待《美国学院和大学史》的话,会很自然地发现鲁道夫勾勒出了一个详细的当时大学的社会运行体系,时而体现在大学财政问题之中有关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的阐述,时而体现在有关校方和学生对学院生活不同定义的描写,也体现在美式足球运动发展过程中有关大学公共关系和校友网络的议论。对于本书,时人称为历史学家重回学院和大学史研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鲁道夫将女子教育和大学体育赛事专辟一章,与我们熟知的其他大学“正史”同列了。正是这些隐藏在历史角落里的点点滴滴,形成了鲁道夫本人对于其在前言中提出的本书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美国学院和大学如何和为何成其所是以及带来了何种结果”,鲁道夫的回答极简地体现在他在本书最后一章对芝加哥大学校训的引用之中:“推动知识增长,充实人类生活”,他进一步将此命名为美国共识。
从本书覆盖的时间跨度来说,鲁道夫将叙史的终点标定在20世纪中期,也就是美国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形成统一自我之前的三个世纪,这也可以看作在北美荒野诞生的学院和大学从蹒跚学步进入青春期的这段历程。在本书成书之时,美国刚刚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黄金十年,州际公路的建设和汽车的普及将美国在地理空间上连为一体,郊区的繁盛塑造了稳定的社会空间,婴儿潮和电视的普及开始伴随着商业文化呼啸而至,业已形成的庞大中产阶级正在构筑他们新的社会身份。当其时也,美国社会六十年代巨大的青春期伤痛还没有到来,美国社会还处于快速的扩张和发展时期,美国学院和大学还没有明确清晰的身份界定,仍在懵懂地探索所有潜在的不确定性。在鲁道夫笔下,这一时代充满了精英或平等、生存或发展、继承或创新、进步或倒退反复缠斗的无数注释。正如这部学院和大学史所揭示的,从广袤荒凉的北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美国大学,并不一直伴有“山巅之城”的远大理想和历史宿命,并不一直在重要的关键时刻做对了选择题。恰恰相反,在三个多世纪里,大学与宗教(第四章《宗教生活》)、大学与政府(第十章《杰克逊式民主和学院》)、大学与科学界(第十一章《19世纪50年代的危机》)、大学与社会(第十二章《新时代的黎明》)的关系一直在不断调整,不断试误,不断选择。他揭示了美国社会独特的实用主义土壤造就了重视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和渐进改革的传统,组织多样性为试误充当了减压阀,也为从头再来提供了容错空间,最终成就美国大学今日的形态。

鲁道夫
从本书试图表达的内容来说,鲁道夫的专著可以看作是一部致敬美国开拓精神的学院和大学史。本书中随处可见对于拓荒和实验充满自豪的溢美之词,如“19世纪学院的建立与运河开凿、棉花种植、农业开发和黄金开采一样,笼罩在同一种时代精神之中。这些活动,没有一项遵循完全合理的程序。所有人都被美国人对明天的信念所感动,毋庸置疑,这种信念是美国人打造更美好世界的一种能力。在学院建立的过程中,理性是无法与永远进步的浪漫主义信念相抗衡的”(第72页)。“美国学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些以自己的方式白手起家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发现了一个新目的。”(第90页)“它们(大学)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它们能否满足一个对过去几乎毫无兴趣的民族的需要,它们对今日的兴趣也只限于它们能给明日带来何种益处。”(第139-140页)正是这种未确定性使早期美国学院和大学处于一种不断追求发展和完善的冲动之中,从而也成就了一段充满无限可能的学院和大学史,在鲁道夫眼中,开拓精神和多样性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鲁道夫在写作本书前阅读了大量院校的原始史料,深知在北美大地上植根于地方自治,由不同教派和政治力量建立的美国学院和大学其来有自,路径和归宿不一。既然初创时期美国学院和大学教育是以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为目的出发,鲁道夫准确地把握了多样性作为美国学院和学院初创时期的特点。“在这里,牛津大学毕业生的社会优势和社会义务被简化为北卡罗来纳的农村生活和郡县政府的要求。在这个不同的世界里,盛行的是相同的伟大传统。”(第86页)他写道,“一所学院能增长知识,与物质和野蛮做斗争。一所学院是对州的支持;它是忠诚的指导者、公民的指导者、良知和信仰的指导者。一所学院有其实用价值:它帮助人们学习他们必须要知晓的事物,以便管理世界的俗务;它也培养大批教师。学院就是这样的。所有这些都是学院的目的”(第33-34页)。无论是创立一所国立大学的失败,1819年达特茅斯学院案终裁确立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分立,还是1828年耶鲁报告对自由教育的辩护,或者是1862年莫雷尔赠地法案对校地关系的调整,鲁道夫表明,通过多样性解决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有赖于创造一个保护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制度环境、一个大学与社会密切接触但保持适当距离的社会环境和一个具有生动活泼的大学文化的组织环境。
从本书的内容旨趣来说,著者完成了一部作为美国公共精神生活史的学院和大学史。鲁道夫在书名中坚持将学院与大学并列,甚至在本书前十章中近乎一半直接以学院为名,足见他对于学院的重视和偏爱。他充满感情地写道,“学院方式为美国大学的许多非智力目的奠定了哲学和历史基础。……学院方式会形成这样的一种观念,即一所学院可以是一所感化院,一所道德苏生的学校。它的寄宿制倾向是美国大学未能形成学生跨校流动和转学传统的原因。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一所美国高等教育院校都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学习的机构”(第136-137页)。鲁道夫心心念念的“学院方式”至少包含两层涵义。一方面,与其后发展的专业研究生院组织相比,学院教育体现了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独特的奠基功能:思想广度、精神旨趣、优美人格、健全体魄、社群精神等等。在另一方面,以住宿制为组织形式的学院生活不仅继承了英格兰学院传统,也为北美先民在教会之外开辟了新的世俗的公共社会空间和精神生活的实验室:“学院方式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课程、图书馆、教师和学生不足以构成一所学院,它坚持用住宿制度总括上述事物。”(第114页)显然,学院生活已然成为了美国大学少有的不可撼动的基石和信条之一,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表述:“精神生命几乎像传染病一样会在接触之中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教育从长远来说是一件在每个学生和他的机构之间展开的事情。我们过多谈论的方法,只起了次要的作用。给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自己利用机会,不管是好是坏,他们会设计出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人际接触。”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所指出的,今日的大学教育已经远远扩大到了正常的课程教学以外,“课外活动,不仅被看成是娱乐的场所,而且被看成是本科生学习相互合作、学习为同伴谋福利的理想的组织形式”(德里克·博克著,乔佳义编译,《美国高等教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0页)。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主席博耶去世后,该基金会下属的博耶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委员会在题为《改造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报告中曾指出,“本报告所体现的理念将把流行的学生作为接受者的文化转变为一种学生作为探索者的文化,一种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共同进行探索之旅的文化”,也暗合鲁道夫史家之笔中隐而未发之意,可谓德不孤,必有邻。
鲁道夫的著史风格也颇有其个人特点。在威廉·玛丽学院约翰·塞林(John R. Thelin)教授1990年的导言中曾提到在本书出版后,学术界有批评鲁道夫的研究忽略人口结构和统计数据分析的,对其逸事化的写作风格也毁誉不一。尽管已经发生的历史具有唯一性,但是对历史的解释和推理却具有多样性。卡尔·波普尔曾言,“不同的历史学家总能概括出各不相同的、甚至互相抵牾的历史规律,很难说清孰对孰错、孰优孰劣”。与坊间大多数侧重宏大叙事,勾勒波澜壮阔的高等教育发展轨迹,专注揭示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动力的同类著作不同,在这部横跨三个世纪的美国学院和大学史中,他更多走进史料深处,将个人记录、演说、新闻报道、书信、传说等多种体裁融为一体,描摹那些历史转折时刻的细节,这些细节或许只是稍纵即逝的偶然事件,很多时候伴随着失败的经验,甚至并不总是光明体面,然而正是通过这些不同题材的浩繁史料以及细节书写,同时也因为逸事、演说和日记能提供更加朴素的历史真实,较之条分缕析的简单演绎能承载更加丰富的意义,鲁道夫带领读者一起经历了他对本书核心问题的归纳、猜想与反驳。以此来看,他弃“致广大”而不取,反其道选择“尽精微”的叙述方式或许就不那么奇怪。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我们重读鲁道夫的美国学院和大学史,自然不仅仅为了获取有关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史实,相反,我们需要通过这些逝去年代的路标和墓碑为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时代找到方向和归属。鲁道夫写作美国学院和大学史之时,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仍能代表着美国教育质量的最高水平,70%的学生就读于这类学校,这一比例在21世纪初已经下降到5%以下。即使在今天,当我们翻开鲁道夫这部专著时,仍能发现那些曾经徘徊不去的困境时时返回,在每一所大学的灵魂深处游弋。为何大学,何以大学,以何成其大学之类的问题,事关人类发明的这一重要社会组织的未来命运。1997年,《纽约人》(The New Yorker)刊载了詹姆斯·特劳勃(James Traub)的一篇题为《新型大学》的文章,对被称为是“新型大学中的第一个”的菲尼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hoenix)进行了介绍。该大学拥有高等教育的业务核心部分如教师、学生、教室、考试以及学位计划,然而却没有校园生活和学术生活,它是学生可以不与其他学生交往甚至不与教授见面而能够得到学位的少数几所大学之一,也被称为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式连锁店。2009年4月27日,《纽约时报》在其社论版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泰勒的文章,题为“我们所熟悉的大学走向末路”(End the University as We Know It)。即使是高等教育学者阿瑟·莱文也发出悲观的感叹,预言从现在起到往后的几代人时间里,“我们仍将拥有一些寄宿制学院和一些研究性大学,但其他的大学中有许多将销声匿迹”。大学作为以知识为工作材料生长起来的古老机构,在一个知识众筹削平了旧的智力世界等级秩序的时代,在一个高等教育被视为消费行业而被期待服务于各种外部需求的时代,大学必须重新审视其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重读鲁道夫的美国学院和大学史,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塑造多元的美国社会形态,建立稳定的智力生活和公共空间的过程中所做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路标还是失败的墓志铭,都依然有着耐人寻味的价值。
没有有意义的共同生活的社会是无趣的,没有新的可能性出现的时代是无望的,这或许是我们需要重新发现鲁道夫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没有鲁道夫的学院和大学史也是不完整的,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结尾时写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还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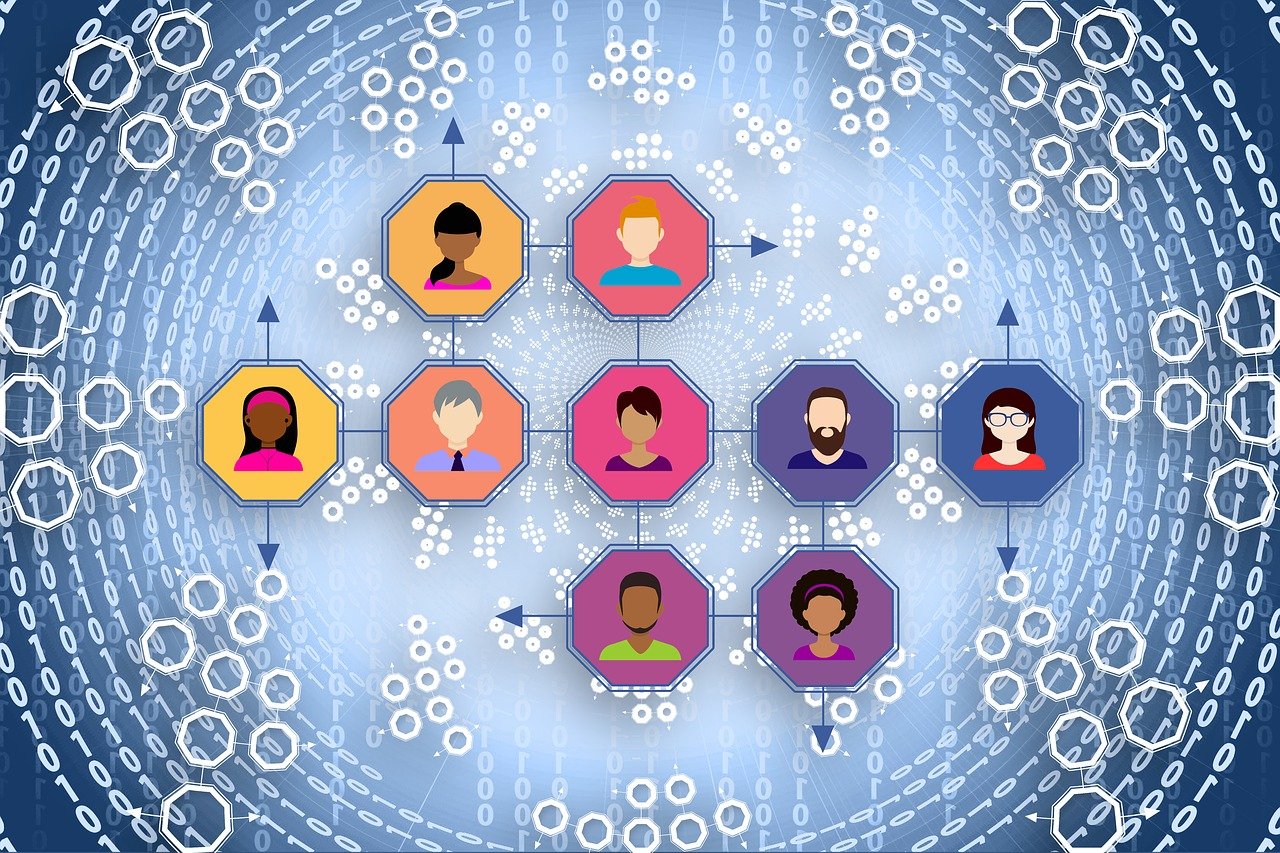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