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怕对那些在职场中成功追逐激情的人,这项研究也不那么让人感觉舒适。在这本书的序言、后记等部分,作者契克多次十分坦诚地谈论起自己的学术生涯。毫无疑问,她本人就曾是一名忠实的激情追求者,甚至是激情原则受益者。因为在本科阶段选修了社会学课程,受到当时任课教师的鼓励,契克果断选择从相对收入较高的工科领域,“跳”进了社会学的“深坑”。就这样,在顺利地完成学术训练后,契克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社会学家。恰恰是《激情的陷阱》这项研究使她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或许就占据了相当多的特权,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与之类似的幸运,甚至许多人根本就不具备追寻激情的同等机遇和条件。
但问题在于,这个时代的人们,好像习惯了将职场成功论证为个人奋斗的“爽文”,与这种“走向成功”的叙事互为表里的另一面,则是将个人在职场中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个人的无能或无作为。这确实是一种特别有美国特色且十分“有毒”的职场文化。于是这种关于职业、职场的叙事方式所折射出来的认知偏颇无疑值得警醒。《激情的陷阱》告诉我们,在职场中追寻激情而碰壁,未必是自身能力不及的反映,反而可能是不公平的社会结构施加在个体身上的结果。同样,在职场中顺利地寻找到满足激情的职业,固然一定有个人奋斗的因素,但或许个体身上拥有或具备的各种或隐或现的特权,才是在漫漫职场长路上比个人激情、努力更为关键的因素。
《激情的陷阱》尝试将求职一事放置在更为确定的社会结构和话语中进行全面审视,而一旦从更为宏观的尺度,去观察求职和打工的我们自己,至少能将工作/劳动这件事从彻底的个人主义话语中“拯救”出来——不是从个体单打独斗的角度去解释这个“吃人”的职场,而是从不愉快的职业境况中,发现属于更大群体范围的集体困境。也只有将分析问题的视角从个人转变为集体,才能从中认真检讨当代美国职场中存在的结构性缺失,从而有可能重塑或探及这个时代解决劳动力困境的集体行动方案。
就当代美国职场这个研究对象而言,本书固然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研究。作者出入于各类数据图表和大量访谈材料之中,最终为我们编织起一张围绕“激情原则”所搭建起来的认知图示网络。本书最为深刻的洞察,莫过于证明了,哪怕仅仅将激情原则理解为一种流行的社会观念或文化偏好,它也从来不是横空出世之物;相反,求职领域的激情原则主张,深深奠基于近几十年来占据美国社会主流的绩优主义意识形态和新自由主义个人责任论。作者认为,这两种意识形态观念,共同造就了美国职场中蔓延着的“激情至上”风气。在这个意义上,《激情的陷阱》将应对当代美国求职困境的处方,把强调激情的个人主义话语提升为一套可供集体行动的前提方案,意在重新强调劳动力问题背后始终存在着的社会责任。

美国社会学家埃琳·契克
然而问题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关注集体困境、寻求职场不平等问题的集体解决方案,在我看来,顶多只能算是一种观念层面的纠偏之举,因为只消仔细看一下本书所提供的大量访谈资讯,便不难注意到谈论职场和劳动力问题的复杂性。至少从这项研究所聚焦的大量个体案例来看,处于求职状态或身处职场的个体,是否真的从行动到认知都脆弱不堪,这个问题本身就非常微妙。绝大多数书中采访到的美国大学生,如作者所言,对职场的认知从来都不“天真”。美国的求职者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单纯”或盲目才选择了寻求激情,与之相反,激情的追寻通常表现为一种应对恶劣职场环境的自愿选择。不少人提到,如果注定要面对一种普遍缺乏保障且艰辛过劳的职场生涯,不如从一开始就选择一份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职业,最起码可以让自己的人生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
照此看,激情作为一种情感和态度,本身就不那么同质化。至少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种截然不同的职场激情。积极的激情是将一个人喜欢、爱好什么,作为个人特异性和自我标榜的一部分,正如各类职场励志书籍中鼓吹的那样。消极的激情却是无可奈何心态下的产物,人们在工作和职业中寻求一丝可能始终不过是虚妄的“热爱”,仿佛自我安慰般地面对大概率如苦役一般的职场人生。当然,不管是积极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激情,还是带有自我保护和宽慰意味的、不无消极色彩的激情,从本书所揭示的追求激情的后果来看,大概率还是会把个体带入高度分化的不平等职场环境之中,并且事实上也很难用激情带来的情绪价值,一股脑地抵消职业不平等和职场剥削对劳动者造成的伤害。但真正的问题或许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激情”去探讨一种老生常谈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如本书反复谈到的种族/族裔、性别、阶级等既有框架),而是必须看到,在世界范围内遭遇“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尤其是全球经历新冠疫情的打击之后,追求职场激情——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职场文化副产品——为何在今天的社会流行思想中仍有极大的市场?这种观念与经济发展并不合拍的“韧性”反而更耐人寻味。
从这一点说开去,可以看到,尽管本书在探讨激情所带来的职业剥削问题时,经常追溯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刻洞见,但激情和劳动这个主题,反而更容易让人联想到韦伯关于劳动问题的经典分析。也就是说,现代劳动从来就不只是劳动本身,反而劳动很容易成为一种自我论证的中间物。不管这种自我论证、自我表达是否只是自作多情,一种与“自我”高度联动的想象和理解劳动的认知方式,始终是内在于现代劳动之中的特质,并且事实上构成了“劳动”一事的主要张力所在。然而本书却似乎有意绕开了这一点,这样也就拒绝了从韦伯思想的延长线上去重新审视劳动。
这种研究策略并非难以理解。因为在当下过分残酷的劳动力市场中,激情原则更容易显得像是一种自作多情的想象游戏。本书使用了多个角度来阐明,基于激情原则的求职策略终将导向不平等的职场后果。进而书中也谈到,一旦将激情视为应对自我异化劳动的方案,个体仍将不可避免地沦陷进异化劳动的讽刺结局。可问题在于,“在工作中寻求激情”的这种具有反讽色彩的劳动事实,恰恰折射出眼下已经沦为职场弱者的劳动者,或许只能以指向个体自我的“内求”方式去“选择”寻求激情,作为某种应对恶劣职场现实的脆弱抵抗。这项研究最终期待社会从外部改善职场环境,也呼唤一种更为宽松、包容的求职文化,却很少深入到个人层面去关心和探讨,劳动者应该如何看待并安放这种常见的职业激情。或许这是无解的。恰如“主义无法解决失恋”这个玩笑所昭示的那样,不论如何改善整体的职场环境,职业激情的追求以及为此可能带来的个体挫败,本身就不是这项研究所能彻底覆盖的内容。
所以阅读这部著作仍需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对个体的求职者或已经步入职场的“打工人”来说,可能很难从本书寻求个人应对职场困难的具体回答,因为本书志不在此。可本书的意义在于,至少对那些无法清楚辨识职场困境的人,它能让人收获一份“清醒”,学会用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思考自我与职场的关系。其次,必须注意美国职场与中国职场的巨大差异。正如书中提到,大量亚裔案例往往在求职时更重视薪酬和社会流动。在中国的职场文化中,即便很难说突出自我实现的求职文化就真的全无市场,激情也很少被视作求职的至高原则。这是中国与美国职场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中国,求职者通常会抱有一种强烈目标导向的求职心态,对于理想职业的认知却又高度的同质化。最终,大部分求职者会为了某个理想职业,很早进行大量个人投资,这个过程往往过度地漠视激情和个体的主观爱好。与此同时,中国式的理想职业背后,又通常捆绑了大量来自家庭的需求和期待。于是在职业环境持续劣化的今天,职场中弥漫着“空心化”和无意义感,充斥着带有强烈自我“工具人”倾向的“打工人”。
上述观察或许未见得准确,但我们仍有必要提示本书的预期读者:与《激情的陷阱》所揭示美国社会和美国职场相比,在激情劳动的问题上,中国显然代表了一种相当不同的现实语境。但是,不管怎么说,将这本《激情的陷阱》视作批判优绩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剂猛药,倒也未尝不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一个“优绩”日渐不等同于“优秀”、“优秀”也很难继续兑换“优越”的时代。相反,人们或许正在意识到,论证“优秀”并不意味着要去不断迎合各种外在化的优绩指标,而已经出身优越的人们不仅可以巩固既有的地位,这种不平等的“优越”,进而还能“制造”出更多“优秀”的个体。考虑到这点,本书将个体职业困境同社会不平等问题联系起来,显然便是相当值得关注的分析路径了。
此处中译本采用了更符合全书内容的副标题“过度工作、理想工人和劳动回报”,正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书中记录下的大量激情追求者们,在真实美国职场中所经历的冷酷现实。我们希望,在这个职场环境不断劣化的时代里,唤醒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劳动心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希望将“激情”这种情感元素完全从职场中剥离。既然工作时间无限延长已经是事实,生活被工作所吞噬和并轨,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结果,那么对工作情绪价值和切身感觉的强调,对于朝不保夕的打工者而言,又算什么根本性的谬误呢?换句话说,哪怕激情只是甜味素,至少它让我们的职业生涯尝起来不那么“苦”——这话献给所有在“比烂”的职业选项中反复犹豫着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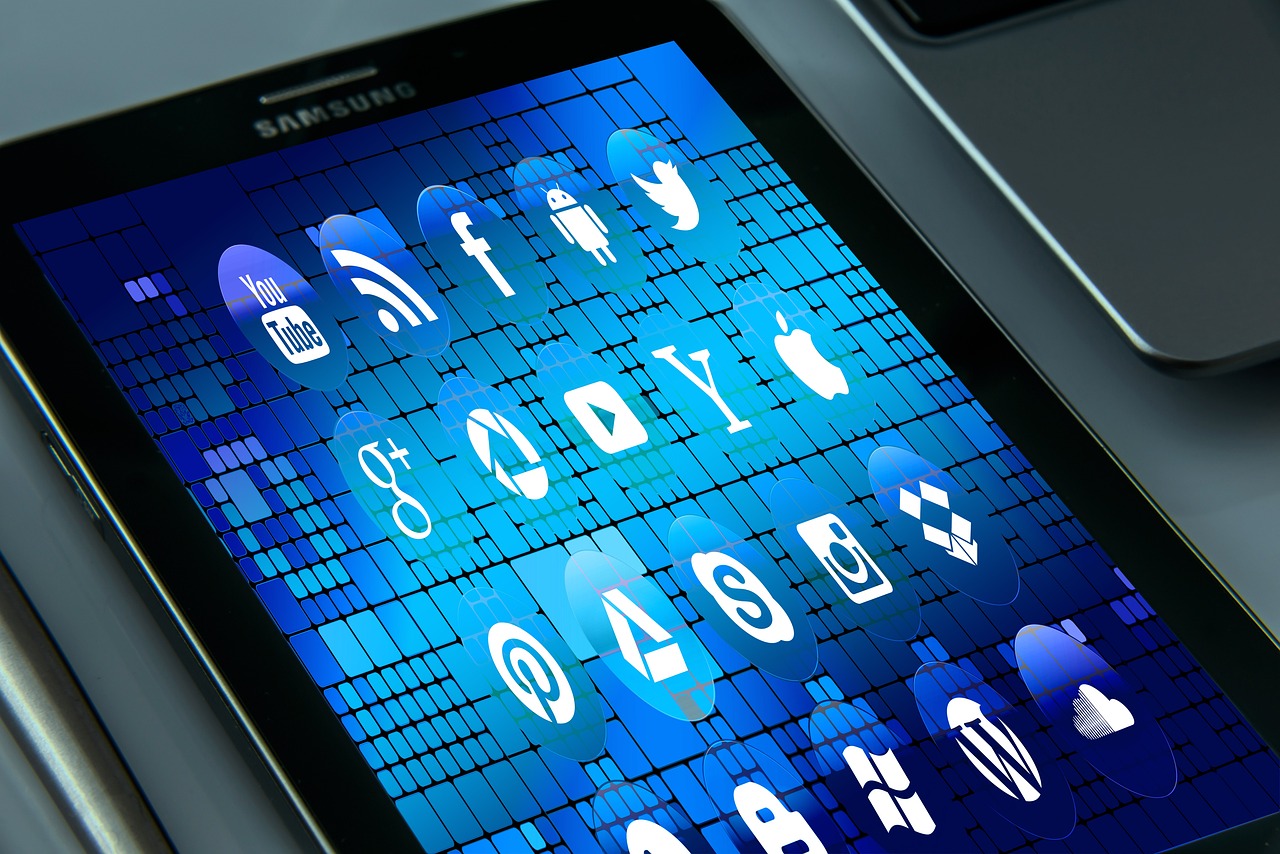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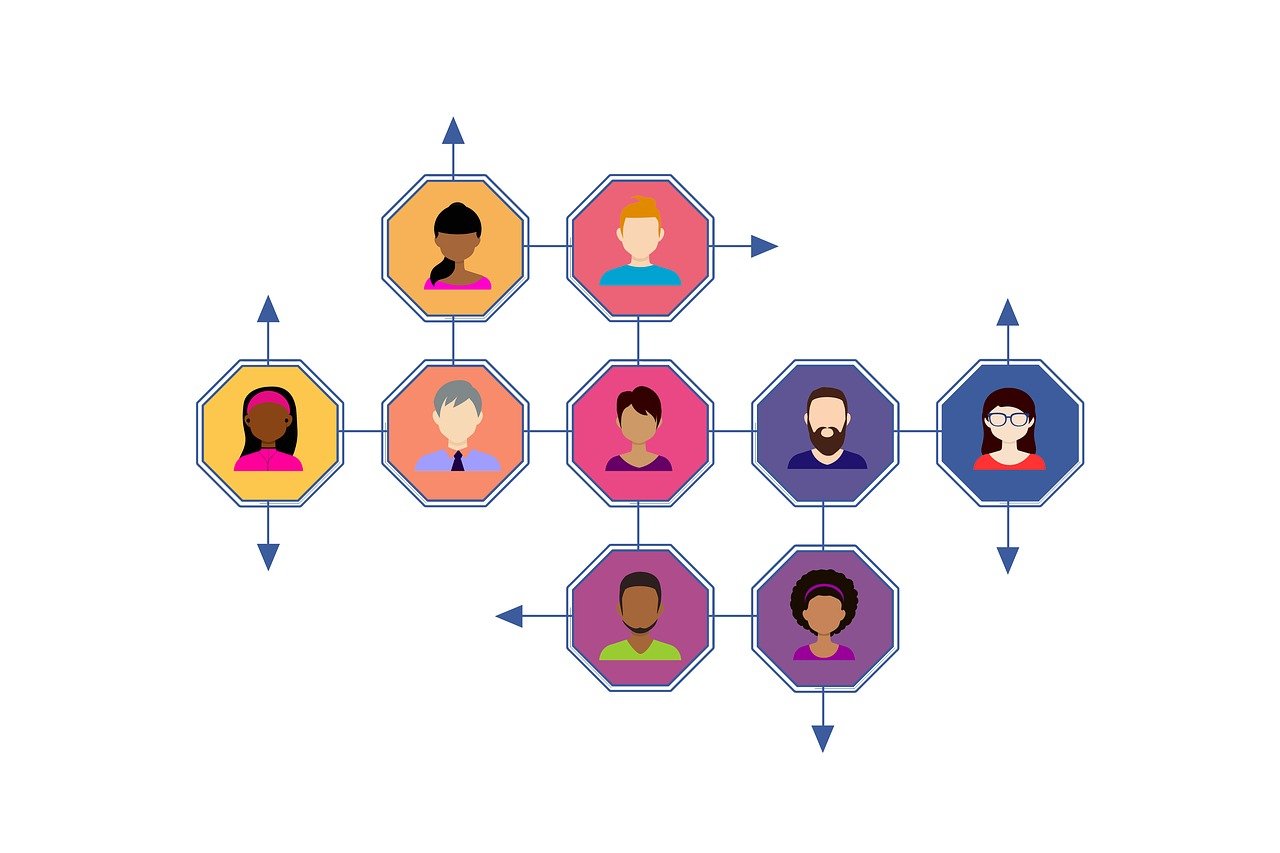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